
文 / 许德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文摘要:与合同成立不同,无效系价值考量而非事实判断,应与因意思瑕疵如欺诈胁迫等而撤销、因行为人未作出行为如被代理人未授权等而无从归属等情形区分开来。《民法典》第153条确立了民事争议的裁判者在判断合同违法无效过程中的权威地位和主导身份,是效力判断的裁量依据。违法、背俗无效与违反类型强制无效有重大差异,前者在于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道德准则,后者则主要服务于降低沟通成本,以促进交易便捷地达成,故应被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合同的批准生效规则系国家对特定合同效力类型审查上的例外保留,应区分批准行为主体、批准内容等类型化地考察相应效力。在上述类型化区分的基础上,主合同无效仅于违法无效时方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相对不生效指物权变动相对于特定第三人的权利内容而言不发生效力。
关键词:无效;成立;越权代表;无权代理;批准生效;合同形式;可撤销;相对不生效
目 录
一、无效系价值考量而非事实判断
二、违法、背俗无效与违反类型强制无效有重大差异
三、批准生效合同应类别化对待
四、主合同无效仅于违法无效时方导致保证合同无效
五、相对不生效指权利变动相对于特定第三人的权利内容而言不发生效力
六、余论
导言:
在合同从成立到确定生效并可履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仅用“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等概念难以充分概括或描述的效力状态。在这一背景下,理论与实践中有很多关于合同效力分类,尤其是合同无效分类的有益讨论。[1]对此,学者如韩世远老师、耿林老师等认为,在确定类型后,的确有关效果不言自明,但类型判断本身同样需要费力斟酌,未必能减轻工作负担。[2]因此,考虑到无效判断问题的复杂性,不人为地对具有强制因素的规范做概念区分(“统一说”)更合适,即将效力规范统称为“强制规范”,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地判断有关规范的性质及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3]学者如杨代雄老师也指出,尽管比较法如德国法上规范性质说并没有被完全摒弃,但已非主导性学说,而更多是强调规范重心与规范目的。[4]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关于合同效力的类型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目标,其一是将合同效力问题与合同成立等非合同效力问题区分开来,以期更准确辨识影响合同拘束力的不同因素;其二是通过必要的类型界定,寻找合同效力类型化判断与效力综合统一判断之间的平衡点,以期减少合同效力裁判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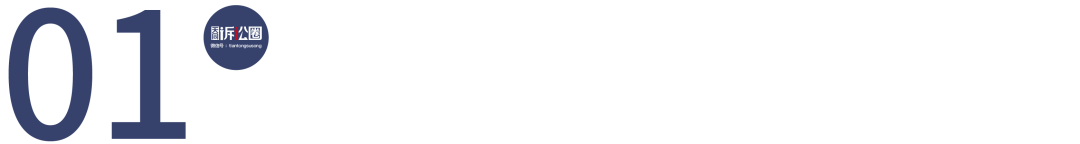
无效系价值考量而非事实判断
欲仔细探究“合同效力”的含义,须了解其来源。关于合同效力即合同拘束力的来源,理论上有诸多深入探讨。例如,我国有研究认为,应将合同效力基础归结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非法律规定,如认为“制定法赋予(法律行为)效力时须尊重行为人的意志”,“所谓自由形成法律关系,是指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决定法律关系”。[5]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行为是“依照当事人自由之意思发生其意愿的法律效果的行为”。[6]这一观点采纳了意思主义[7]的合同拘束力理论,接近康德关于“(试图论证)我为什么应该遵守我的诺言”是徒劳的,因为遵守允诺是一个“纯粹理性的公设”[8]的观念,难以反驳,但可能忽略了合同法背后的价值多元性。例如,在早期的合同制度中,合同拘束力被认为是来源于行为的特定形式本身(“歃血为盟”),在这些形式背后,隐藏着神意或者某种神秘的力量。当前,意思主义以外的合同拘束力理论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如信赖主义[9]的观点认为合同拘束力源于保护信赖的需要,功能主义的观点则认为合同拘束力源于促进福利或提高效率[10]的需要。[11]总之,关于合同的效力,意思理论有强大的解释力,不过,当事人达成意思一致合同即生效固然为常态(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民法典》第502条第1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即确立了“法律行为有效推定原则”[12]),却也不能完全排除国家基于管制需求,对合同的效力个别地予以审查和限制,从而使合同成立与合同最终确定生效之间存在时间差。[13]此种对合同效力的个别审查或限制,在性质上不属于对当事人是否达成了意思一致的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考量,重心在于审查当事人的合同安排是否符合法律所确立的价值选择。
1.狭义无权代理或越权代表应导致合同不成立而非无效
(1)狭义无权代理订立之合同的效力不能归属于本人
合同成立与合同效力的区别是,合同成立指双方当事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状态,合同生效则是国家经过对合同的评价,对其法律上拘束力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无权代理订立的合同,如A持伪造的授权委托书谎称有著名企业甲的授权,以甲的名义与乙订立合同,因A并无代理权,故其意思表示并不能归属于甲。换言之,此种情况下甲并未作出意思表示,故在甲与乙之间并不成立合同关系,这也意味着《民法典》第171条中的“不发生效力”是一个用词准确的结果性描述,“不发生效力”的结果,是因欠缺代理权,代理行为的效果不能归属于被代理人,有关法律行为未在甲乙之间成立。与此相对应,在理解《民法典》第172条在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时,也应认识到该条中“代理行为有效”这一表达所描述的并非无权代理人所实施的行为“有效”,而是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或有关的法律行为在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成立”。在上述背景下,《合同编解释》第18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虽有“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但该规定旨在限制或者赋予民事权利,行为人违反该规定将构成无权处分、无权代理、越权代表等,或者导致合同相对人、第三人因此获得撤销权、解除权等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违反该规定的民事法律后果认定合同效力”,就区分了“不能归属”与“无效”,较好地贯彻了这一原理。
归属(Zurechnung),是使一人的行为效果由另一人承担的法律技术,主要指特定主体(如被代理人)的行为并未满足有关的构成要件(如未与相对人订立合同),但基于归属规范的补足(如代理规范),仍然将有关法律效果归于该主体的法律技术。[14]可以看出,归属制度的功能,主要是补足特定的构成要件即法律行为成立层面的事项,而非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评价,如代理制度补足了本人未作出意思表示的要件缺失,善意取得制度补足了处分人无处分权的要件缺失。在补足了全部构成要件后,法律行为才成立,在此基础上,才有效力评价的问题:如果有关“被代理人—代理人—相对人”的行为违法,则有关行为仍然不能被(国家)认可或赋予强制执行力。[15]在这个意义上,“无权处分、无权代理、越权代表”并不适用《民法典》第153条,而应根据“无权处分”、“无权代理”、“越权代表”等相关制度确定行为的法律效果,如在“狭义无权代理”“越权代表”的情况下,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一般无须承担责任,而行为人须承担无权代理所引发的履行或赔偿责任;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若第三人构成善意取得,则无权处分人可能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或者违约责任。
(2)越权代表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无拘束力
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并不能导致本人与相对人之间成立合同关系,或者说,有关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见《民法典》第171条第1款),是容易理解的。但对其中“归属”的内涵理解不深刻,会引向不准确的结论。例如,按照《合同编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在越权代表的情况下,有关代表行为不对法人发生拘束力,但是法人有过错的,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便是错误的规定。
产生这一错误认识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过分关注越权行为的侵权乃至违法属性,并以该属性连接至第157条(当然,此种连接也是错误的,毕竟法人自身并未从事越权行为),而不是关注其中的“归属”要素;其二是机械理解了法人实在说或法人机关说。理论上,常有观点在提及“法人实在说”乃至“法人机关说”时,认为“机关成员的职务行为构成法人行为,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归属于另一个人’,而是‘部分之行为构成整体之行为’”,进而得出“法人机关成员不是法人的辅助人,因此其行为的效果承受不涉及行为归属”。[16]也有学者在概括“代表说”时,认为“当出现公司机关越权行为时,在代表说的观点下,机关的行为就是公司的行为,因此公司对机关的越权行为亦应承担责任”。[17]此类概括中关于“机关说”或“实在说”在越权代表中应用的描述是错误的。上述“法定代表人为法人机关”,“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等于法人的行为”“部分之行为构成整体之行为”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实在说”是针对非实体的学说,不能改变“实在说”或“代表说”背后的法人拟制属性。实际上,“机关说”“实在说”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其所描述的对象即法人的虚拟属性——对于原本就实际存在、可观察、触碰、感知的事物(人体、大脑),人们不必再提出个“实在说”(人体实在说、人体机关说)来描述它。这意味着,“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等于法人的行为”本身,其实还是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如同”法人的行为的变通说法。这种说法不能反过来被作为逻辑推理的起点,认为越权代表制度是和无权代理在本质上并不相同的制度。抽象而言,法人的概念、法人权利能力等概念的核心着眼点,就在于解决法人无法独立于其成员,但又要区分于其成员的问题。[18]对此,代理制度提供了难以超越的、不能更成熟的制度框架。在上述背景下,应当认为,在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时,若要确定越权代表情形下法人的责任,第171条关于无权代理法律后果的规定、《民法典》第500条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19]或《民法典》第1165条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20],都是比第157条更合适的选择。
2.合同成立在性质上指称意思表示一致的事实状态
“合同成立”与“意思一致”大体相等。这意味着,若当事人将合同成立系于意思之外的因素,就会与“成立”这一概念相矛盾,宜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解释。例如,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盖章的同时,约定“本合同自XX政府部门批准之日起成立”,其中的“成立”解释为“生效”便更为合适。虽然合同成立后未必能即时生效或全部生效,但也至少会发生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撤销合同的效力,很多时候还产生促进合同生效的义务(见后文关于批准生效合同的论述)。
合同形式问题可以很好地揭示成立与生效的区别,尤其是合同成立的事实属性。在我国法上,常有观点认为,若不考虑遗嘱的特殊情况,根据现行法的规定(主要是反面解释《民法典》第490条第2款),如果没有采取法律规定或约定的形式,有关合同是不成立的。[21]这一观点,可能误解了合同形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也与《民法典》第134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相冲突。
就其性质而言,法律对交易形式的要求,本质上是一种对交易的政策性规制(通常所说的证据功能或警示功能亦均是如此),故其所影响的对象应是效力而不是成立。另外,朱广新老师关于“《民法典》第490条第2款履行治愈形式瑕疵必须以合同(合意)已经存在为前提,如果合同尚未成立(不存在),权利与义务无从发生,何谈履行”[22]的意见,也值得赞同。不过,仅仅从逻辑上批评这一规则,理由或许还不够充分。诚然,在存在这一规定的情况下,需要通过“逻辑上的一秒钟”进行“拟制”,即有关合同在履行的同时(或履行后一秒钟)成立。但在未采取法定或约定形式则合同不生效的主张之下,也会存在这样的逻辑问题:既然合同尚未生效,如何履行(有拘束力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只有将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解释为是履行“尚未产生拘束力的‘内容’”,逻辑上才能圆通,或者也要动用“逻辑上的一秒钟”,认为有关合同的履行的同时生效,如此一来,“履行生效”(或者“未采书面形式则合同成立但不生效”)的主张在论证上便没有明显的优越性。
将形式作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可使合同形式制度的层次更丰富,有助于更妥善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体而言,成立与否主要是事实层面的判断,裁判者的回旋余地较小:在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况下,或许还可以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认为其事实上并未就书面形式达成真正的一致;但在法律规定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的情况下,如果同时认为有关法律规则导致合同不成立(如文义解释第490条第2款),则裁判者的裁量空间将极有限)。与成立相对,有效与否乃是价值衡量,裁判者可以在合同成立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权衡,必要时通过援引诚信原则等确立例外规则判定合同有效。例如,在英美法上,未按《防止欺诈法》采取特定形式的合同虽然无强制执行力(相当于我国法上的无效),但若相对人信赖该合同而作出相应的行为,裁判者仍可根据信赖或禁反言等规则例外地肯定合同的效力。[23]又如在德国法上,尽管裁判者不能仅根据公平考量而确认合同有效,但如果综合相关事实认定合同无效将严重违反诚实信用且效果上将使一方合同当事人“难以承受”,法院也可以例外地援引诚实信用原则肯定合同的效力。[24]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通常情况下合同不成立和合同不生效在效果上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另外在当事人未采取法定或约定的书面形式时,也往往难以认为其达成了意思表示的一致,《民法典》第490条第2款(的反面解释)也是勉强可接受的规则。当然,虽然可能不得不接受现行法中未采取书面形式合同不成立的规定,但合同不成立的法律后果并非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在一方有违诚信时,另一方当事人仍可根据《民法典》第500条要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乃至赔偿全部履行利益的损失。
3.可撤销与无效体现了不同的法律评价
在讨论法律行为效力时,学者如朱庆育老师等曾将效力瑕疵事由分为三类[25]:源于自身因素的效力瑕疵事由(包括行为能力、意思保留和错误)、源于他人因素的效力瑕疵事由(包括欺诈、胁迫等对表意自由的影响和无权处分、无权代理等事务处置行为)和源于秩序因素的效力瑕疵事由(包括法律禁令、公序良俗和形式强制)。仅就无效的后果而言,这些分类是妥当的。但把不同类型的无效原因混在一起描述,可能导致误用或误判。例如,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26条并未规定合同可撤销,而是规定为无效,便不仅有违民法法理,也剥夺了劳动者维持合同关系的可能性(例如雇主在工作内容上欺诈劳动者,但劳动者并不排斥相应工作,愿意继续受雇)。[26]
就其性质而言,“自身因素”与“他人因素”的效力瑕疵事由,其实可以归为一类,即都指向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瑕疵”意思表示不能产生效力的根源不在于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给予否定的评价,而恰恰在于对当事人真意的遵循。或者说,这一过程并不是对一个已经存在的行为加以否认,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法律所认可的行为,自然也谈不上对行为效力的否定。
之所以将因可撤销行为导致的合同无效与违法无效区分开来,在于二者的无效原因及与之相关的法律后果有重大差异。一方面,在可撤销的场合,当事人仍保有不行使撤销权即肯定合同效力的选择,而违法无效的法律后果是不容当事人自主决定的。例如,对于通过假离婚或假结婚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固然有认定为无效的空间,但对于“假离婚”行为本身,若并不涉及第三人利益,依可撤销规则将有权撤销的主体限于婚姻行为当事人更为合适,即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撤销“假离婚”协议,还是“假戏真做”。另一方面,合同在因意思瑕疵而被撤销后,通常发生一方赔偿另一方损害的问题,如行为人对重大误解的相对方,对受欺诈、受胁迫方的赔偿;而在合同违法无效时,通常较少涉及一方对另一方的赔偿。例如,当事人为了获取垄断利益而订立固定销售价格﹑限制生产销售数量﹑划分市场的垄断协议,都会构成排除或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法》否定的行为,进而被认定为无效。[27]对于此种协议,就没有保护其中某一方当事人的必要。
4.通谋虚伪表示导致法律行为不成立
在《民法典》的一些条文中,有时虽然使用了“无效”的表述,但其含义并不是因为某项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由国家否定其效力,而是因欠缺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而不生效力。例如,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的“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若有关虚假行为并不直接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害,则此种“无效”在性质上更多是属于因欠缺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而不生效力,而非国家基于特定公共政策否定其效力(如毒品买卖合同无效)。在这个意义上,《合同编解释》第14条第1款规定的“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交易订立多份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中的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其中的“无效”更多是因有关意思表示未达成一致而不发生效力。例如,表哥甲欲将其所有的汽车赠与给表弟乙(设二人均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经济独立),但甲将此事告知父母时,甲父母持反对的意见,为宽慰父母,甲与乙“订立”汽车买卖合同,将汽车出卖给乙,价款30万元,但实际上并无出卖的意思。一年后,甲与乙因其他事情发生争执,甲因故诉请乙按买卖合同支付价款30万元。对此,乙可主张买卖合同为基于通谋虚伪表示订立,进而无需承担付款义务。类似地,在涉及阴阳合同的争议中,“阳合同”因不能反映当事人的真意,并不能据此认定为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故性质上亦属于不成立。[28]至于“阴合同”合同能否成立、生效,以及当事人是否依约履行,还需要根据相应的成立、生效规则综合判断。
认为通谋虚伪表示本身并不构成违法无效,即仅导致合同不成立,还可以为其他制度构建基础。[29]例如,在前述表哥甲与表弟乙的例子中,表哥向第三人丙表示,表弟乙欠车款30万元,并将该债权让与给丙,在丙向乙核实时,乙表示“确有其事”,此后,乙可能便不得以其与甲之间的合同为通谋虚伪表示而对抗丙。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民法典》第763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如果认为通谋虚伪合同具有违法属性因而将其评价为无效,则很难正当化对第三人的信赖保护。
5.《民法典》第153条是效力判断的裁量依据
影响合同效力的规范散见于《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主要是公法规范),且数量上后者占主体。那么,在存在《民法典》之外的、可能影响合同效力的其他公法规范时,判断合同效力究竟应以该规范为依据,还是应以《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为依据呢?回答是:二者均是依据,但《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30]是基础,即并非要从强制规范出发并追问其是否要求有关法律行为“无效”,而是要通过第153条第1款判断该规定是否导致合同无效,及有关具体案件中是否存在“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31]当然,如果特别法已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了规定,则直接依据该特别法处理即可,无须再动用第153条第1款。[32]第153条第1款是一个规定于民法中的“公法评价规范”[33],用以评价有关公法强制规范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影响。[34]该规范被学者如耿林老师称为“引致规范”,即通过该规范,把“无私法效果规定的行为要求规范与私法上的法律行为效果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对于具体强制规范本身而言,特别是对来自公法性质的强制规范来说,其规范目的本身通常并不直接涉及法律行为的效力”。[35]例如,对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4条规定的“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如果仅就这个规范目的本身解释,得出的将是公法效果本身”[36],欲使其对民商事交易发挥作用,还需要第153条第1款的介入。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将第153条第1款称为“引致规范”,其“引致”的功能也不宜过分强调。换言之,第153条第1款的核心作用仍在于“评价”(有关强制规范),至于“引致”公法强制规范,不过是评价的步骤或后果而已。对于第153条第1款的性质或功能,更妥当的描述是,该条为民商事争议的裁判者探究公法强制规范的目的及影响提供了依据,用以决定有关公法强制规范“是否需要以影响私法上法律行为的某种效果作为必要的配合”[37],以实现公法目的与私法自治的妥当平衡。《合同编解释》第16条关于《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但书“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解释,就很好地彰显了第153条第1款所确立的裁判者在判断合同违法无效过程中的权威地位和主导身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153条第2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有助于更好地阐明第153条第1款本身即为评价规范,是裁判者裁量的依据,而非仅仅是“引致”规范的观点:虽然作为一项效力评价规范,第153条第2款并未界定公序良俗的含义(裁判者也要求助于社会一般观念以认定有关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但这并不妨碍法官以该条为依据认定某项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说,有关行为无效的依据并不是社会一般观念中的道德标准,而是经由153条第2款评价的“公序良俗”。
综上所述,尽管合同“无效”可以有不同含义,但通常人们心中“无效”的原型,常常是“违法无效”或“自始、确定、终局”无效,包括因违反具体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无效(《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也包括违反法律规范的整体性价值即公序良俗而无效(《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如果不保持认识上的“警惕”,泛化“无效”的概念,很容易把第171条第1款中无权代理的法律行为“不生效力”或第146条第1款中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理解为“违法无效”,进而适用有关违法无效的制度,从而不能正确处理有关的法律关系。在上述背景下,《合同编解释》第18条关于不适用民法典第153条的情形有其深意,值得赞同,而第20条第1款则误将不能归属看做是无效,存在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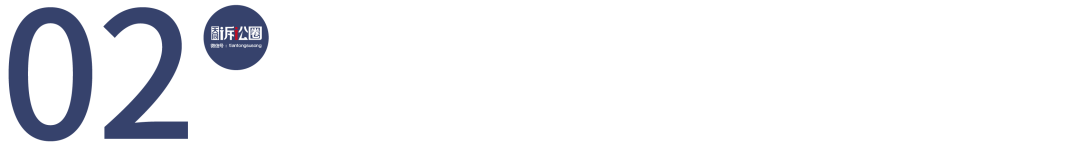
违法、背俗无效与违反类型强制无效有重大差异
违反类型强制无效指因违反有关用于类型强制的法律规范而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例如,为了促进票据流通和票据使用的效率,我国《票据法》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第8条),以及“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第9条)。此处的“无效”虽然指有关票据不生效力,但主要强调票据(作为合同关系的标准化呈现)应遵循特定形式,并无在道德层面予以否定的意味。[38]又如,如前所述,若认为不符合法定形式要求则合同无效(而不是现行法所规定的成立),则该种“无效”就是典型的违反类型强制的无效。
理论上将违法及背俗无效与违反类型强制无效都归结为秩序因素的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事由,在逻辑上是通顺的,毕竟类型强制也是一种法律上的秩序要求。[39]但是,若停留在将类型强制与违法或背俗等同对待这一步,便仍欠精细,容易让人错误地以为违反类型强制与背俗或违法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事实上,在效力上,违法及背俗无效的合同是不可补救的;而违反类型强制的合同,则是事后可补救的(如完善有关形式要求);在违法及背俗无效时,双方常常均有过错,难谓一方对另一方负有赔偿责任,而在合同因违反类型强制而无效时,常存在一方须承担责任的问题。
法律关于类型强制的要求,主要服务于降低交易成本。在这个意义上,类型强制规范是中性规范,相当于确立了一种统一的交易符号,以便利各方交往,如法律关于不动产抵押须办理登记方可生效的要求。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类型强制规范也具有实现公平交易、保护特定主体利益的功能。如《民法典》第401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虽然表面上是对抵押权实现的方式作了限定,但其客观上也具有保护抵押人的效果。《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未经公司决议越权提供担保不对公司发生效力的规则,表面上是规定了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规则,也同时具有保护公司其他股东的效果。在法律规范具有此种混合属性时,不应将其仅仅作为类型强制规范对待,而是应结合其规范目的,综合地加以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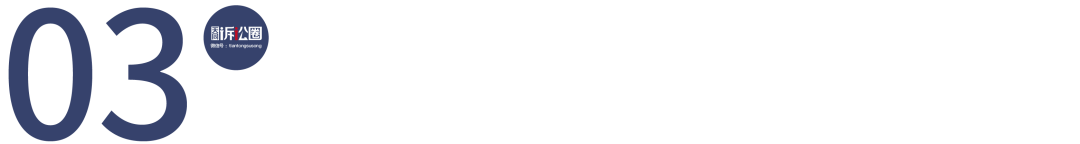
批准生效合同应类别化对待
在某些情况下,或者源于当事人的意思(如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或附生效期限的合同),或者源于国家的管制需求(如需要批准生效的合同),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之间会存在时间差。不过,即便存在时间差,一般认为合同成立后就会产生某种拘束力,如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事实上产生了当事人不能单方阻止条件成就的义务(第159条),而需要批准方能生效条件的合同,通常也会产生当事人协力报批的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的违约责任(第502条第2款)。另外,合同成立后,争议解决条款、保密义务等辅助约定,通常也自成立时起即发生拘束力。
对于已经成立但尚未被批准的合同中的主给付义务,学说上存在共识,即认为该部分的生效,取决国家的个别许可。此种个别许可的安排,与合同只要达成意思一致且不违反法律即生效力的一般许可相对,是国家对特定合同效力审查上的例外保留。实践中分歧较多的,是关于批准生效合同中报批义务的属性。报批(义务)约定与争议解决条款、保密条款等事实上具有独立性的合同条款不同,构成主合同义务生效的前提。甚至,若有关合同因法律规定须进行报批,在当事人未约定的情况下,该报批义务也客观存在,并具有拘束力(第502条第2款第2句)。
对于尚未被批准的合同,我国一些研究[40]主张应称之为“未生效合同”,即该类合同具备“有效要件(一般生效要件)但不具备特别生效要件”,已“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第119条),而且应“受法律保护”(第465条)。[41]上述分析结论值得赞同:在合同应予批准而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虽然“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乃至(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履行的“义务”已具备拘束力,但合同的(需要批准的)主体内容尚未生效。[42]不过,对于此类合同,称之为“未生效合同”还是容易引起误解,尤其容易使人以为未生效的合同也能产生拘束力。或许阐明其全称为“报批义务已生效的待批准合同”或更完整的“报批义务已生效,待批准内容尚未生效的合同”更为合适。也在这个意义上,《民法典》第502条第2款第2句中规定的“违反该义务的责任”,被解释为违约责任更为合适,而《合同编解释》第12条第1款中规定的“继续履行”与“赔偿责任”也应理解为合同义务的继续履行及违约损害赔偿。
关于报批义务拘束力的来源,目前学界结合合同拘束力理论(报批义务成立后即可产生拘束力)、类推附条件合同的理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展开的论述已相当充分。[43]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确立报批安排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影响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44]以下区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加以说明。
其一,批准安排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设置批准要求,以便个别判断有关交易是否符合国家政策考量。对此,我国的出口管制审查(出口管制法)、反垄断部门对涉及“经营者集中”合同的审查等(反垄断法),外商投资、技术转让等的国家安全审查(国家安全法)可作为例证。对于此类批准要求,若合同订立后未能依法完成,则有关合同的主体部分应不发生效力。从形式上看,在这一类批准中,批准者乃是以国家法律的执行者身份从事具体行政行为。不过,就其实质而言,正如马新彦老师所指出的,决定合同是否批准的与其说是行政机关,不如说是法律的明文规定。[45]在这个意义上,若有关合同不能通过批准,表面上看是国家行政机关以具体行政行为否定了合同的效力,但实质上仍然是有关合同违反了法律而不能产生合同效力。[46]这意味着,即便当事人不申请批准而自行从事相应的活动(如订立并履行会产生经营者集中效果的并购协议),有关合同也会因违法而无效。例如,在反垄断审查实践中,市场主体间的经营者集中行为需要经过事先审查,被批准后才能得以实施(《反垄断法》第26条),这意味着,未经审查而自行实施的经营者集中行为是无效的,实际上,所有“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第3条),都是《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的“垄断行为”。
其二,有些批准既涉及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具通过财产最终所有者的同意补足当事人(可能是所有者代理人)意思能力不足的意涵,如对各类处分国有资产交易的批准:处分人所处分的国有资产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同时,处分人在处分时又会被作为民法主体对待,因此又有如何作出意思表示的问题。在这类交易中,批准者在形式上是行政机关,更是民法上的“所有权人”;其批准行为是一种行政许可,更是最终所有者在作出意思表示。[47]例如,在转让国有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时,根据法律的规定,应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批准相关交易。[48]此类批准在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真正的股东(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所代表的国家)就转让股份这一特定事项作出决定,从而使这种“批准”与单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进行的批准有所差别,而和股东会批准公司对外担保或行为人欠缺代理授权而由被代理人追认有更大的相似性。[49]这意味着,在讨论因未批准而产生的责任时,一方面不宜以未经审批则不生效的思路处理合同效力问题;另一方面也有考虑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应否受保护,以及在未批准时行为人应否承担无权代理责任的必要。
其三,有一些类似批准的“同意”,在内容上与行政许可相去甚远,而与民法上的意思表示更近。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4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或《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转让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受让人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并提交双方转让协议,依照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程序报请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此处的“同意”或“批准”,在性质上其实接近于《民法典》第555条规定的债权债务概括转移中,一方当事人对转让债权债务的“同意”。在这个意义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前句规定的“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应限缩解释为转让对发包方不发生效力,而不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无效。实际上,该条后句规定的“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也更多是强调发包方就像债务人在债权让与中并无实质决定权一样,原则上应予同意,而不是“批准”有关转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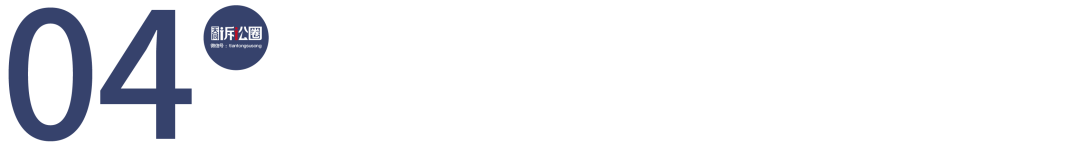
主合同无效仅于违法无效时方导致保证合同无效
合同效力具有诸多状态,其既受当事人意思的影响,又受法律规定、公序良俗、社会一般价值的影响,应当精细地加以区分,而不应将“无效”等同于“违法无效”,以至于难以细致地解析当事人的权利状态。以《民法典》“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第682条)的说法为例,这里的“无效”如果理解为是“违法无效”,则相关规定是合理的,但如果认为包含了各类无效的情形,很可能会过分干涉当事人的自愿约定。例如,我国《公司法》第121条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年)》第78条规定,“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若某个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而从事了相应交易,如与合同相对方订立重大资产出售合同,同时约定上市公司将在特定时间内召开股东大会作出有关决议,另外,约定合同相对方(在股东大会决议前)先付款,并由第三人为该上市公司交付有关资产提供保证担保。此后,公司未能召开股东大会批准该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有关重大资产转让合同无效,将直接导致《民法典》第682条的适用,从而担保合同也无效,进而上述重大资产购买人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为避免此种不当结果,《担保制度解释》第2条(“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或者约定担保人对主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担保责任,该有关担保独立性的约定无效”)中的“主合同无效”应当解释为“违法无效”。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主张,《担保制度解释》第2条的上述规定,应限缩解释为当事人不得在同一份保证(担保)合同中对主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在另一份保证合同约定对主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承担担保责任,则该合同有效,实系不得已而为之的解释方案。[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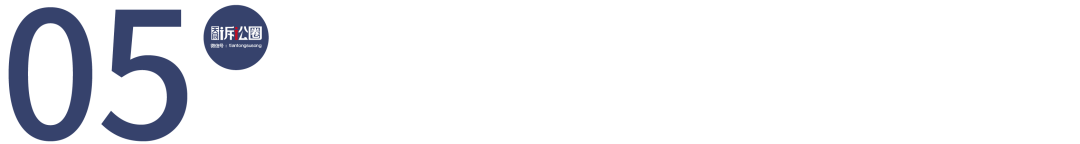
相对不生效指权利变动相对于特定第三人的权利内容而言不发生效力
在合同“生效”和“无效”之间,存在中间地带。“相对不生效”就是其中之一,又称处分行为相对于第三人不生效(relative Unwirksamkeit einer Verfügung[51]),主要指有关的处分行为相对于特定第三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发生效力。例如(例1),在所有权人(A)与第一买受人(B)订立买卖合同,并为B设定了预告登记的情况下,A又将房屋出卖于第二买受人(C)。此时,即便法律允许C被登记为新所有权人,该项权利变动在B的权利范围内相对于B也不生效力。[52]又如(例2),公司原股东(A)在未征求其他股东(B)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C)转让有限公司的股份时,该项股权变动相对于B也不发生效力。[53]
对于如何妥当运用教义学工具描述“相对不生效”的构成,理论上有很多讨论。对此,值得参考的学说是:在前述例1中,C已因物权合意与登记行为而取得所有权,但该所有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具体而言,该所有权会因预告登记权利人B行使权利而“瞬间”回归至出卖人A,并应B的请求,经过此后的登记程序而移转给买受人B。可以看出,在这个描述中,需要拟制地认为A还可以因相对不生效而成为所有权人,同时运用“瞬间”变动的“技术”(其实也是一种拟制),使所有权在AC、AB之间转移。
“相对不生效”所指的主要是处分行为,尤其是物权变动相对于特定人不发生效力,而不是债权合同因为特定人的主张而不发生效力。原因在于,合同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国家的一般性承认,原则上没有理由允许合同以外的其他私人否定合同的效力。以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例,此类合同无效的原因,要么在于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在恶意串通的程度重或负面影响大的情况下),要么构成串通行为人对特定第三人的(共同)侵权从而第三人可以通过恢复原状的救济主张废止有关合同,并不存在这两种情形之外的第三人主张恶意串通合同无效的可能。[54]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就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而言,通常否定有关权利变动的效果即可,而没必要否定整个交易的效力。以《民法典》第406条第1款为例,“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若当事人约定抵押物不得转让,而抵押人违反该约定转让了抵押物,无论有关约定是否进行了登记,抵押物转让合同的效力均不受该约定的影响(“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又如,在承租人违法转租的情况下,法律规定出租人可要求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解除合同,即足以保护出租人的利益,包括要求返还租赁物,而不必规定有关转租合同无效,实际上,《民法典》第716条第2款便未提及违法转租而转租合同无效的事由。在这个意义上,《城镇房屋租赁合同解释》第15条第1款(2009年)中关于“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房屋的……该转租合同可被认定为无效”的规定,是不妥当的。
在张俊秀诉唐韶华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案涉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转让出资应先由公司按不超过150%价格回购,公司回购后,按各股东持股比例向各股东分配。公司决定不回购的,股东方可依法向股东或者股东之外的人转让出资,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据此,法院认定有关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无法履行,且违反了当时《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第5项,因此应为无效,同时,根据该法第58条,认为双方均有过错,故唐某无须对张某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在这个裁判中,法院便未准确识别本案中出资转让协议系相对无效,并进一步将违反公司限制股份转让规则的行为定性为违法无效,存在效力类型上的认定错误。[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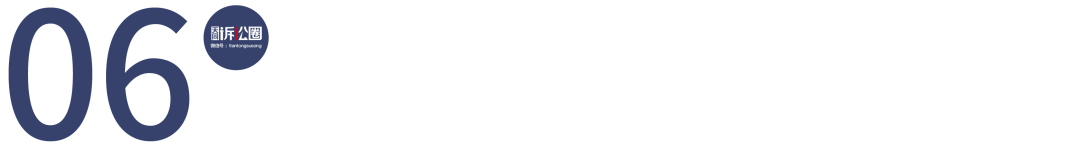
余论
承继《合同法》第58条,《民法典》第157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应“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的规定,将诸如违法无效、因意思瑕疵而撤销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未获追认等情形的法律后果混在一起,是理论与实践中忽略无效类型界分的重要原因。区分具体的效力类型,辨析成立作为事实判断与效力作为价值评价的差别,澄清违法无效与类型强制无效的差别,将有助于从构成要件层面建构相应制度的适用条件。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以不当得利法为中心的返还法,分别确定返还的法律效果,可更好地处理合同不生效力的诸种状态。
注:本文的写作,得到了王萌、李滕、张悦的研究协助,特此致谢。论文发表于《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6期,第19-31页。
注释:
[1] 例如,金可可老师认为,强行规定的违反又可以区分规范内容的违反与强行性面向的违反。进一步,依据规范内容,强行规定又可以区分为行为规范和单纯强行规定,其中单纯强行规定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内容无涉法律行为的规范和内容涉及法律行为的规范,后者又可以分为直接限制法律行为内容的规范和并非直接针对法律行为内容的规范。金可可:《强行规定与禁止规定》,《中德私法研究》,第13卷,2015年,第4-21页。又如,王轶老师认为,准予实施事实行为的行政许可为简单规范,准予实施法律行为的行政许可为复杂规范。准予实施事实行为的行政许可的规范(即简单规范)不能成为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换言之,违反此类规范的合同并无适用《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空间,应为有效。例如,在出租违法建筑的情况下,出租人所从事的违法建筑行为应当被处罚,违法建筑应当被拆除,但租赁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王轶:《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86页以下)。这一主张值得商榷。在法律规制某种事实行为的情况下,与该事实行为有关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是否受影响,仍然应当仔细考察法律规定的目的、违法的程度及违法行为所触及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判断,而不能仅基于法律所禁止的事实行为作出判断。例如,当事人违规设立烟草生产厂并转卖或出租该厂,有关该厂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按照王轶老师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12条等是有关烟草生产的简单规范,似乎有关合同就应当认定为有效。对此,另外一种说得通的推理是:烟草生产属于国家专门管制的领域,因此,该违规建设的烟草生产厂的转卖合同会因为标的不合法而无效。
[2] “规范目的的探寻无法通过对规范属性的界定替代。”韩世远:《规范属性、规范目的及合同效力评价》,《中德私法研究》,第13卷,2015年,第25页。卡纳里斯以德国最高法院根据《法律咨询法》(RBerG)禁止无照执业(因此不属于对合同内容的限制,而是对合同缔结主体资格的限制)的规则否定合同效力的例子,主张“对内容之否定和对合同缔结的环境的否定的区分显然是太狭隘了,不足以囊括所有要考虑的案件”。卡纳里斯:《法律禁令与法律行为》,赵文杰等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13卷,2015年,第59页。
[3] 耿林:《论中国法上强制性规定概念的统一性》,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51页。
[4] 杨代雄:《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96-407页。
[5]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6] 王洪亮:《法律行为与私人自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53页。
[7] Charles Fried, Contract as Promi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015, Chapter 2.
[8]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0页。
[9] Richard Craswell, Contract Law, Default Rules, and the Philosophy of Promising, 88 Mich. L. Rev. 489 (1989).
[10] Louis Kaplow et al., Fairness Versus Welfare, 114 Harvard Law Review 961 (2001).
[11] 上述所有理论都涉及“合同理论”(contract theory)这一哲学问题。系统的整理,见Daniel Markovits, and Emad Atiq, “Philosophy of Contract Law”,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21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21/entries/contract-law/. 总体而言,在上述理论中,意思理论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意思理论仍然要面对一些需例外处理的问题,如赠与合同、暴利(usury)等有失公平的合同是否具有拘束力等。
[12] 朱庆育:《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体系》,《师大法学》2019年第2期,第234页。
[13] 当然,即便存在时间差,源于对当事人自由意思的尊重,一般认为,合同成立后,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拘束力,如附生效条件或附期限的合同,事实上产生了当事人不能单方阻止条件成就的义务(如《民法典》第159条),又如需要批准方可生效条件的合同,通常也会产生当事人协力批准的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的违约责任(如《民法典》第502条第2款)。另外,合同成立后,有关争议解决的约定,通常自成立时起即发生拘束力。
[14] Reinhard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4. Aufl., 2016, S. 522-523; 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88-491页。
[15] „Zurechnungs- und Haftungsnormen zielen daher auf verschiedene Ebenen: Zurechnung zielt auf die Tatbestandsseite einer bezogenen Norm (was nicht ausschließt, dass die Zurechnungsnorm die Rechtsfolge der bezogenen Norm noch einmal wiederholt), während das Schwergewicht der Haftungsnormen auf der Rechtsfolgenseite liegt.“ Reinhard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4. Aufl., 2016, S. 522-525.
[16] 杨代雄:《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90页(注释4)。
[17] 王毓莹:《公司法定唯一代表制:反思与改革》,《清华法学》2022年第5期,第133页。
[18] 深入而有洞见的研究,见冯珏:《自然人与法人的权利能力——对于法人本质特征的追问》,《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364页以下。
[19] 若法人开启了缔约磋商、缔约准备或者交易接触,并在这一过程中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则法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杨代雄:《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541页。
[20] 纪海龙:《无权代理人过错责任及其减免——<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解释论》,《法学》2023年第1期,第144页。
[21] 顾昂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杨代雄:《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58-359页(认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490条第2款,只能将合同形式解释为合同的特别成立要件)。
[22] 即在尚无合同的情形下,“所谓‘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合同法实际上制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立法现象:在明确规定书面形式是合同成立的要件之同时,又规定不遵守法定书面形式要件同样可以成立合同”。朱广新:《书面形式与合同的成立》,《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59页以下。
[23] Farnsworth, Contracts, Aspen Publishers, 3rd Edition, 2004, pp. 190 ff.
[24] Palandt, 2022, § 125 Rn. 22.
[25] 朱庆育:《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体系》,《师大法学》2019年第2期,第237-246页;关于我国法曾用“无效”描述各种类型的“效力瑕疵”,也曾将“无效”称为“绝对无效”,将“可撤销”称为“相对无效”等学说发展过程的分析整理,见常鹏翱:《等同论否定说:法律行为的可撤销与相对无效的关系辨析》,《法学家》2020年第5期,第13-15页。
[26] 该法第38条还违反合同法基本法理地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该无效合同。谢增毅:《对<劳动合同法>若干不足的反思》,《法学杂志》2007年第6期,第63页;叶名怡:《<民法典>第157条(法律行为无效之法律后果)评注》,《法学家》2022年第1期,第189-190页。
[27] 王磊:《公私协动视野下垄断行为的私法效力认定》,《法学》2023年第8期,第108页。
[28] 石佳友:《融资性交易中名实不符合同效力认定规则之反思》,《法学评论》2023年第3期,第138页以下。
[29] 武腾:《无效、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与善意第三人保护》,《清华法学》2018年第1期,第159页。
[30]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31] 卡纳里斯:《法律禁令与法律行为》,赵文杰等译,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文中的第一项总结)。
[32] 如果司法解释可以被看作是“准特别法”的话,则诸如《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1条第1项,可认定为此种“特别法”(当然,这些规定也可以看作是对《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或当时的《合同法》第51条第5项)的解释)。姚明斌:《“效力性”强制规范裁判之考察与检讨》,《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第1268-1269页。
[33] 苏永钦老师称之为“转介条款”(苏永钦:《以公法规范控制私法契约—两岸转介条款的比较与操作建议》,《人大法律评论》2010年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0-21页,第25页),但“转介”二字容易和“引致”“转引”等表达混淆,让人以为《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纯粹是一个技术性规范,而非价值权衡的基础性规范。例如,苏永钦老师认为“通过转介条款源源引进的活水,古典的民法典才得以与时俱进”,系将有关被引入的公法强制规范作为“活水”,但按本文的主张,第153条第1款这一公法评价条款本身及与该条款相关的法教义学积累(包括案例类型、苏永钦老师提及的衡酌因素和裁量效果)才是“活水”,进而推动私法中的自治观念与公法中强制规范的互动和平衡。
[34] 卡纳里斯:《法律禁令与法律行为》,赵文杰等译,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35] 耿林:《论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法学家》2017年第1期,第127页。
[36] 耿林:《论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法学家》2017年第1期,第127页。
[37] 耿林:《论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法学家》2017年第1期,第127-128页。耿林老师这句“判断是否需要以影响私法上法律行为某种效果作为必要的配合”的落脚点是“以实现公法的目的”。这是值得商榷的:如上文所述,第153条第1款是民法规范,其功能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贯彻公法规范或“实现公法的目的”,而是平衡自治与管制,并在这一平衡的限度内实现公法的目的。强调此种“限度”非常重要,这是第153条第1款但书的要求,是司法裁判中不因某强制性规定而否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依据。
[38] 许德风:《合同自由与分配正义》,《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979-980页。
[39] 在该文中,朱庆育老师使用了“形式强制”这一表达,认为违法与背俗无效涉及的是法律对于行为内容的控制,而法律对行为形式的要求涉及的是对行为形式的控制。见朱庆育:《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体系》,《师大法学》2019年第2期,第238页,第245-246页。
[40] 刘贵祥:《论行政批准与合同效力———以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为线索》,《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吴光荣:《行政批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法学家》,2013年第1期,第99页;刘贵祥,吴光荣:《关于合同效力的几个问题》,《中国应用法学》,2021年第6期,第4-7页;许中缘:《未生效合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合同效力类型》,《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1期,第27-28页。蔡立东老师详细阐述了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别,认为“可见,合同有效表征私法规则赋予合同以法律效力的状态,而生效则表征这种效力现实地发生作用,特定义务已经具备履行条件,合同目的由此得以现实地实现,故有效合同方存在某些效力尚未发生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合同效力的长成逻辑不绝对是或不应绝对是作为‘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绑定进路’以及‘未生效合同说’背景的‘成立—未生效—生效—有效’,而应解为‘成立—有效—未生效—生效’”,值得赞同。蔡立东:《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第67-68页。
[41] 刘贵祥 吴光荣:《关于合同效力的几个问题》,《中国应用法学》,2021年第6期,第6页。
[42] 在指导案例123号中,法院认为,“对于于红岩反诉请求判令隆兴矿业继续履行办理采矿权转让的各种批准手续的请求,因双方在《矿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矿权转让手续由隆兴矿业负责办理,故该院予以支持”。
[43] 刘贵祥:《论行政批准与合同效力———以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为线索》,《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149页;吴光荣:《行政批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法学家》,2013年第1期,第111-112页;相关总结,见汤文平:《批准生效合同报批义务之违反、请求权方法与评价法学》,《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5-107页。
[44] 汤文平:《批准生效合同报批义务之违反、请求权方法与评价法学》,《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2-103页(类型区分)。
[45] 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规定,“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可以应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这进一步表明,决定合同效力的并不是行政机关,而依然是法律的规定。
[46] 马新彦:《论民法对合同行政批准的立法态度》,《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260-261页。
[47] 李永军:《民法典编纂中的行政法因素》,《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2页。
[48] 如《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12条。
[49] 马新彦:《论民法对合同行政批准的立法态度》,《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266-268页;缪因知:《国有股转让协议批准要求对合同效力之影响》,《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第1376页以下。作者认为,一般国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需要批准才可生效,另外国企出资人与国资监督管理机构应区别对待,前者所享有的是“作为国有出资人、间接/终极持有人在财产处分性质上的决定权”,而无权以国家机构的身份,对非直接下级企业的国资转让行使监督权(第1382页)。
[5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92页;高圣平:《担保法前沿问题与判解研究》(第5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5页;吴光荣:《担保法精讲——体系解说与实务解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71-72页。
[51] Larenz, BGB AT, § 23 IV, S. 471-476.
[52] 钟嘉儿:《相对不生效力制度的新生与实际运用》,《私法》2022年第1期,第92页以下(如第107页)。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正如钟嘉儿所指出的,仅仅说相对不生效系相对第三“人”无效不够严谨,应当进一步明确,有关不生效实际上是相对于第三人的权利内容而言。例如,如果A是所有权人,B是预告登记的抵押权人,C是第二买受人,则有关“相对不生效”的正确描述是:有关A与C的所有权变动在B所享有的抵押权范围内不发生效力,而非完全不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效力。
[53] 如前所述,“无效”本是一个模糊的法律概念,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相对”二字,更使这一概念难以准确把握。例如,曾有不少观点认为,可撤销合同属于相对无效合同(见李永军著:《合同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第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这可能是不严谨的,一方面,因意思瑕疵而可撤销的合同,严格来说并不是此种“可撤销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而不过是法律在当事人有意思瑕疵的情况下额外赋予行为人不受其表示出来的意思拘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可撤销合同在撤销权行使之前(或撤销除斥期间经过后)也并非无效合同,而撤销权行使之后即自始无效,也并不存在“相对无效”的效力状态。见高莹:《论合同的相对无效》,北京大学2020年硕士毕业论文,第10页。即使存在所谓的撤销后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情形,也是有关合同相对于第三人有效,而非无效。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87-388页。理论上,还有学者认为债权人让与未通知债务人的,对债务人不生效力,也属于相对无效(前引杨代雄书,第388-389页),这是值得商榷的:就债权让与行为而言,在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让与合意之时,即发生效力,在法律未赋予第三人权利(如优先受让权)的情况下,并不存在该让与行为相对于第三人不生效力的情况,至于受让人在未通知的情况下不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只是债权实现的步骤未完成而导致受让人暂时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但这并不影响让与行为的效力,因此还不能说是债权让与“相对无效”。
[54] 茅少伟:《恶意串通、债权人撤销权及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当代法学》2018年第2期,第23页。
[55]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2017)青2801民初281号判决书(本案同时涉及股份购买人迟延付款的行为,该行为是否构成抗辩权的有效行使,判决中未做进一步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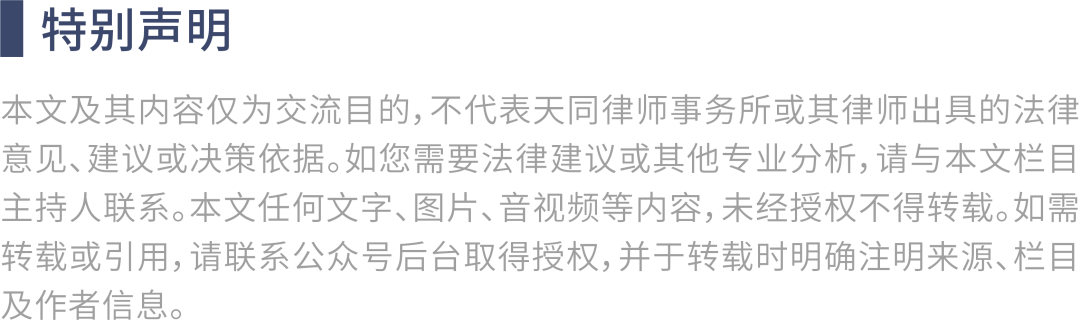
“合同实务”栏目由廖鸿程律师、吴陶钧律师主持,战斗在合同实务栏目一线的天同律师们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合同实务的相关思考。如您对“合同实务”栏目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查看往期文章,请点击以下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