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写在前面:
寻找 天同码现已重启编辑,如您所在团队是2019年至今公报案例的代理团队,希望您能联系我们,我们会将对应的天同码笔记标记并公开署名为您的团队作品。
打招呼时,请备注“公报案例律师”,并指明具体的代理案件。 |
公司卷 - 解散清算 - 公司清算 - 怠于清算
公司卷 - 股权转让 - 交易安排 - 股份代持
4.7.2
2024
隐名股东内部股转未造成损失,不得主张清算责任
—— 隐名股东股转行为只是代持人向隐名股东返还股权的行为,并未导致代持人和债权人任何损失,不得向股东主张未及时清算的赔偿责任
标签:| 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 | 破产清算 | 代持协议
案情简介:云公司股东为中公司和逯公司,因经营管理困难且两方股东对公司应否清算不能达成一致,被强制清算,京公司是云公司的债权人。云公司曾持有东公司若干股权,在强制清算前被无偿转让给第三方。清算组认为股权实际出资人为但某,云公司系代但某持有东公司的股权,该股权无偿转让系依但某的指令而为。现京公司主张,因中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对云公司组织清算,导致云公司持有的东公司股权被转让流失,要求中公司在东公司股权价值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① 在云公司成立清算组之前,其持有的东公司股权已被转让。难以认定云公司的股权转让系因中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清算所导致。② 根据章程约定,确定清算组成员对公司清算,系云公司股东会行使的职权,清算义务人系全体股东。在逯公司不配合的情况下,仅有中公司一方股东,无法单独成立清算组完成清算程序。③ 在清算过程中,云公司管理人未发现转让东公司股权给云公司造成损失,故京公司主张中公司未及时清算导致云公司财产流失,理据不足。
实务要点:代持人向隐名股东返还代持股权的行为,并未导致代持人和债权人任何损失,不得向股东主张未及时清算的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深圳中院(2024)粤 03 民终 3598 号
主要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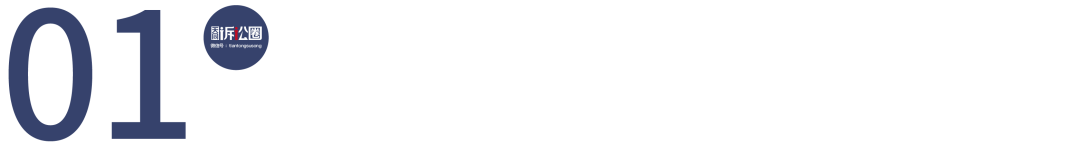
中公司从未经营管理云公司,派驻至云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周某也早已离职,因此中公司从未控制云公司
一方面,云公司《章程》约定,禄公司认缴出资2000万元,实缴出资2000万元,中公司认缴出资3000万元,实缴出资0万元。第九条约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自云公司成立至案涉股转行为发生时,中公司从未对云公司实缴出资,而是直至另案强制执行,通过对云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履行出资义务。因此,中公司客观上就没有经营管理云公司的权限,更无法通过股东地位对云公司实施控制。
另一方面,中公司虽曾派出周某到云公司,但如前述,中公司未曾履行出资义务,因此事实上周某也从未以董事长或者法代身份在云公司行事,且周某早已于2012年离职并入职其他公司,不可能再以中公司派出人员身份继续在云公司工作,此后中公司未再向云公司派出任何人员。
综上,中公司在云公司既不享有股东权利,也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更无法“控制”云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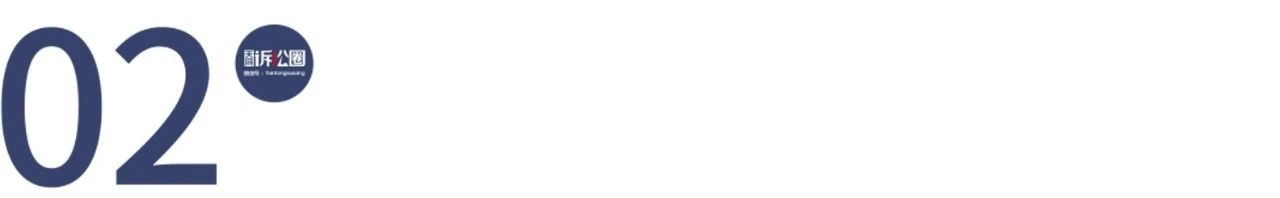
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禄公司和何某。案涉东公司股权转让也是在何某控制下所为,与中公司无关
2.1 云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以及内部会计凭证均显示,何某实际经营管理云公司
云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中,何某均代表云公司在合同中签字,并加盖云公司的公章。典型如云公司与京公司签订的系列合同。云南昆仑公司的内部会计凭证显示,何某一直以董事长名义签署财务审批文件。
2.2 何某系云公司实际控制人这一事实已经刑事裁定书查明和认定
刑事裁定书查明,禄公司和何某实际控制云公司、何某负责云公司的日常经营。且在中公司和禄公司达成解散云公司的初步共识后,何某故意隐瞒中公司已决定解散云公司、云公司已不具备以相关公司名义履约能力的事实,2012年底之后仍伪造中公司原派驻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某的签名,私自使用已经与中公司协议共管的公章。
何某利用控制云公司的便利,在未经中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共管的公章,在云公司被判决解散后操纵云公司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公司根本不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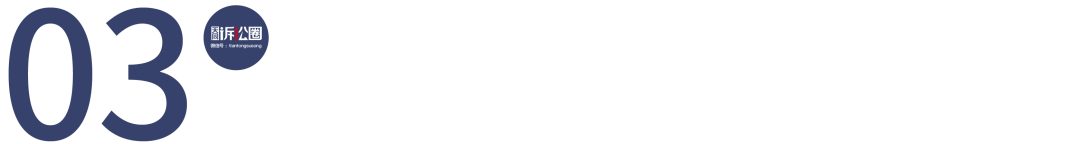
云公司出现解散事由的时点并非2012年5月,中公司在彼时没有任何解散清算云公司的义务
首先,本案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的“股东会决议解散”情形,原二审判决错误认定云公司在2011年8月形成公司解散决议并在2012年5月再次形成了公司解散决议。
就2011年8月决议:云公司当日系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股东会决议,并未决议解散公司。
就2012年5月专题会议纪要:刑事裁定书查明,云公司双方股东在2012年5月的《会议纪要》只是达成了解散的初步共识。《会议纪要》形成后,中公司授权云公司两次向禄公司发函,均明确要求禄公司尽快配合处理公司解散事宜,包括“形成股东会决议”。
退一步说,即使认定双方股东在2012年5月达成了解散合意,该合意也已经通过2012年10月决议变更:2012年10月双方已经合意中公司对外转让云公司股权,不再解散云公司;云公司办理更名,等。既然云公司已不具备解散和清算的基础,中公司当然也不具有解散清算义务。
后禄公司拒不配合办理公司更名、资产审计事宜,双方产生争议,已经不属于股东自行解散的范畴而应纳入法院判决解散范畴,中公司也因此在2013年4月提起了公司解散之诉。因此,云公司解散事由出现时点应是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即2014年9月,彼时中公司方负有成立清算组的义务。而早在8月20日禄公司和何某就已利用控制云公司之便,私自转让了东公司股权,在前发生的股转行为与中公司在后是否成立清算组之间毫无因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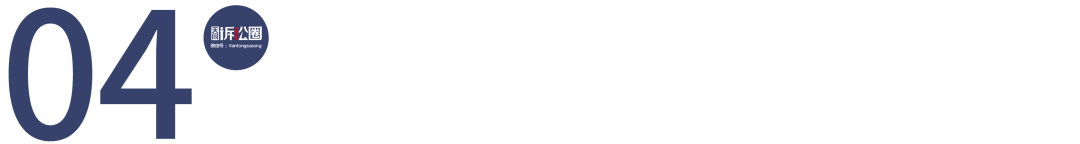
中公司虽未控制云公司,但一直在持续积极地推进云公司解散清算事宜,已经完全履行身为工商登记股东的法定义务,不存在任何懈怠的事实或者主观故意
一方面,在云公司被判决解散前,如上所述,在2012年5月《会议纪要》后,云公司曾代表中公司分别于2012年9月、10月发函催告禄公司尽快推进云公司的解散清算事宜。2012年10月双方形成新的股东会决议后,11月云公司还发函催告禄公司尽快按照10月决议内容开展云公司的资产审计、更名工作,否则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解散清算云公司。在禄公司拒不配合推进相关工作、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中公司于2013年4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散云公司。
另一方面,中公司收到解散公司的一二审判决后,当即联系媒体主动登报公布了解散之诉的判决结果,主观上未怠于解散清算云公司,更谈不上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恶意。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据此,云公司的全体股东均是清算义务人,即需全体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确定清算组成员、开展清算工作,而非单一股东可单独决定或完成的事项;且云公司章程第七条也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10)对公司清算作出决议……”。由于无法联系上禄公司或何某,根本无法形成指定清算组成员的股东会决议,且云公司一直系禄公司和何某实际经营管理,中公司客观上无法单独开展清算工作。京公司主张“中公司作为股东之一,即使联系不上禄公司,也可单独成立清算组,开展清算工作”,显然违背章程规定和法律意旨,更是完全未考虑云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控制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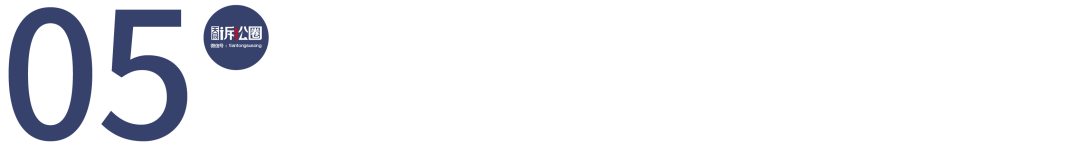
京公司主张中公司未在解散公司判决生效后的15天内成立清算组与东公司股权流失具有因果关系,与事实不符
首先,如前述,东公司股权的转让行为是何某控制云公司实施,与中公司无关。且因无法联系上何某及禄公司,2014年9月前无法成立清算组,中公司在此情况下也及时申请了司法强制清算,中公司并未故意拖延清算,不构成“未在法定15天内成立清算组”。
其次,京公司再审中主张,由于清算组成立过晚,受让东公司股权的案外公司已经注销,导致无法再撤销东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自清算组成立后,且知道或应当知道股转事实后才开始起算,并不会因清算组的成立时间而受到不利影响。而无论是中公司、还是清算组,都是在京公司2015年起诉要求中公司承担清算责任时,才知晓股转事实。
再次,股权受让方案外公司在2015年6月被注销,而早在注销前的2014年10月,中公司就已经申请强制清算,至于法院在强制清算申请后近三年才指定清算组,与中公司无任何关系;且即使案外公司被注销,清算组或者京公司也可向其股东等主张责任,而不存在京公司所谓的“注销后就无处索赔”的困境。
最后,清算组综合款项支付、代持各方当事人的说明、东公司另一股东的确认、但某未申报债权等证据事实,认定“存在代持关系”而“非借款”,进而未向但某追索股转款或撤销股转行为。京公司起诉要求中公司承担清算责任时,也已经知晓案涉无偿股转情况,其如认为案涉股转并非返还代持股权而是云公司转移财产的行为,完全可以自行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且若京公司认为清算组判断有误,也可以督促清算组行使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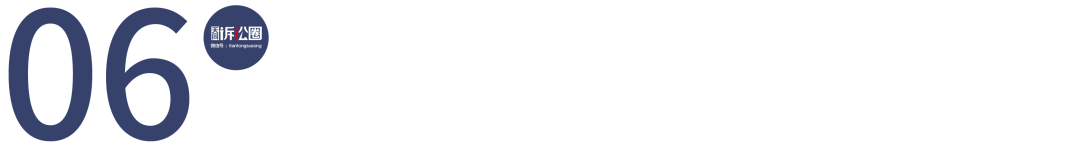
目标公司东公司、代持人云公司、被代持人(隐名股东)但某均认可云公司系为但某代持东公司股权,但某事实上也一直实际经营管理东公司。案涉股转行为只是代持人云公司向隐名股东但某返还股权的行为,并未导致云公司和债权人任何损失
无论是隐名股东但某、代持人云公司,还是目标公司东公司,都知晓并且认可4250万元借款对应的东公司股权系云公司替但某代持,借款只是各方达成的表面合意,不足以否定各方关于代持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
事实上,但某也一直实际经营管理东公司,行使隐名股东权利:
其一,在东公司成立前,但某就已经要求云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授权委托,实际取得东公司的控制权,以行使隐名股东权利。
其二,在筹备成立东公司过程中,但某代表东公司签订租房合同。在成立当日,东公司就作出《董事会决议》,聘任但某担任总经理,由此可见,但某在东公司成立之始直至案涉股权变更登记前,始终实际经营管理东公司。
其三,在东公司股权自云公司名下变更登记至案外公司名下后,案外公司又作出决议委派但某为东公司董事长兼
法定代表人;在东公司股权自案外公司变更登记至程某名下后,程某继续指派但某为东公司董事长。
综上,无论东公司股权是登记在云公司名下,还是变更登记至案外公司名下、乃至再变更至程某名下,但某都始终实际经营管理东公司,行使其作为东公司隐名股东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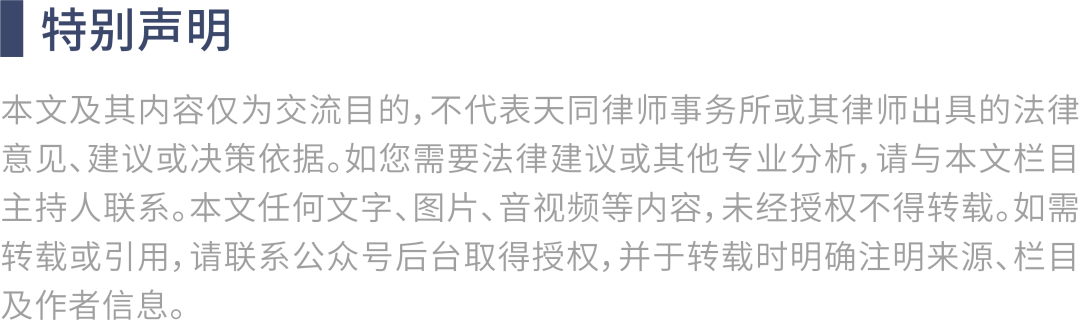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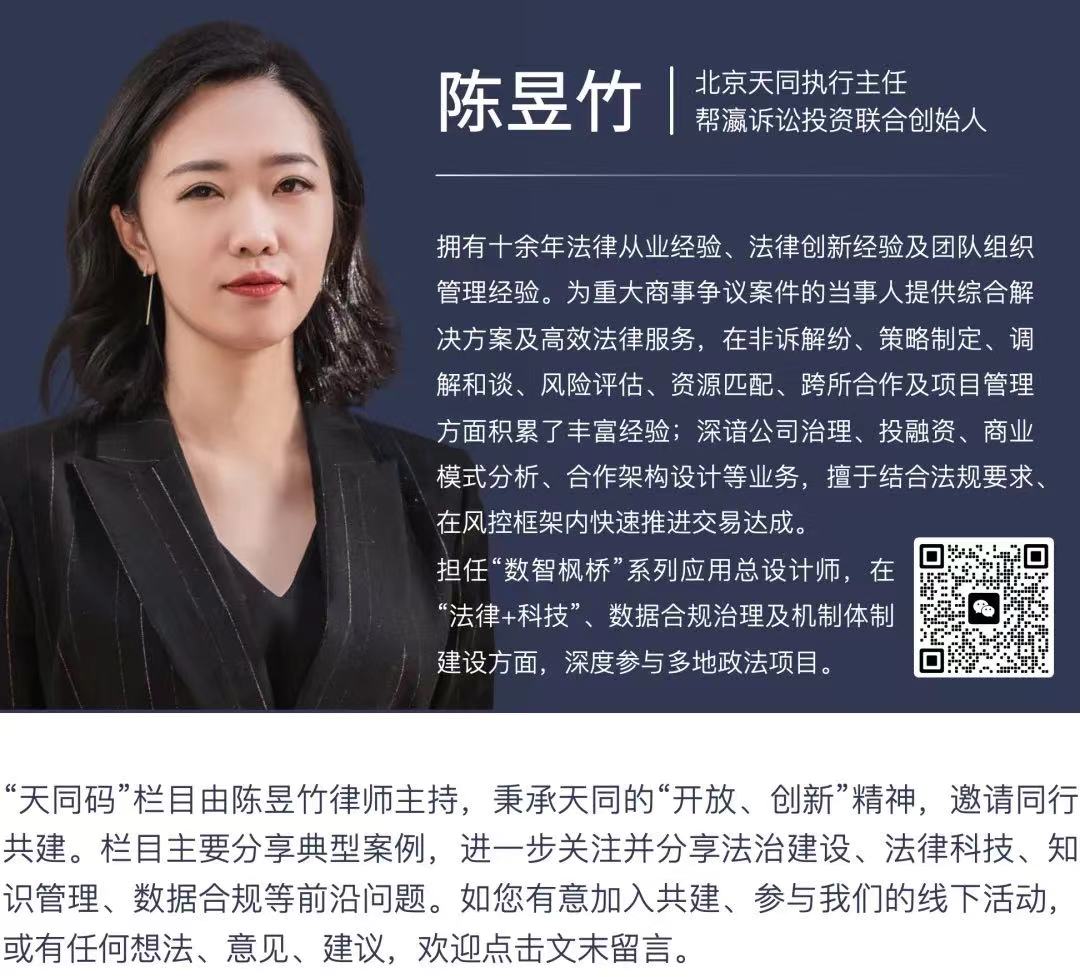

查看往期文章,请点击以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