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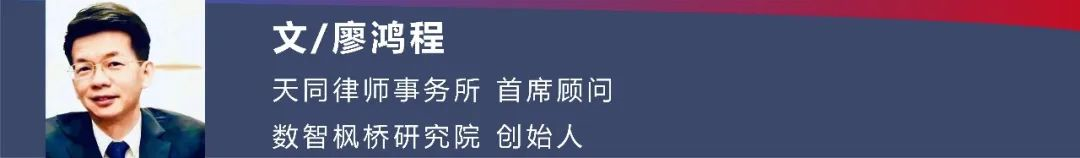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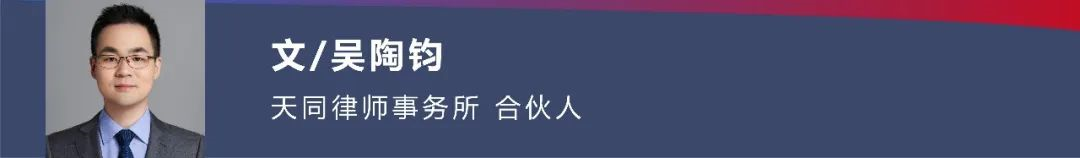
公司工作人员超越权限代理公司签署保证合同是实践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形,对此,公司稍有不慎将面临无辜承担保证责任或赔偿责任的风险。本文中,笔者将结合近期代理的一起保证合同纠纷,就公司如何科学应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希望给遇到类似问题的企业家、同仁提供一点参考。
【案情简介】
某公司系一家生产水泥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执行董事行使董事会职权。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章程未作规定。
2022年,公司的客户张三(下称“债务人”)因资金短缺向李四(下称“债权人”)借款1000万元。对于该借款,公司经营部经理(下称“公司工作人员或经营部经理”)未经公司股东会及执行董事同意,擅自代理公司为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保证合同上签字)。经法院委托鉴定,保证合同上公司的印章与公司真实的印章不同。
因债务人到期未能偿还借款,债权人起诉请求债务人偿还借款,并请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件分析】
题述案件涉及公司工作人员代理公司签署保证合同,且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与公司真实印章不同的情形,对此,就保证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以及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4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2条、第21条,应根据代理规则确定。具体而言,如果公司工作人员构成有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保证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如保证合同没有其他无效情形,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公司工作人员构成越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保证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至于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则应根据公司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具有什么程度的过错确定。在该分析思路下,笔者认为公司可以考虑从如下三个方面应对债权人的起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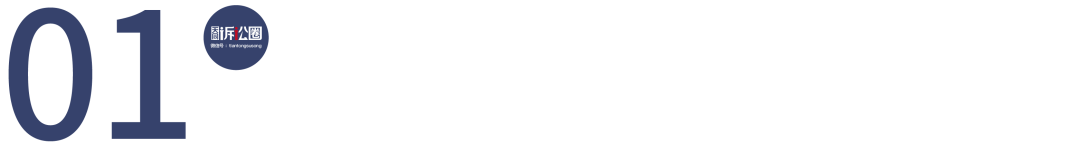
公司工作人员无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其签署保证合同未经公司有权机关同意,构成越权代理。
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1条第2款第1项及第2项,公司工作人员签订合同所涉事项属于依法应由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事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超越其职权范围。
根据《公司法》第16条(新《公司法》第1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下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九民纪要》第17条,公司为他人提供非关联担保,除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的情形外,只有章程规定的股东会或董事会才有权决定。笔者认为,如果章程没有规定,有且只有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才有权决定。其中,对于没有董事会、仅有执行董事的公司,执行董事代行董事会职权,此类公司有且只有股东会或执行董事才有权决定。 [1]
题述案件中,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执行董事行使董事会职权。并且,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章程未作规定。因此,题设公司有且只有股东会或执行董事才有权决定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工作人员未经有权机关同意代理公司签署保证合同,构成越权代理。
类似案件中,公司有权机关是否曾以出具决议或者其他书面文件的方式同意公司工作人员对外提供担保,比较容易查明。比较难查明的是,公司有权机关是否曾以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比如执行董事控制公司公章,其虽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同意案涉担保,但其以在案涉合同中加盖公章的形式同意案涉担保)同意公司工作人员对外提供担保。
笔者在题述案件中就曾遇到类似问题。该案中,债权人谎称其亲眼看到公司执行董事要求经营部经理在案涉保证合同中签字,即执行董事口头同意公司经营部经理签署案涉保证合同。另外,在诉讼中债权人还申请了已经从公司离职的经营部经理出庭作证,公司经营部经理亦在庭审中谎称,案涉担保经过了公司执行董事同意其才在保证合同中签字。
对于前述问题,笔者在案件代理中首先向法院陈述了案件的真实情况,即公司执行董事在债权人提起诉讼并收到起诉状后才知道经营部经理代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宜,在此之前,公司经营部经理从未向其请示过该事项,其更未授权或同意经营部经理在案涉保证合同上签字。同时,笔者主要从以下角度论证案涉担保没有经过公司执行董事同意:
第一,经法院委托鉴定,案涉保证合同中的公司公章与公司真实印章不同。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执行董事同意该担保,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印章应该是公司的真章而非假章。从该事实来看,案涉担保显然未经执行董事同意。
第二,该案历经原一审、原二审、再审审查、再审审理、重一审等程序,笔者于再审审查程序介入,每次程序中法院均会询问债权人及公司经营部经理案涉保证合同签署的过程,笔者发现,债权人及公司经营部经理的说法有多处重大矛盾。比如,经营部经理称,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债权人不在现场;债权人则称,其在现场,其亲眼目睹了执行董事要求经营部经理签署保证合同的过程。又如,经营部经理称,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债务人不在现场;债权人则称,债务人在现场。再如,经营部经理称案涉保证合同在A地签订;债权人则称,案涉保证合同在B地签订。
上述事项并非保证合同签署的细枝末节,而是事情的核心。对于如此重大的事项,如果是出于亲身经历,经营部经理的陈述与债权人的陈述不可能出现数量如此多的、如此明显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说法恰恰可以说明,所谓“执行董事同意案涉担保”完全是经营部经理和债权人虚构、杜撰、编造的。
第三,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债务人尚欠付保证人约800万元货款,此时债务人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此时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实际上就是为债务人承担债务。从常理来看,公司执行董事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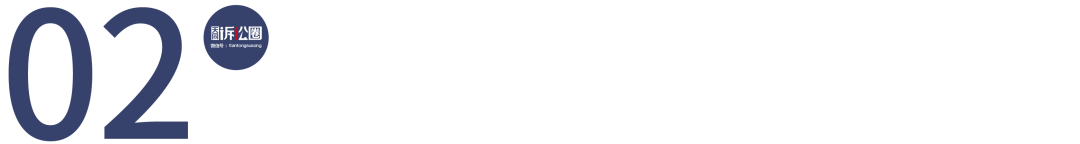
债权人在接受担保时未对案涉担保是否经过公司有权机关同意进行审查,债权人不构成善意,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保证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一)公司可主张,债权人未尽审查义务,其系恶意。
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1条第1款、《民法典》第172条,参照《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第1款、《九民纪要》第17条,公司工作人员构成越权代理时,保证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应根据案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确定。具体而言,如果债权人系善意,则案件构成表见代理,保证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如果债权人系恶意的,则案件不构成表见代理,保证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28条第1款第2项,对于公司工作人员越权代理的情形,债权人的善意,是指债权人不知道公司工作人员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就善意的认定标准,该条并未规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第3款规定,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情形,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笔者认为,公司工作人员越权代理时债权人是否善意的认定可以参照该条规定确定,即如果债权人已对公司有权机关的同意进行了合理审查,则其为善意;反之,则其为恶意。当然,公司工作人员的代理权限显然小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债权人对公司工作人员代理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应负有更高程度的审查义务。
综上,就题述案件,公司可主张债权人未对案涉担保是否经公司有权机关的同意进行合理审查,其系恶意,案件不构成表见代理,保证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二)如果债权人善意与否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公司可主张,债权人应对自己已履行合理审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根据《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28条第2款,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发生争议的,债权人应当就案件存在代理权的外观承担举证责任。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中,代理权的外观应指案涉担保经过公司有权机关同意。因此,债权人应就案涉担保经过了公司有权机关同意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债权人应就其已经合理审查案涉担保经过了公司有权机关同意承担举证责任。
再者,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提供担保的情形,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第3款“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以及《九民纪要》第18条第1款“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债权人应对其履行了合理审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最高法院在对《<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中也持此观点。[2]举重以明轻,对于公司工作人员越权提供担保的情形,债权人也应对其履行了合理审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综上,类似案件中,如果债权人善意与否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公司可以主张,债权人对自己已履行了合理审查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2款,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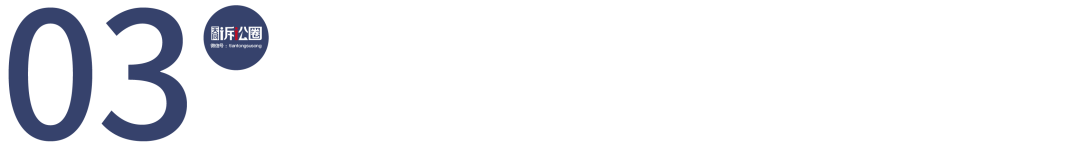
债权人与代理人恶意串通制造了公司提供担保的假象,债权人具有明显过错,公司没有过错,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在公司工作人员构成越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时,债权人有过错而担保人无过错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和债权人均有过错的,公司应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公司有过错而债权人没有过错的,公司应就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1条第1款规定,在公司工作人员构成越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时,如果公司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第1款第2项规定,在法定代表人构成越权代表且不构成表见代表时,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参照适用该解释第17条的有关规定。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1条第1款并参照《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第1款第2项、第17条第1款,在公司工作人员构成越权代理但不构成表见代理时,债权人有过错而担保人无过错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和债权人均有过错的,公司应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公司有过错而债权人没有过错的,公司应就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二)债权人与公司工作人员恶意串通签订担保合同属于债权人有过错而公司无过错的典型情形,此时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债权人明知公司工作人员伪造或变造决议属于债权人与公司工作人员恶意串通的情形,此时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债权人明知公司工作人员超越权限订立合同不属于债权人与公司工作人员恶意串通的情形,此时公司仍应根据其过错承担责任。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3条第1款规定,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公司名义订立合同,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显然,公司工作人员(代理人)与债权人(相对人)恶意串通签订担保合同,属于债权人有过错而担保人无过错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就债权人有过错而担保人无过错的认定,最高法院的观点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出台前后发生了一定变化。
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出台前,《九民纪要》第20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时,“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参照该条,如果债权人明知公司工作人员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或者明知有权机关的同意文件系伪造或变造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出台后,最高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明确,债权人明知公司工作人员伪造或变造决议的,属于债权人与公司工作人员恶意串通的情形,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3]另外,最高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也持此观点。[4]因此,在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变造的情形下,最高法院保持和《九民纪要》一致的立场。但是,最高法院摒弃了公司在债权人明知公司工作人员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时不承担责任的观点,其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明确,“只要法定代表人不能提供适格决议,相对人应该明知其超越权限提供担保,但这仅表明相对人是恶意的,并不能进一步推导出公司自身无过错。而只要公司自身存在过错,其就应承担责任,故公司不能仅以相对人明知超越权限为由主张免责”。 [5]
(三)公司可根据《民法典合同编解释》第23条第2款并结合案情主张,债权人与公司工作人员恶意串通签订了担保合同,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难以证明案件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公司则可以尽可能主张债权人存在过错而公司不存在过错,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就题设案件,笔者结合案情从以下方面协助公司减轻或免除责任:
第一,公司合理怀疑债权人与公司工作人员恶意串通制造了公司提供担保的假象,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而言,公司工作人员与债权人关系密切,比如二人是同村人、公司工作人员是债权人的表舅、公司工作人员经常将闲散资金放置于债权人处对外放贷获得高额收益、公司工作人员也经常向债权人介绍借款人。甚至,案涉保证合同中公司的印章是假章,公司工作人员也曾帮助债权人查找公司的内部资料作为债权人的证据。根据以上事实,公司合理怀疑债权人与公司工作人员恶意串通制造了公司提供担保的假象。
第二,本案债权人经常从事借贷担保业务,其对公司对外担保规则极其熟悉,其明知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会导致保证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同时,债权人与保证人在同一个城市,且双方有过往来,债权人审查案涉担保是否经公司有权机关同意非常容易。在此情形下,债权人仍然未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查,债权人具有明显过错。
第三,公司具有严格的印章管理制度,案涉保证合同上的印章系他人伪造,公司对于案涉保证合同无效没有过错,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具体而言,公司于成立时即出台严格的印章管理制度,公司所有文件用印均需由执行董事审批并由出纳加盖。另外,经法院委托鉴定,案涉保证合同中的公章也系他人伪造并加盖。因此,公司关于公章的管理和使用规范,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注释:
[1] 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87页。
[2] 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86页。
[3] 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38页。
[4] 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74页。
[5] 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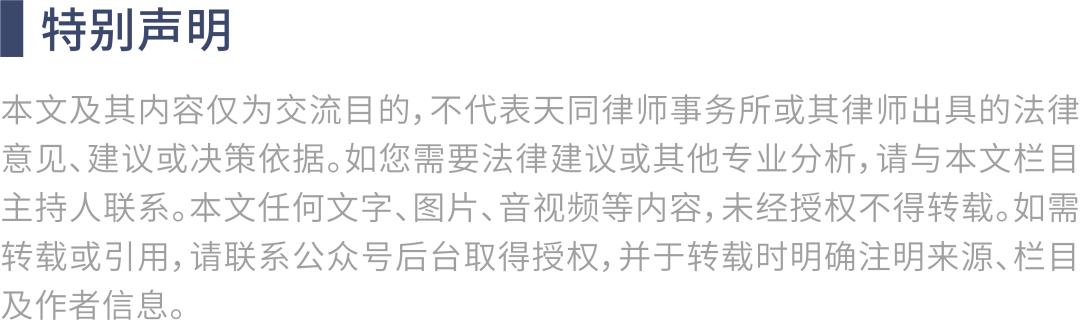
“合同实务”栏目由廖鸿程律师、吴陶钧律师主持,战斗在合同实务栏目一线的天同律师们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合同实务的相关思考。如您对“合同实务”栏目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查看往期文章,请点击以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