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张会会、李扬、宋攀,天同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
引入:今年以来,我们收到了多起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证券公司免责的胜诉判决,在其中一起案件判决书中,法院采纳了我们关于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属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人的观点并判决驳回投资者对证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下称“本案”)。近年来,我们也注意到证券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被卷入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情况愈发常见,但司法实践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法律定位等核心问题却远未形成共识。基于在证券类争议解决领域的长期耕耘,我们在厘清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职责范围及与其他各方主体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拟以本文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是否属于证券虚假陈述案件适格被告的问题进行重点讨论,以求对受托管理人相关法律共识的形成有所裨益。[1]

司法实践概述
通过梳理司法实践现状,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债券受托管理人责任问题并未形成统一裁判思路,在本案之前总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三种:(1)如“超日债案”[2]及“XZ债案”[3]中,法院和仲裁委均采取违约责任分析路径,分别以投资者“没有证据证明其该项损失与受托管理人的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无法举证说明第三被申请人(受托管理人)就募集资金用途进行监管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为由认定受托管理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如“HY债案”中,法院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一并处理涉及的受托管理责任争议,但以投资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XX证券公司作为受托管理人时未勤勉尽责”为由未支持投资者对受托管理人的责任主张,即采用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归责原则,可见法院在处理时仍然区分了证券公司作为承销机构与受托管理人的不同身份,进而适用了不同的裁判规则;(3)如“正源债案”中,法院认为投资者与受托管理人纠纷属于委托合同纠纷,而投资者与发行人系债券融资法律关系,两项争议的诉讼标的并不相同,被告亦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且该院对前项争议不具有管辖权,据此直接驳回投资者对受托管理人的起诉。[4]
整体来看,司法实践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职责范围及其在证券交易中与各方形成的法律关系等问题均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尤其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是否属于证券虚假陈述案件适格被告的问题亟需明确。虽然目前尚未检索到判决债券受托管理人承担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案例,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以受托管理人未勤勉尽责为由要求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连带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因此,有必要厘清法律规则并明确上述问题,从源头阻断受托管理人被不当地纳入虚假陈述案件的实体审理,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也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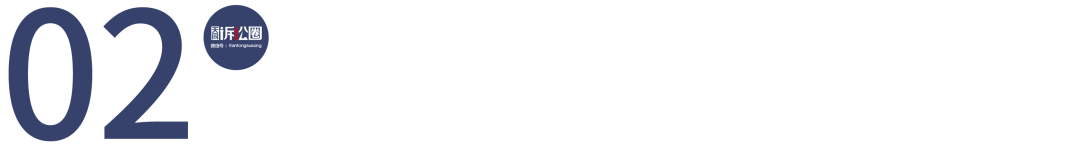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法律定位
(一)受托管理人概念及特征的厘清
债券受托管理制度的直接法律规定可参考《证券法》(2019年)[5] 第92条,该条明确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由发行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并订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受托管理人应勤勉尽责,公正履行受托管理职责,不得损害债券持有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该条的条文解读指出,债券受托管理制度是“是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设立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的机构”。[6] 结合上述条文以及业务实践,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为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由发行人委托的在债券存续期间履行法律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约定职责的机构。
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归纳受托管理人的履职特点,即履职目的的偏向性、履职范围的迟滞性及有限性、履职身份的独立性。其中,偏向性是指即使受托管理协议由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但其设立目的却在于维护债券持有人而非发行人的利益。迟滞性及有限性一方面指受托管理人主要在投资者已经成为债券持有人后的债券存续期间代理债券持有人履行职责,而非在债券发行期间确保投资信息的准确、真实及完整披露,另一方面指受托管理人的职责主要落脚于对发行人相关情况的“关注”“跟踪”“监督”,对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督导”,[7] 显著不同于承销机构的(事前)尽职调查职责。而所谓独立性,可以从两个维度把握:其一,身份独立性。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发行人、承销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及受托管理人均为并列的、各自独立的主体。发行人需要配合承销机构及受托管理人的工作,承销机构与受托管理人分别在各自的履职阶段和职责范围内履行相关义务。其二,制度独立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下称“《债券座谈会纪要》”)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为保障债券持有人和债券投资者的利益,现行法律和监管规则在信息披露责任之外,还作出了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制度安排。”
结合对上述特点的归纳可知,受托管理制度本身独立于、区别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受托管理人亦独立于承销机构及证券服务机构,与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二)受托管理人相关法律关系的梳理
在债券交易中,各交易环节所涉主体较多,法律关系也较为复杂,为更好理解受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有必要界定受托管理人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简单来说,债券交易中主要的角色包括发行人、承销机构、债券持有人及受托管理人。以受托管理人作为观察点,其与其他三个主体的关系分别是:
(1)受托管理人由发行人委托,与发行人分别作为合同双方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但受托管理人并不对发行人负责,仅需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履行相关职责且并非为了发行人的利益,而发行人则需要配合受托管理人的工作。
(2)承销机构和受托管理人在实践中常常为同一主体,但两者在履职期间、职责范围上存在明确的界限。就履职期间而言,《公司债券承销业务规范》等规定明确,承销机构系在债券发行前和发行阶段履行职责,债券发行结束后由受托管理人依法持续履行受托管理职责。就职责范围而言,承销机构作为“看门人”之一,其负有在证券发行之前对证券发行文件按照规定进行核查的职责。而对于受托管理人,其制度设计缘起于债券持有人集体行动难的困境,如前所述,其主要承担着代表债券持有人监督发行人的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利益。相应地,募集说明书“声明”部分关于承销机构和受托管理人承担责任的承诺完全不同:承销机构一般承诺,如果募集说明书及摘要因存在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承销机构则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而受托管理人一般承诺,如果在受托管理期间因未按照相关规定、约定履行职责的行为,给债券持有人造成损失,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债券持有人与受托管理人之间虽未直接签订合同,但募集说明书中一般会约定“投资者认购、交易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甚至明确约定“受托管理人应作为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的代理人”,由此通常认为债券持有人与受托管理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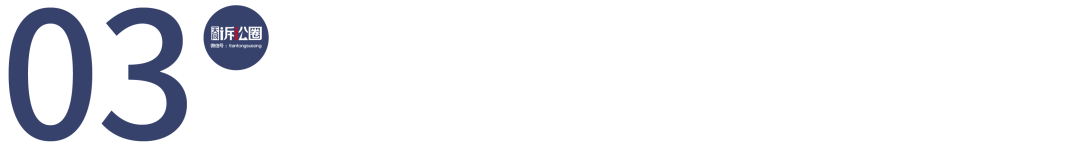
债券受托管理人并非虚假陈述案件适格被告的分析
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债券座谈会纪要》答记者问中已经明确表示,“现行法律和监管规则在信息披露责任之外,还作出了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制度安排。”可见,受托管理制度是排除于信息披露制度之外的,受托管理人责任独立于、区分于信息披露责任(虚假陈述责任),受托管理人也就不属于虚假陈述案件适格被告。
此外,目前要求受托管理人承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不论是基于证券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失属于纯粹经济利益损失的原因,还是基于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投资者对中介机构主张适用过错推定规则的原因,抑或是连带责任需明确约定或规定的原因,投资者要求受托管理人承担证券虚假陈述连带赔偿责任都应当提供《证券法》上的依据。而实践中认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是虚假陈述案件适格被告的理由主要有两类:一是认为受托管理人属于《证券法》第85条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是认为受托管理人属于《证券法》第163条规定的证券服务机构。基于此,在前述正面分析了受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职责范围以及制度性质之后,下文将进一步结合法律法规逐一针对性地反驳这两个理由,以确证债券受托管理人并非虚假陈述案件的适格被告。
(一)从法律地位来看,受托管理人并非《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也并非《证券法》规定的证券服务机构
1.受托管理人不是《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证券法》第85条首次明确“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虚假陈述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表述也来源于此。但是,从这一条文本身即可看出,该条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是指对自己实施的虚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投资者损失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而《债券座谈会纪要》第25条明确规定受托管理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未勤勉尽责公正履行受托管理职责。这表明受托管理人对债券持有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的无过错责任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
而且,《证券法》第85条规定的承担虚假陈述责任的主体包括两类,第一类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自己实施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第二类是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内部人以及保荐人、承销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对发行人实施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过错推定的连带赔偿责任。可见,《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包括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荐人、承销机构,举重以明轻,自然更加不可能包括受托管理人。
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投资者是基于发行人实施的虚假陈述行为要求存在过错的受托管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么该主张将与受托管理人属于《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张直接矛盾,因为两项主张涉及的虚假陈述行为实施主体、归责原则均截然不同。
2.受托管理人不是《证券法》规定的证券服务机构
根据《证券法》第160条、第163条的规定可知,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的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并不包括受托管理人。《债券座谈会纪要》第3条亦明确债券服务机构不包括受托管理人,并在第六章“关于其他责任主体的责任”进一步规定,只有未履行核查把关责任的债券承销机构和债券服务机构才属于证券法规定的虚假陈述案件的适格被告,区分于受托管理人责任。
(二)从职责范围来看,受托管理人承担虚假陈述责任不符合责任义务一致原则
1.受托管理人不掌握发行人的第一手信息,不可能是《证券法》上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证券法》设置信息披露义务人并规定其承担无过错的虚假陈述责任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掌握应披露信息的第一手来源,如上市公司、发行人、特定情况下的大股东,是信息第一责任人。然而,受托管理人并非发行人的内部机构,并不掌握发行人的第一手信息。此外,结合前述归纳的受托管理人履职特点和职责范围,其亦不具备获知发行人第一手信息的相应权限。在此背景下,将受托管理人归属于《证券法》从严规制的第一责任主体显然违背立法目的,也不符合责任义务相一致原则。
此外,证监会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62条已经规定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属于该办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就《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信息披露由上市公司负责,交易对方并非证券法所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可见,“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狭义和广义的概念。不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均对《证券法》规定的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信息披露义务人采取了极高的认定标准,将受托管理人认定为《证券法》所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无疑不合理地扩大了受托管理人的责任边界。
2.受托管理人并无对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尽职调查之义务,也就不存在承担虚假陈述连带赔偿责任的基础
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主要是持续关注发行人和保证人资信情况和偿债保障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诉讼等。
可见,受托管理制度是投资者已经成为债券持有人以后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代理制度,完全不同于投资者成为债券持有人之前保障其基于真实、准确、完整信息作出投资决策的信息披露制度。相应地,受托管理人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和风险处置,而证券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尽职调查以后出具专业意见。也是基于此,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披露的信息负有尽职调查义务,也就不可能要求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受托管理人责任裁判思路的畅想
虽如前文梳理的司法实践有不同处理方法,但已经有法院在实践中逐步厘清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及职责范围等问题。
在我们近期收到的裁判文书中,原告明确其对受托管理人主张的是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之后,审理法院基本采纳了我们上述分析的核心观点,分别从受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和职责范围来明确受托管理人不应当承担虚假陈述赔偿责任。[8] 如果此类裁判观点可以成为司法实践共识,发行人、承销机构及受托管理人等各类主体才能更加明确自身在债券业务中的角色定位,债券受托管理制度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原有的制度作用。
注释:
[1] 本文讨论范围限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为论述之便,下称“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受托管理人”。
[2] 参见(2014)朝民(商)初字第27934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2020)沪仲案字第XXXX号裁决书。
[4] 参见(2021)辽02民初35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5]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证券法》均为《证券法》(2019年),以此作为分析对象的逻辑在于《证券法》(2014年)相较于《证券法》(2019年)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相关条款中并无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规定。
[6]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中国民法典适用大全·商事卷·证券法(一)》,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599页。
[7] 关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主要规定于《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
[8] 鉴于法律规定的时效性,案件和文章论述所依据的法律规定版本不同,如案件中适用2014年版《证券法》,而本文以2019年版《证券法》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