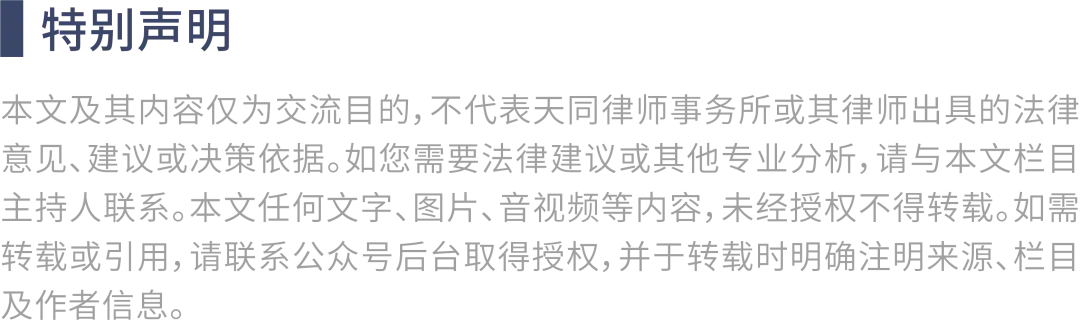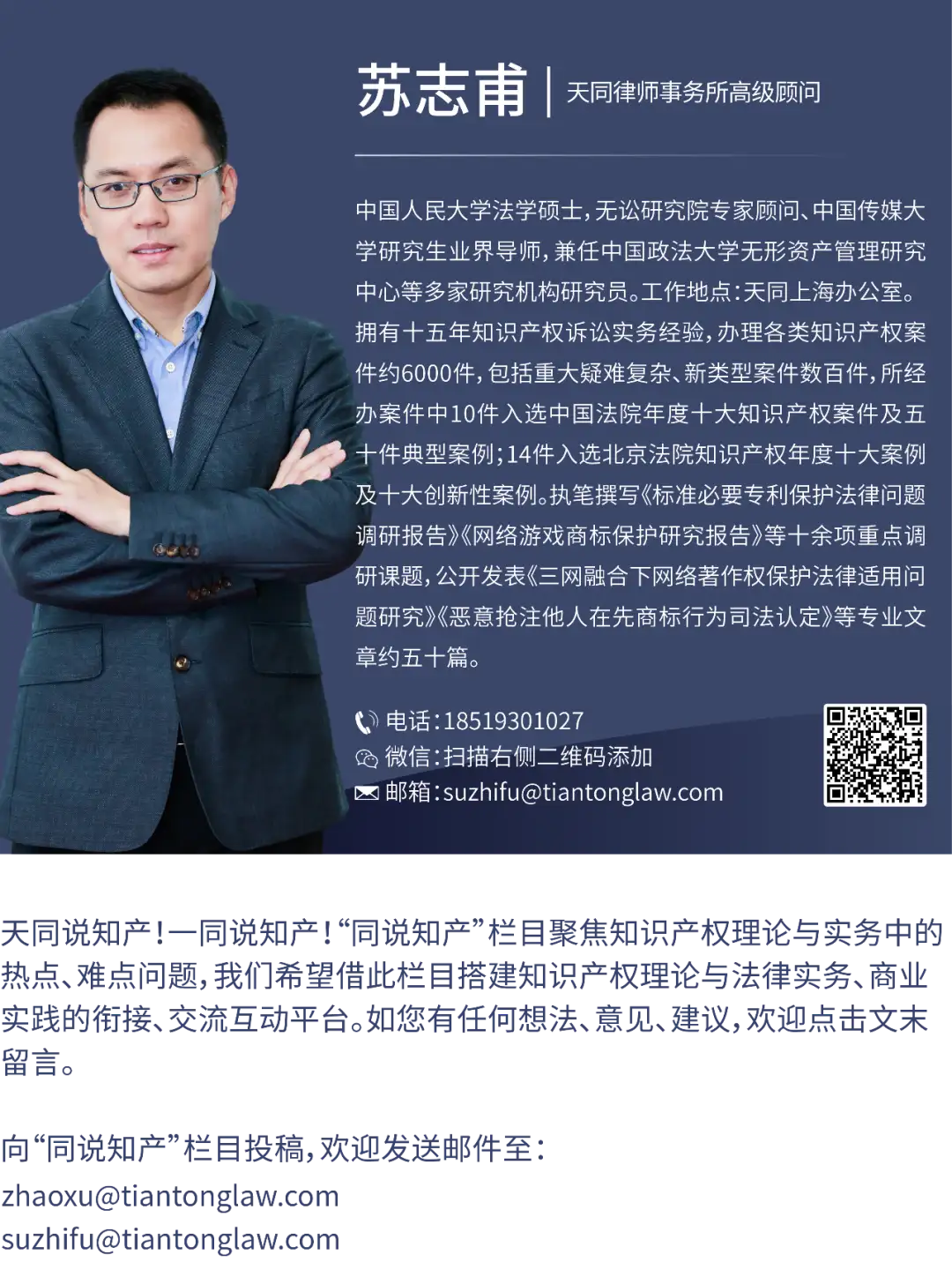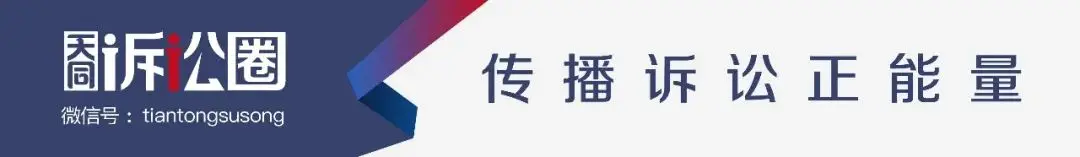
栏目主持人苏志甫按:知识产权滥用概念肇始于英美国家,经过判例法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国,随着知识产权受重视程度的提升以及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在知识产权价值日益凸显的同时,受利益驱动或出于市场竞争考量的滥用知识产权现象已经较为突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成为了当前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特刊发冯晓青教授的专题研究,以飨读者。

注:本文原载于《知识产权》2022年第10期,第3-38页,原文标题为《知识产权行使的正当性考量:知识产权滥用及其规制研究》,为微信推送便宜略有调整,如需引用请以纸质版论文为准。
目录:
一、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及沿革
(一)知识产权滥用之概念界定
(二)知识产权滥用的历史沿革
二、知识产权滥用的表现及其类型化
(一)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表现概述
(二)构成一般权利滥用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三)构成排除、限制竞争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及其认定
三、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立法、司法、行政及行业监管
(一)立法应对
(二)强化知识产权滥用的司法审查
(三)强化行政监管与行业协会监管
四、结 语
内容提要:知识产权滥用是知识产权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当行使权利,违背设立知识产权的制度宗旨和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政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知识产权滥用概念肇始于英美国家,经过判例法发展而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知识产权滥用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大体上分为构成一般权利滥用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和构成排除、限制竞争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其中,前者如属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内的限制、本可以正当使用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不适当延长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行为,与欺诈和掠夺在先权利有关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维权与诉讼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后者如利用强势地位签订垄断协议而排除、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行为。鉴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对于其他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损害性,需要对其予以法律规制。具体而言,包括以知识产权法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反垄断法规制以及强化知识产权滥用的司法审查等。
知识产权滥用,是近些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越来越关注的概念。对于这一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已成为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禁止滥用知识产权属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范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该行为在知识产权行使意义上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从国外来看,英美等国家较早就形成了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相关典型案件。就我国而言,随着知识产权在当代经济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人越来越重视利用该权利的垄断性特征独占市场,在利益驱动下,这也使得知识产权滥用的现象开始显现。由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对于社会公众乃至公共利益具有损害性,并且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宗旨背道而驰,如何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和制度实施层面规制这类行为,成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中的重要课题。22021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在“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部分,即明确提出要“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法”。本文即拟对这一问题,立足于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和历史沿革,以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等原理和规定为指引,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试图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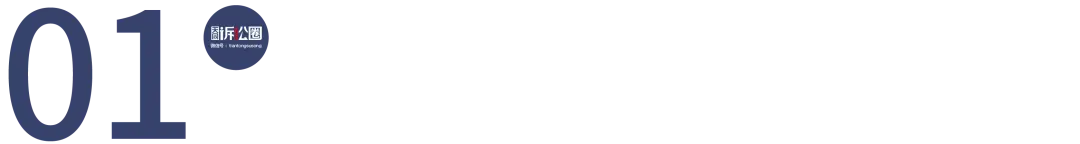
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及沿革
(一)知识产权滥用之概念界定
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的定义,我国《反垄断法》和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均未予以明确规定,国内外学术界则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定义。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滥用是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时超越了权利的界限,而构成损害他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1]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滥用是违背知识产权设定目的的不当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2]一种观点从违背知识产权制度的相关公共政策角度界定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内涵。[3]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将知识产权滥用做广义的理解,即不仅包括知识产权人不当行使自己的权利,还包括“行使”根本不存在的“知识产权”。[4]
对于上述主流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强调知识产权滥用是超越权利界限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法律逻辑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权利,但凡超越其权利边界,已经不存在知识产权,难以称得上权利滥用。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相似,解释了知识产权滥用的本质,即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违背了知识产权这一专有权利设置的目的或者违背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确实揭示了知识产权滥用的本质特征,符合知识产权法理学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认知。但是,从对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界定来说,仍显得过于抽象和概括,且难以与其他与知识产权侵权有关的行为相区别。因此,需要进行改造和优化。至于第四种观点的缺陷更加明显,因为所谓权利人根本不存在知识产权,行为性质属于欺骗社会公众,不存在滥用权利的基础。
笔者认为,可将知识产权滥用定义为:知识产权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当行使权利,违背设立知识产权的制度宗旨和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政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这一定义表明了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可责难性,行为人行为客观上具有不当性并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基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政策的相悖性,该定义也揭示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是违背设立知识产权的制度宗旨和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政策的行为。
(二)知识产权滥用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知识产权滥用这一概念是权利不得滥用这一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自然延伸。由于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而在民事法律中很早就确立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随着知识产权在当代经济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的现象也日渐增多,从而在客观上提出了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要求。特别是随着2008年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了对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制度,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研究与理论逐渐成熟。
从知识产权滥用理论的产生来看,国外关于知识产权滥用概念的提出和适用来自于司法实践,特别是涉及“不洁之手”理论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运用,并且通常是作为被告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抗辩所提出的理由。一般认为,美国1917 年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案首次提出了专利滥用抗辩问题并被法院所接受。考察美国涉及专利侵权或著作权侵权的案例,可以发现这些案件的侵权诉讼被告基于不洁之手原则提出了不构成侵权的抗辩。[5]在这些案件中,只要法院能够确认专利权人或者著作权人的行为缺乏情理或者不具有正当性,如“在有些方面影响了当事人在法院审理案件上的公平”[6]或者被告能够证明因为原告和诉争事件直接相关的不合理行为而受到损害,则法院可以基于上述“不洁之手”原则对于原告主张的专利权或者著作权不予以保护。例如,在Keystone Driller Co. v. General Excavator Co.[7]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原告故意隐瞒了不能授予专利权的相关证据,因而对其主张的专利侵权救济请求不予支持。法院认为,应当维护衡平法上的“不洁之手”原则。在Mitchell Bros. Film Group v. Cinema Adult Theater案[8]中,法院则认为,如果原告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其主张的著作权侵权救济就可能被驳回。
从知识产权滥用理论在美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看,美国通过判例法逐渐确立了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原则,并且首先是在专利法领域得到确认,随后在著作权领域也逐渐被接纳。国外有学者甚至认为,权利滥用原则在专利法领域根深蒂固。如前所述,最初是通过适用衡平法中的“不洁之手”原则而被法院接受专利权滥用抗辩原则的。除了前述1917年案外,1942年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Morton Salt Co. v. G. S. Superego Co.案[9]也是极具影响的判例。在该案中,涉案的专利技术是G. S. Suppiger 公司生产的一种设备。专利权人出租其专利产品附加了一个条件,即承租人只能从其购买该设备需要使用的沉淀罐装食品的盐片剂,不得从其他渠道购买。法院认为,G. S. Suppiger 公司搭售行为会对非专利产品的自由竞争产生损害,因而认定该行为构成了不受保护的专利滥用行为。法院基于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超过了专利法授予的有限的权利范围而认定专利权人不能获得专利法的保护。[10]基于此,法院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该专利侵权诉讼案明确适用了专利滥用抗辩原则,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确立禁止专利权滥用原则的案件。此后,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被告时常将专利权滥用作为不侵权抗辩的手段和武器。例如,在1956年的United States Gypsum Co. v. National Gypsum Co.案[11]中,被告即提起专利权滥用抗辩。不过,法院也同时指出,当专利滥用行为被消除后,专利权人仍然能够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上述专利权滥用概念的提出和在专利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影响到在著作权法领域中适用权利滥用抗辩原则。从国外特别是英美国家著作权滥用理论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来看,著作权滥用理论同样源于英美衡平法,作为对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原告“不洁之手”行为的回应。例如,在Massie& Renwick Ltd. v. Underwriters' Survey Bureau Ltd案[12]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已经考虑到适用著作权滥用原则的问题。尽管早期的这些案件与当代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出现的诸如软件许可之类的许可协议引发的著作权滥用问题相比显得有些陈旧,[13]毕竟司法实践中已经注意到著作权滥用原则的适用问题。又如,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Broadcast Music,Inc.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Inc.案[14]中,法院认可了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关于本身存在反托拉斯违法行为的认定,暗示可以接受著作权滥用抗辩的原则。
在著作权滥用理论及其适用司法方面,值探讨的是1990年Lasercomb America,Inc. v. Reynolds 案[15],其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案涉及原告许可被告使用其计算机软件。在该案中,原告和被告签署了计算机软件合同,原告要求被告在一百年内不得在现有软件基础上进行后续开发、生产竞争性产品。在该案中,被告提出了原告存在著作权滥用的抗辩,认为原告行使著作权的行为超越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其企图在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外限制竞争。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则认为,该案许可协议中期限达到99年,且在合同期限届满后1年内不允许被告设计和原告软件进行竞争的软件,使得Lasercomb的著作权保护期限被变相延长,从而接受了被告提出的著作权滥用抗辩,否定了地方法院关于被告构成著作权侵权的认定结论。上诉法院强调,该案的实质在于原告行使著作权的行为是否违背了著作权许可所蕴含的公共政策,而不在于是否以不符合反垄断法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16]该案被认为是美国著作权侵权诉讼中首次适用著作权滥用原则,首次基于著作权滥用的原因而驳回著作权人主张侵权的诉讼请求。关于该案,还值得指出的是,上诉法院澄清了著作权滥用抗辩与著作权人在正常情况下行使诉权的关系,认为法院并非否认Lasercomb享有的著作权,其不存在滥用著作权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由此可见,著作权滥用的认定是基于个案进行的,在个案中认定某著作权人存在滥用著作权行为而对其指控被告著作权侵权的主张不予支持,不等于该著作权人在其他案件中也不受保护。
在美国,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等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存在,也推动了美国司法部加强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范指引。例如,美国司法部于1975年颁布了专利权滥用的“九不规则”,明确了九种“本质滥用行为”,具体包括:(1)搭售行为,即在许可协议中要求被许可人购买非专利产品;(2)不合理回授条款;(3)限制购买者转售专利产品;(4)禁止被许可人在专利权范围之外从事经营活动;(5)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签订不再授权予第三方的协议;(6)强制性一揽子许可;(7)不合理地将许可使用费与被许可人的销售额绑定;(8)限制被许可人使用通过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9)限定专利产品的最低转售价格。[17]上述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专利权滥用中常见的可以直接认定的行为,有利于为司法实践中认定专利权滥用行为提供指引。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美国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理论及其司法适用中,对于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的认定逐步引入了公共政策标准。众所周知,知识产权法具有独特的公共政策,其与知识产权法赖以实现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密切相关。以美国知识产权法为例,立法和司法者从其宪法依据即赋予美国国会制定授予作者和发明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专有权利的法律,旨在促进科学和有用技术的进步,这被解释为“为公共福利而创作和传播知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8]在美国知识产权法中,尽管高度重视通过有效保护知识产权而形成的激励创作和创造的制度激励机制,同时也更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背后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目标。例如,在1948年Unites States v. Paramount Pictures, Inc.案[19] 中,法院主张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人的报偿是作第二位考虑的”。在Mazer v. Stein一案[20] 中,法院更是指出:美国《宪法》著作权和专利权条款背后的经济哲学是,授予著作权和专利权是通过作者和发明者的天资增进公共福利的最佳手段,值得对作者和发明者付出的努力给予报偿。在United States v. Paramount Pictures, Inc.案[21]中,法院认为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一样,其激励作者的目的次于增进公共福祉的目标。如果说,著作权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社会公众不断扩大接触独创性作品的可能性,法定著作权垄断制度所带来的作者私人收益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在更早的1909年关于美国著作权法的国会委员会报告则指出:“国会根据宪法的条款制定著作权法,不是基于作者在他的创作物中存在的自然权利,而是基于要服务于公共福利……手段是保障作者对其创作物享有有限保护期的专有权。”[22]
考察美国等国家知识产权滥用理论及其司法适用的发展可以看出,公共政策标准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在认定涉案知识产权人的行为构成权利滥用时,引入了公共政策标准。不过,这里的公共政策标准的内涵和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的公共政策的内涵相比,更侧重于促进正当、有效竞争和提高竞争、创新效率等方面。在后面还将着重分析的反垄断意义上,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涉及对竞争政策的违反,尤其是表现为限制、排除竞争,从而损害竞争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这在美国相关典型案件中也得到了体现。例如,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Practice Management Info. Corp. v.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案[23]中,被告AMA在HCFA许可协议中明确提出了限制性措施,要求原告承诺不使用其他竞争性的编码系统,原告认为该措施构成著作权滥用行为。该上诉法院一方面肯定了对于著作权滥用的抗辩不需要提供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证明,另一方面则明确了需要结合竞争效果的公共政策。在判决书中,针对著作权滥用抗辩是否适用问题,法院着重考虑了作为被告的著作权人的许可行为对竞争效果的影响。法院认为,由于许可人“阻止被许可人使用其他竞争性的产品”,这样就使得著作权人从竞争对手处获得了“实质性不公平的优势”,并且这一行为违反了著作权法所体现的公共政策。[24]
知识产权滥用理论的出现及其在国外司法实践中适用,反映了知识产权在经济社会中地位不断提高的现实,也反映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导致市场经济主体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运行的竞争秉性需要合理规制的迫切需求。如《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指出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市场经济主体更加注重运用知识产权开展国内外市场竞争,借此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知识产权人为了开展竞争并在竞争中胜出,难免利用其受法律保护的独占权利,采取排除、限制竞争的手段实施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这一现实使得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知识产权滥用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禁止,反而出现了诸多新的现象和特点。特别是当前数字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日益繁荣,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也拓展到网络平台和电子商务环境中。对于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也越来越注重其对违反知识产权法赖以实现的促进公平和有效竞争的违反方面。当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也存在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内,并非都来自反垄断法领域,从下文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表现及其认定的探讨即可以深刻认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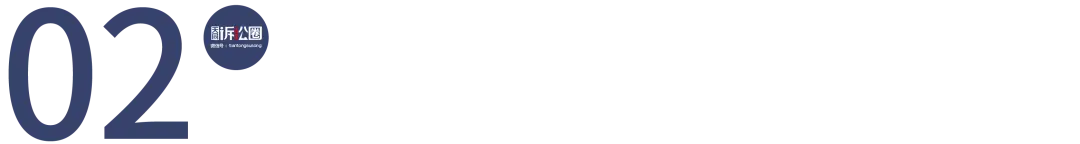
知识产权滥用的表现及其类型化
(一)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表现概述
知识产权滥用,不仅是一个理论上针对知识产权人不适当行使权利的法律概念,而且是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基于知识产权是一个类称的概念,在研究知识产权滥用问题时,需要立足于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特点研究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滥用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尤其是专利权滥用和著作权滥用。不过,无论属于何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滥用的表现形式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共通性。此外,知识产权滥用的表现还可以从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而分为一般意义上的违反权利设定目的、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侵害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与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本部分关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分类,也主要按照这一标准进行。当然,在研究知识产权滥用问题时,也有很多成果并不严格区分构成一般权利滥用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与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而是可能两类行为都存在。
关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表现,现有研究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例如,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滥用现象主要表现为拒绝许可或不实施专利、采取过渡的技术措施、专利联营、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为(如搭售)、延长保护期(如将专利期限延长至法定期限之外)、滥发警告函、滥用诉权等”,并大致将其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是基于权利的绝对性而拒绝许可、不实施或者不充分实施以及滥用技术措施等;其二是基于权利的相对性而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市场行为;其三是以程序性权利为基础的规则滥用。[25]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上述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分类包含了一般权利滥用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和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关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表现,国外学者基于对司法实践的总结,也进行了归纳。仅以著作权滥用为例,有学者将著作权滥用概括为以下四种较为典型的类型:(1)利用著作权迫使被许可人让步;(2)限制被许可人与著作权人的竞争对手进行交易的能力;(3)限制被许可人以外的其他人竞争能力的交易;(4)司法制度中的反竞争性使用。[26]还有学者将著作权滥用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1)搭售,即将受欢迎的电影或者计算机软件等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与使用其他作品捆绑在一起;(2)利用在合同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在合同及许可协议中约定反竞争条款;(3)强制性一揽子许可;(4)拒绝向竞争对手发放许可证。[27]
同样是著作权滥用行为,我国有学者则认为,典型的著作权滥用行为体现为“利用版权限制被许可人开发竞争性产品、超出版权保护期限行使权利、滥用诉权、不正当行使版权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他有损公共政策的行为以及垄断行为等”。[28]
从上述关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类型和表现看,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涉及权利人以许可等方式行使权利、以许可合同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时,存在利用许可合同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排除、限制竞争的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除此之外,还存在属于一般权利滥用范畴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如针对本来可以合理使用的行为进行不适当限制的滥用行为,以及滥用诉权的行为。以下将分别对构成一般权利滥用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和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类型和表现进行探讨。
(二)构成一般权利滥用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属于广义上的权利滥用的范畴。这些行为,并非都涉及排除、限制竞争从而构成反垄断法规制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以下几种情况即属于较为典型的构成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1.属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内的限制、本可以正当使用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从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理来说,知识产权是一种具有专有性的权利。未经知识产权人许可,也没有法律特别的规定时,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知识产权人的知识产品。专有性也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只有保障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才能通过赋予知识产权而调动知识产权人从事知识创造的积极性,实现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和促进创新性成果传播和利用的目标。也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国际公约都以维护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的独占和垄断作为重要目的。这也是为何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政策构建中“言必称保护”的原因所在。
然而,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认识不能停留在仅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的层面,而必须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立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宗旨,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律不仅保护知识产权人的私权,而且需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在知识产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基于此,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知识产权都有其合法的边界范围,知识产权法律在规定知识产权人可以享有的专有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知识产权的限制制度。据此,当社会公众的行为符合知识产权限制制度的条件时,知识产权人即无权禁止他人使用。在知识产权法律中,都规定了相应的权利限制制度。例如,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专利法》中规定的专利侵权例外、权利穷竭制度,《商标法》中规定的正当使用制度等就是体现。此外,知识产权法还规定了权利保护期限制度和地域性原则。根据这些规定,在权利保护期限届满以及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范围内,社会公众都可以自由使用相应的知识产品,而不受原有的知识产权人或者知识产权保护地域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人限制。
基于上述,属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内的限制本可以正当使用的行为,如果知识产权人明知或者应知他人的使用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而仍然主张权利,就有可能构成知识产权滥用。应当说,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并非罕见。[29]
2.不适当延长知识产权保护期限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保护期限。这也是合理平衡知识产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所需。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保护期限,使得社会公众在知识产权期限届满后能够自由、免费地使用,而不再受到知识产权人的限制。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制度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例如,防止知识产权人以有限的智力投入而享有无限的利益;避免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成本过高。[30]基于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重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违背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制度的设立宗旨、不适当延长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或者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届满后的行为仍然主张知识产权的行为,均涉嫌对相关权利的滥用,不应获得支持。
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以下几种情况即属于与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或权利滥用相关的典型案例:
第一种情况是,试图通过作品的演绎创作形式或者改进发明形式,延长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例如,演绎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产生的作品。从著作权保护期限的角度来说,演绎作品受著作权保护与原作品是否处于著作权保护期限之内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针对著作权保护期限届满的作品创作演绎作品,演绎作品作者享有独立的著作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届满的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动或者改编而主张著作权的案例。[31]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已有作品为基础进行二次开发的衍生作品日益增多,特别是在已有作品具有较高的市场生命力时,这种情况更加普遍。在已有作品著作权保护期限届满后,衍生作品是否受到著作权保护,则需要判定其与已有作品相比,是否存在独创性表达空间。
第二种情况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内,利用在签订协议中的优势地位,通过许可协议约定在知识产权期限届满后仍然需要支付许可人以使用费。毫无疑问,根据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制度的基本原理和规定,某一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一旦届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并且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在上述情况中,显然作为知识产权人的许可人不适当地利用了自己在签署合同中的优势地位,迫使对方接受在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届满后继续支付费用的要求。实际上,前述美国涉及知识产权滥用的判例就认定这类行为缺乏法律的正当性依据,相关约定不受法律保护。
第三种情况是,当知识产权人享有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届满后,寻求另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或者主张不正当竞争保护。对于上述情况,是否应认定为知识产权滥用,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根据个案分析。原则上说,基于知识产权复合保护的特点,知识产权人在其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届满后,寻求另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或者主张不正当竞争保护,只要满足受其他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或者指控的被告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件,就可以主张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或者制止不正当竞争。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知识产权具有不同的保护条件,基于同一客体,知识产权人因而可以获得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例如,针对某一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在该专利保护期限届满后,原专利权人可以基于该专利产品中具有独创性和个性化特色的包装、装潢主张著作权保护或者基于该包装、装潢具有一定影响而主张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法律所要禁止的则是,当某一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届满后,原知识产权人针对原有的知识产权再主张保护。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知识产权人也不能说是权利滥用,因为此时原先的知识产权人已无知识产权可言,不存在主张权利的法律基础。
3.与欺诈和掠夺在先权利有关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在形形色色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其中一类涉及通过法定程序获得某一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人,由于其取得知识产权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如剽窃、他人作品或者技术成果或者“抢注”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然后进行著作权登记、申请并获得专利或者申请注册商标,再向目标群体发起相应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应当说,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看似基于获得相关的权利或者权利证书而具有合法基础,但由于其获得权利本身侵害了他人的在先利,从社会公众的角度看行为人以侵害他人在先权利作为手段,对于相关授权机关和社会公众构成了欺诈。因此,对于这类本身缺乏权利正当性基础的知识产权,其权利人行使权利本身即已构成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对此,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认识:
首先,行为人获得的知识产权侵犯了他人在先的知识产权,不仅不应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反而基于其侵害他人权利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来看,保护在先权利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相对于在先权利而言,在后取得的权利可称之为“在后权利”。在后权利的取得和行使,不能侵害在先权利,在后权利取得及其行使的合法边界范围是明确的,即在先权利构成了其权利边界的“分水岭”,一旦越过这一“分水岭”,就会构成权利取得的瑕疵或者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侵害在先权利。当然,从广义上说,相对于在后取得的知识产权的在先权利,并不限于某一知识产权,像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意义上的民事权利也可以成为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在先权利。同时,还应指出,在后权利的取得,并非一定侵害在先权利。在有的情况下,在后权利的取得本身不存即在法律上的障碍,特别是程序法上的障碍,但在后权利在获得后,其权利人行使权利时可能会构成对在先权利的侵害,此时就需要对在后权利的行使予以限制。例如,在早年的计算机类上“恒升”注册商标所有人诉同类商品上“恒生”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侵权诉讼中,[32]被告在申请注册“恒生”商标过程中,原告曾提出异议,但在异议复审阶段,原告放弃程序性权利,从而使得被告“恒生”商标得以注册。原被告商标适用于相同商品、商标存在近似,且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恒生”注册商标在获得注册后继续在计算机类商品上使用,就会导致对“恒升”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该案虽然以象征性的1元作为补偿而以调解形式结案,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思考,例如如何处理在后权利和在先权利的关系,特别是当在后权利属于合法取得但其行使又必然侵害在先权利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在后权利?
在近些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践中,针对上述以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为手段获得某种知识产权的案件不在少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所谓“知识产权人”在获得权利后,大肆向相关群体发动侵权攻势,彻底暴露了其侵吞他人果实、披着合法的外衣从事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险恶用心。这类行为完全违背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宗旨,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以下不妨分别从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司法实践角度加以探讨。
在著作权案件中,涉及上述权利滥用的,包括以下情况:一是在剽窃、抄袭他人作品基础上,对于被剽窃、抄袭人以外的第三人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在剽窃、抄袭他人作品基础上形成的“作品”,不仅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反而应当承担侵害他人著作权的法律责任。上述向第三方“行使著作权”的行为,构成权利滥用。二是“捷足先登”,利用著作权自愿登记制度,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据为己有,并取得登记证书,然后以此向认为相似作品的作者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我国对著作权的获得也实行自愿登记原则。在著作权登记实践中,不排除个别不法行为人故意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然后向相似作品作者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这种情况,对于著作权登记机关和社会公众来说都构成了欺诈行为。这种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的行为由于缺乏合法的权利基础,因而不应当受到保护。严格地说,与其将其视为著作权滥用行为,不如定性为侵害被登记作品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因为原告主张著作权的作品来自他人,并非其创作而成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获得。
关于著作权滥用,这里还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是:将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通过加上水印等“权利管理信息标记”,谎称是自己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向第三方主张权利,这种情况是否也应视为著作权滥用行为?笔者认为,上述情况不宜视为著作权滥用行为。原因很简单,因为涉案作品已经进入公共领域,原告根本不存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这种情况,应当视为对于社会公众的欺诈行为,原告向第三方主张权利自然不能获得保护。针对这种情况,在有些国家甚至规定了刑事责任。在我国,也确实出现了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向多人主张权利的案例。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和相关法律对此如何适用法律未做规定,笔者认为建立侵害公共领域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必要性。[33]
在专利权案件中,涉及上述权利滥用行为的,典型的如明知为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而将其申请为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并利用这类专利申请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程序的机会,在获得专利权后,即对于众多使用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目标群体发动批量侵权诉讼攻势。在上述情况下,专利权人获得专利权显然也是缺乏合法的权利基础的,其行使具有瑕疵的专利权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因为对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任何人可以自由使用,并不需要获得许可与支付费用。当然,针对上述情况,应注意明确相应的边界范围,因为很多专利授权确权和侵权纠纷案件,涉及现有技术或现有设计的判定,甚至不同层级的法院认识并不一致。[34]
在商标权案件中,涉及上述权利滥用的案件常见于将他人在先的相近似的标识抢注为商标,然后通过高价转让的形式逼迫目标企业就范,在转让不成时即通过商业维权等形式发起批量商标侵权诉讼,企图获取高额侵权赔偿并夺取被告的市场。这种行为明显违背市场主体应当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35]构成对商标专用权的滥用。[36]
在商标纠纷案件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即原告明知其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已不复存在,却仍然委托律师事务所进行批量维权,相关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前提下则依然判决被告构成商标侵权并承担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责任。这类案件,是否可以视为商标权滥用之诉?对此,笔者认为,由于原告主张权利的基础不存在,并不能将原告提起系列侵权诉讼的行为定性为权利滥用的行为,而应当认定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被告合法权益的欺诈行为。
其次,本身缺乏权利正当性基础的知识产权,其知识产权申请与获得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甚至恶意。这里不妨通过一个典型案例简要说明:在某公司与邵某侵害商标权纠纷再审案[37]中,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针对邵某注册涉案商标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进行了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业务上的优势,恶意注册商标,损害他人在先权利,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属于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不应受法律的保护。该案涉及权利滥用行为,从邵某的主观动机看,显系具有注册和他人在先标识相近似的商标,并通过诉讼途径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
再次,上述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对于市场竞争者和社会公众利益具有损害性。上述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在先权利或者在先权益,因而必然会对市场竞争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产生损害。例如,在广州某贸易公司、义乌市某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38]中,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广州某贸易公司于2018年取得涉案商标的专用权后,没有形成充分的商标宣传或实体销售的依据,而是利用商标禁用权及损害赔偿制度,针对广大游戏周边产品卖家提起了大规模侵权诉讼,主观恶意明显,既缺乏合法的权利依据,也不符合我国商标法的基本立法原则,其借用司法资源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属于权利滥用,依法不予保护。
4.涉及知识产权维权与诉讼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战略运用在促进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竞争力提升方面的作用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人和利害关系人拿起法律武器积极进行维权。其中,向涉嫌知识产权侵权人发出侵权警告函和向人民法院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就是十分常见的维权形式。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专有权利,除非存在法律的特别规定,未经许可其他任何人不得行使知识产权人的专属权利。发侵权警告函和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因而也是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的正常体现。
但是,也必须看到,近些年来,一些知识产权人在进行知识产权维权时,存在滥发侵权警告函或者滥用诉权、恶意起诉等滥用知识产权的现象,有的案件还相当严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商业维权现象十分普遍。商业维权固然存在其合理性,但如果滥用商业维权,也同样会造成权利滥用的不良后果。
(1)侵权警告函的滥用
侵权警告函,是知识产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涉嫌侵权人发出的书面信函,一般需要指出涉嫌侵权人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及其后果,以及通过协商和解等方式解决存在的侵权问题。对于被警告的单位或个人而言,收到侵权警告函后,既不要完全漠然视之,也不要感到害怕,而应当冷静地进行分析其是否存在警告函中主张的侵权行为。在现实中,警告函的滥用体现为,权利人在侵权事实和证据不够充分的前提下,通过大范围、大批量形式了滥发警告函,从而使得被警告的单位或个人生产经营处于时刻受到威胁的状态。[39]很多权利人在发出侵权警告函后,既不撤销警告函,也不向有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使得被警告人无适所从。在处理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函问题时,一方面需要防止滥发侵权警告函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被警告的单位或者个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也同样应当注意防止针对侵权警告函滥用不侵权之诉的诉讼救济途径。
(2)滥用维权手段实施恶意投诉
当前,随着知识产权对于市场经济主体开展市场竞争活动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与知识产权保护宗旨背道而驰的各式各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时常出现,以维权为名、行恶意投诉之实的现象和案例也并非少见。在有的涉及商标侵权的诉讼案件中,原告在一审获得胜诉后,急不可耐地向被告的合作伙伴、销售门店甚至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实施大范围投诉。应当说,在二审判决之前,一审判决认定商标侵权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以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判决为依据到处投诉,使得相关经销商、合作伙伴和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错误地以为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而采取了行政处罚等措施,可能会无端引发更多诉讼,这种投诉构成恶意投诉。
(3)恶意诉讼
在知识产权诉讼特别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也存在知识产权滥用问题。这种情况尤其体现为恶意诉讼。这类恶意诉讼,体现为行为人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具有恶意,在客观上存在对被提起诉讼行为人的损害后果。恶意诉讼的本质特点是提起诉讼的知识产权人具有追求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实现自身不正当利益的恶意。毫无疑问,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的恶意诉讼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本身构成了知识产权滥用,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宗旨背道而驰。因此,针对知识产权人恶意提起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不仅不应当支持,反而应对恶意诉讼行为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追求相应的法律责任。
例如,在某智能科技公司与某电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再审案[40]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知识产权案件构成恶意诉讼的以下条件:一是行为人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无事实或者法律依据;二是行为人提起诉讼主观上具有恶意。行为人的恶意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认识因素。在行为人恶意取得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尤其要明知其取得知识产权不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其二为目的因素。即行为人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要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三是行为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给他人造成了损失,且损失与行为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具有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恶意诉讼行为本质上缺乏主张权利的合法基础,或者说其主张权利的行为缺乏正当性。恶意诉讼行为还是一种侵权行为,原因在于该行为的实施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这无疑有助于对于恶意诉讼行为的认识,特别是认识到该行为的危害性。[41]
(三)构成排除、限制竞争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及其认定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从反垄断法规制的角度,研究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为此,先需要从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表现及其认定。
1.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
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知识产权属于法定的具有独占性的权利。根据知识产权法原理和规定,除非法律存在特别规定,未经知识产权人许可,他人不得行使只能由知识产权人行使的权利,否则将构成侵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也正是基于此,2008年颁行的《反垄断法》第55条、现行《反垄断法》第68条前半部分均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国外相关立法也有类似规定。例如,加拿大《竞争法》规定,基于本节的目的,只有依据著作权法、工业设计法、集成电路设计法、专利法、商标法或其他国会关于著作权或工业产权立法行使权利和享有利益的行为,不属于反竞争行为。[42]
不仅如此,从立法宗旨和功能看,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契合性。以我国知识产权法为例,《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单行法第1条都规定了相应的立法宗旨。从这些规定来看,体现了鼓励和保护创新以及促进技术、文化和商品流通领域公平竞争秩序构建的立法意旨。再以我国《反垄断法》为例。2008年颁行的《反垄断法》第1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2022年修正的现行法则将上述第1条做了适当修改,即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增加了“鼓励创新”。这样,就使得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研究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问题时,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实际上,2015年4月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74号公布、根据2020年10月2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号修订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以下简称《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第2条,以及2019年1月4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条,都强调“反垄断与保护知识产权具有共同的目标,即保护竞争和激励创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这可以分别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一是“保护竞争”。这里的保护竞争,实际上是指保护公平竞争、正当竞争和自由竞争;反过来说,要反对和制止不正当竞争、反对危害公平和自由竞争的行为。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看,其隐含着既限制竞争、又在更大程度和更高层面促进竞争的增进有效竞争的制度机制。一方面,如前所述,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知识产权具有独占性、专有性,对于同行竞争者来说无异于是对相关竞争行为的抑制或者限制。例如,根据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时,技术发明一旦公开,则可以被任何人自由利用。从这里对比可以看出,从静态的角度看,专利制度会限制竞争,不利于技术扩散,甚至造成技术封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进行第一部专利立法时,就曾存在这种观点。需要从另一方面看到的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有限抑制甚至限制竞争的基础上,在更大程度和层面上促进了公平竞争、正当竞争和自由竞争。知识产权法通过其制度设计和安排,特别是对于仿冒、假冒、剽窃等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有效制裁,维护了公平竞争秩序,对于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来说,其重要的立法目的则是通过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在理论上,反垄断法被视为竞争法的范畴,其以维护公平、自由竞争为己任,以遏制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为重点规制对象。由此可见,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都存在保护竞争的功能和使命。这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体系中都有充分体现。只是需要进一步指出,在保护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方面,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毕竟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其中前者定位于私法且侧重于维护私权与制止知识产权侵权方面保护竞争、后者定位于公法且侧重于维护公共利益角度保护竞争。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除了知识产权单行法,与反垄断法具有紧密联系但并不属于其范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被认为能够对知识产权提供附加和补充的保护,甚至被认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特别法。
二是鼓励或者说激励创新。就知识产权法而言,其被公认为是鼓励创新或者说激励创新的保障机制与制度机制。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即指出:“知识产权制度是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合理确定人们对于知识及其他信息的权利,调整人们在创造、运用知识和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1月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21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则在“总体要求”部分指出:要“牢牢把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和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从制度层面而言,知识产权法是通过确认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享有专有权利、保护对创新的投资、促进创新成果推广运用等制度性机制实现鼓励创新的立法目标的。[43]基于知识产权法鼓励创新的重要立法目标和制度设计,知识产权法甚至被有的学者称为“创新之法”。就反垄断法而言,如前所述,在2008年《反垄断法》第1条中并无“鼓励创新”的内容;2022年该法修正后,则在第1条增加了上述内容。应当说,这一修正在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发展使得创新型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的鼓励创新,其中也包括了创新效率的内容。当然,鼓励创新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对于反垄断法而言,需要通过维护公平竞争,促进创新成果扩散,而不是通过排除、限制竞争形式抑制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扩散。这在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反垄断问题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从后面关于反垄断意义上知识产权滥用的认定因素即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
三是效率。从产权制度的效率观看,它强调的是如何最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并实现最大化的产出和最佳的效用。即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调动人们利用有限资源的积极性,从而使得资源在动态利用中获得最佳经济效益,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就知识产权法而言,“效率是知识产权法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知识产权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在制度设计方面体现为合理与有效的权利配置,也就是使各方主体在权利体系中达致一种均衡状态。”[44]知识产权法本身是一种涉及知识资源分配和有效利用的产权制度与制度安排。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目标,不仅体现于通过产权界定确立产权关系,而且体现为基于知识产品财产权的确保而形成的激励创新的制度激励机制,通过这一机制而实现了对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最终通过提高知识生产和创新效率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45]就反垄断法而言,“经济运行效率”也是其追求的目标。在鼓励创新的价值导向下,反垄断法还存在创新效率的内涵。由于垄断行为有碍公平竞争,其不仅对于竞争效率具有破坏性,而且也不利于创新效率提高,这些都不利于经济运行效率,因而反垄断法需要以提高效率为目标,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四是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知识产权法而言,尽管其是以维护和保障知识产权人利益作为基础,但基于其立法目标,特别是实现知识产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知识产权法中还存在维护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当然,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法基于特定的调整对象和功能,在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机制方面有所区别。例如,著作权法在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更多地体现为维护广大作品使用者在著作权法中使用作品的便利和自由。专利法在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体现为通过规定侵权例外制度等确保专利产品的自由流通以及通过建立以公开换保护的制度机制促进技术信息的分享和流动。商标法在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则更加凸显,这是因为其通过制裁造成消费者混淆之虞的形形色色的商标侵权行为而直接维护了消费者利益。在我国《商标法》中,“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被明确纳入立法宗旨条款中。
从知识产权法的规定看,尽管其保护的知识产权为私权,在私权保护中却依然存在十分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我国知识产权法律都明确规定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原则和具体制度。例如,《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行使权利,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其第53条还针对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规定了需要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专利法》第5条第1款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其第20条则规定: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滥用专利权,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构成垄断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处理。”此外,其第25条第(1)项对不丧失新颖性例外的规定、第49条关于指定许可的规定,以及第54条和第57条关于强制许可的规定都涉及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考量。
对于反垄断法而言,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则更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与立法目标。这是因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损害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具体来说,垄断行为由于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造成市场和竞争的无序,不仅会损害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而且对于消费市场和消费需求具有直接影响。不仅如此,垄断行为基于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还会直接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和自由竞争,以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正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保护竞争、鼓励创新、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和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对于知识产权人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需要介入,以实现维护公平竞争和自由竞争的目标。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共同目标在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和预防与制止垄断行为中的重要性,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某一特定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为反垄断法意义上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也需要充分考虑和评估行为对于竞争、创新和效率以及维护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方面的影响。从后面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判定所考虑的因素分析,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
2.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表现
关于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现行《反垄断法》第68条后半部分明确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从该规定看,受反垄断法规制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应当具备“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什么是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和《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都做了明确界定。其中,前者第3条第1款规定:“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后者第1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不是一种独立的垄断行为。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或者从事相关行为时,达成或者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实施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可能构成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以下将根据《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和《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的规范指引,对于受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及其认定进行探讨。
(1)利用强势地位签订垄断协议而排除、限制竞争
如前所述,达成垄断协议被认为是垄断行为的重要体现。根据现行《反垄断法》第16条规定,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根据《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第4条规定,经营者之间不得利用行使知识产权的方式达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协议。但是,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的除外。垄断协议直接针对的是对市场的分割、垄断,因此需要界定相关市场的含义。针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而言,相关市场具有特定指向性。涉及知识产权滥用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相关市场的界定,包含技术市场以及含有特定知识产权的产品市场。从知识产权滥用排除、限制竞争的司法实践看,通过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多表现为许可合同、搭售、排除及限制竞争的回授条款等。
①联合研发
在当代,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研发的难度以及投入的人财物成本越来越大。加之研发作为探索利用自然规律解决技术问题的活动和过程,本身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整合研发资源,分散技术开发风险,提高研发效率,联合研发这一合作创新形式日益普遍。联合研发也是合作攻关和技术开发的重要形式。从司法实践中联合研发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看,往往涉及联合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权属与利益分配方面的纠纷,同时也涉及联合开发成果的进一步开发、权属及利益分配等问题。除此之外,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问题也值得关注。
联合研发涉及排除、限制竞争问题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对于联合研发无关的研发或者联合研发后续成果进行不适当限制。这种认定需要考虑对于公平竞争和创新及相关的效率的影响。如从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共同目标看,限制经营者在联合研发完成后进行后续研发显然不利于后续创新,这对于被限制的经营者来说也构成了对竞争的不适当限制,因而是不允许的。
②交叉许可
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叉许可,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认识。从知识产权行使来看,交叉许可也是实施许可的一种形式。从知识产权战略的角度看,交叉许可也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一种形式。在企业专利实践中,交叉许可战略通常在企业间的专利比较接近,而专利权的归属又错综复杂或相互依存的情况下适用。如就改进发明与原发明、从属发明与基本发明有必要相互许可对方利用自己的专利,订立专利交叉许可合同。[46]无论从何种角度研究知识产权交叉许可问题,一般都明确认可这一许可形式具有积极意义。但关于交叉许可带来的反垄断问题,学者也开始关注。交叉许可涉及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在专利领域更为常见。国外文献即指出,在专利司法实践中,专利滥用理论已被运用于交叉许可领域。[47]
③排他性回授和独占性回授
在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规定独占性回授条件,是有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涉及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定的重要内容。[48]《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9条规定了排他性回授和独占性回授。其规定,分析排他性回授和独占性回授对市场竞争产生的排除、限制影响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许可人是否就回授提供实质性的对价;二是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在交叉许可中是否相互要求独占性回授或者排他性回授;三是回授是否导致改进或者新成果向单一经营者集中,使其获得或者增强市场控制力;四是回授是否影响被许可人进行改进的积极性。由此可见,这些因素主要考虑回授对市场竞争、经营者集中、被许可人对技术改进的积极性等方面的影响。[49]
④不质疑条款
《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0条规定了不质疑条款。即不质疑条款是指在与知识产权许可相关的协议中,许可人要求被许可人不得对其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异议。分析不质疑条款对市场竞争产生的排除、限制影响,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许可人是否要求所有的被许可人不质疑其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二是不质疑条款涉及的知识产权许可是否有偿;三是不质疑条款涉及的知识产权是否可能构成下游市场的进入壁垒;四是不质疑条款涉及的知识产权是否阻碍其他竞争性知识产权的实施;五是不质疑条款涉及的知识产权许可是否具有排他性;六是被许可人质疑许可人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是否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从上述规定看,不质疑条款是否对市场竞争产生的排除、限制影响,需要考虑许可的性质、对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以及下游市场和竞争性知识产权实施的影响。[50]
⑤标准制定
经济社会发展,使标准日益成为实现同质化产品的共通性、方便消费者的重要范式。随着知识产权在当代经济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标准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当前标准必要专利法律问题日益突出,而其中围绕FRAND原则和禁令引发的反垄断诉讼案件也日益增多。《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0条即规定了标准制定中涉及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认定。根据该条规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共同参与标准制定可能排除、限制竞争,具体分析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是否没有正当理由,排除其他特定经营者;二是是否没有正当理由,排斥特定经营者的相关方案;三是是否约定不实施其他竞争性标准;四是对行使标准中所包含的知识产权是否有必要、合理的约束机制。上述规定表明,标准制定中涉及是否存在排除、限制竞争问题,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对特定经营者或其相关方案的排除,以及对行使相关知识产权的约束机制。
⑥其他限制
基于知识产权的独占性与专有性,知识产权人在行使包括许可使用权时,很可能对被许可人利用其知识产权施加一定的限制性条件。除了前面探讨的可能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一些情形和因素外,在涉及知识产权使用范围、相关商品市场和数量以及具有竞争关系的技术或者商品的限制等都可能涉及排除、限制竞争问题。《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2条列举的即有以下典型形式:一是限制知识产权的使用领域;二是限制利用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的销售或传播渠道、范围或者对象;三是限制经营者利用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数量;四是限制经营者使用具有竞争关系的技术或者提供具有竞争关系的商品。[51]
上述这些限制形式在一般情况下有利于实施知识产权,提高知识产权利用效率,通常也被认为具有商业合理性。但同时,上述限制也有可能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反竞争行为。根据该条规定,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限制的内容、程度及实施方式;二是利用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的特点;三是限制与知识产权许可条件的关系;四是是否包含多项限制;五是如果其他经营者拥有的知识产权涉及具有替代关系的技术,其他经营者是否实施相同或者类似的限制。总体上说,如果上述限制行为有利于许可方和被许可人,且对于其他经营者市场竞争无甚损害,就不需要予以禁止。当然,这里存在如何界分知识产权人合法行为许可权与构成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疑难问题,需要结合个案,认定许可性质和目的,以及许可协议对于其他经营者和竞争市场的影响。
(2)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是典型的垄断类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明显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反竞争后果,因而无一例外地被各国反垄断法所禁止。现行《反垄断法》第7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其第22条则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做了详细列举。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对知识产权人行使知识产权时可能存在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
在界定经营者实施知识产权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首先需要界定“相关市场”。《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4条规定,界定相关技术市场可以考虑以下因素:技术的属性、用途、许可费、兼容程度、所涉知识产权的期限、需求者转向其他具有替代关系技术的可能性及成本等。从上述规范可以看出,界定与知识产权行使有关的市场涉及经营者所处的产品市场或技术市场,以及知识产权人能否形成市场优势地位、替代品和市场应用前景等多方面因素。[52]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知识产权是一种独占权和专有权,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却不能等同。《反垄断法》第22条第3款规定了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即“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经营者拥有和行使知识产权能否形成市场支配地位,显然也应当根据这一定义判定。此外,根据《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4条规定,还可结合知识产权的特点加以考虑:一是交易相对人转向具有替代关系的技术或者商品等的可能性及转换成本;二是下游市场对利用知识产权所提供的商品的依赖程度;三是交易相对人对经营者的制衡能力。[53]在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下,才有必要进一步判定其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从知识产权法保护原理来说,基于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和知识产权人自行实施其知识产权的局限性,作为知识产权人的经营者通常需要以许可、转让等方式行使知识产权,其中许可更是十分普遍的行使权利的方式。这也是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相关的原因。当然,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需要甄别权利人以许可方式正常行使权利与权利滥用,防止两者的错位。在构成权利滥用时,作为知识产权人的经营者通常与相关主体特别是企业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经营者的目的是要通过排除、限制竞争,实现排挤竞争对手、独占市场的目的,其中多数是“基于确保和加强其市场支配地位之目的,以滥用或不合理限制行为,打乱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形成垄断竞争的模式。”[54]仅就知识产权许可而言,除了前述涉及垄断协议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外,还涉及本部分探讨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总结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通过行使知识产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包括不公平的高价许可、拒绝许可、搭售、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限定交易行为、差别待遇等,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强制性一揽子许可、价格垄断等行为。[55]以下将结合上述指南的规范,分别进行探讨。
① 不公平的高价许可
《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5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分析其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许可费的计算方法,以及知识产权对相关商品价值的贡献;二是经营者对知识产权许可作出的承诺;三是知识产权的许可历史或者可比照的许可费标准;四是导致不公平高价的许可条件,包括超出知识产权的地域范围或者覆盖的商品范围收取许可费等;五是在一揽子许可时是否就过期或者无效的知识产权收取许可费。
在上述考虑因素中,涉及一揽子许可时,如果知识产权人就过期或者无效的知识产权收取许可费,这种行为显然不符合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基本原理和规定,因为对于过期和无效的知识产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经营者无权收取费用。在国外相关专利判例中,针对一揽子许可协议,法院也强调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限于授予专利权的范围。例如,在Mercoid Corp.v.Mid-Continent Investment Co.案[56]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重审了Morton Salt案的观点,认为尽管专利权人有权拒绝许可实施其专利,但这并意味着专利权人可以施加不合理条件扩张其垄断权。此外,在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场合,是否存在不公平的高价许可,则需要考虑行业内相关许可费收取的整体情况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其中“公平、合理和无歧视原则”(FRAND原则)就是公认的重要的评判标准。
② 拒绝许可知识产权
拒绝许可是经营者行使知识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情况下,经营者不承担与竞争对手或者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义务。由此可见,拒绝许可本身并非当然地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而是属于知识产权人自由行使权利的范畴。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拒绝许可知识产权则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则另当别论。
现行《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3项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属于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该规定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的情形。在我国知识产权实践中,尽管基于拒绝许可的案件比例不高,但仍然存在一些案件。[57]
从国外知识产权司法实践看,拒绝许可一类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滥用案例也时常见到。例如,在有的案件中,法院主张若被拒绝的产品或者服务对于被许可人的业务开展至关重要,但又无从找到任何潜在的替代品时,著作权人的拒绝许可行为构成著作权滥用。[58]在有的案件中,如果著作权人拒绝许可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被告会明确地提出著作权滥用抗辩的主张。[59]对于拒绝许可知识产权的行为,法院会结合涉案知识产权及其行使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等因素加以分析。[60]
③ 涉及知识产权的搭售
根据现行《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5)项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构成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涉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搭售。《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7条对此作出了规范。其认为,涉及知识产权的搭售是指知识产权的许可、转让,以经营者接受其他知识产权的许可、转让,或者接受其他商品为条件。知识产权的一揽子许可也可能是搭售的一种形式。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可能通过上述搭售行为,排除、限制竞争。
从国外知识产权司法实践看,涉及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搭售,属于较早和较典型的类型。例如,在前述Morton Salt Co. v.G.S. Suppiger Co.案中,法院认为专利权人在许可其专利时要求被许可人一并购买其非专利产品的行为构成专利权的滥用。[61]在Alcatel USA,Inc. v. DGI Tech., Inc案[62] 中,操作系统软件著作权人作为许可人,要求被许可人在使用该操作系统时必须与许可人的微处理器卡一起使用,否则将不允许使用该操作系统。在该案中,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微处理器卡不存在专利权和著作权,著作权人的许可行为滥用了其操作系统软件著作权。在涉及搭售的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捆绑销售协议”。在美国的相关案件中,法院将捆绑销售协议定义为卖方销售一种产品的协议,在该协议中约定买方必须同时购买另一种(或捆绑)产品。例如,在Northern Pac. Ry. v. United States,案[63]中,法院提出了捆绑产品本身违法的观点,即当销售者“对于捆绑产品具有充分的经济实力,能够明显限制该捆绑产品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在无相反证据证明不存在反竞争效果的情况下,捆绑产品销售行为构成权利滥用行为。[64]在著名的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中,美国政府指控微软公司存在将其网页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与其视窗系统非法捆绑的行为,[65]认为这一行为会排除、杜绝浏览器市场的自由竞争行为,因而违反了美国谢尔曼法。
④ 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
现行《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5项还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构成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8条对于涉及知识产权交易中的上述行为作了规范。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在涉及知识产权的交易中附加下列交易条件,可能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一是要求进行独占性回授或者排他性回授;二是禁止交易相对人对其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或者禁止交易相对人对其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三是限制交易相对人实施自有知识产权,限制交易相对人利用或者研发具有竞争关系的技术或者商品;四是对期限届满或者被宣告无效的知识产权主张权利;五是在不提供合理对价的情况下要求交易相对人与其进行交叉许可;六是迫使或者禁止交易相对人与第三方进行交易,或者限制交易相对人与第三方进行交易的条件。上述行为,明显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其中有些行为还明显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因而也需要进行规制。在涉及知识产权行使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案件中,需要查明和认定一方当事人施加的条件是否合理和必要并符合交易对象的特性与行业惯例等因素。[66]
⑤ 限定交易行为
《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4)项规定,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在知识产权行使中,涉及对相关交易限制的行为也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对此,《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第8条作出明确规定。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实施下列限定交易行为,排除、限制竞争:一是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二是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毫无疑问,上诉限制交易对象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反竞争效果,因而也应纳入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范畴。
⑥ 涉及知识产权的差别待遇
现行《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属于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在知识产权行使中,也可能存在上述情况。对此,《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9条做了规定:分析经营者实行的差别待遇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交易相对人的条件是否实质相同,包括相关知识产权的适用范围、不同交易相对人利用相关知识产权提供的商品是否存在替代关系等;二是许可条件是否实质不同,包括许可数量、地域和期限等。除分析许可协议条款外,还需综合考虑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达成的其他商业安排对许可条件的影响。三是该差别待遇是否对被许可人参与市场竞争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上述规定表明,为实现公平竞争目标,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与经营者进行交易时,对于交易条件相同的相对人同等对待、一视同仁,而不能基于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区别对待。
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现行《反垄断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当前,随着大数据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兴起,人类进入数字时代和智能社会。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发展及其产业化,伴随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使得电子商务、平台经济迅猛发展。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平台经济中,一些大型平台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从近些年来发生的一些涉及数据、算法、平台规则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情况看,除了一般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外,也存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实施不公平的高价许可、拒绝许可知识产权、搭售、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限定交易行为、实施差别待遇等行为。[67]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规定是2022年《反垄断法》修改专门增加的内容,旨在适应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发展需要,应对新技术发展背景下新出现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维护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发展环境下公平和自由竞争秩序。
(3)经营者集中
现行《反垄断法》第25条规定了经营者集中这一垄断行为。在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时,也可能存在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经营者集中问题。对此,《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四章规定了“涉及知识产权的经营者集中”问题。其第20条规定:经营者通过涉及知识产权的交易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可能构成经营者集中。其中,分析知识产权转让或许可构成经营者集中情形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一是知识产权是否构成独立业务;二是知识产权在上一会计年度是否产生了独立且可计算的营业额;三是知识产权许可的方式和期限。在实践中,知识产权的利用通常是与有形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一揽子进行的,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的产品化、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充分体现知识产权在经营者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也正因如此,对于涉及知识产权的经营者集中,需要考虑知识产权许可方式、知识产权利用是否可以构成独立的业务并可以独立计算相关营业额。
针对经营者集中等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从立法的层面来说,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实现的规制手段尽管不同,但被认为采取的手段具有相通性。如有学者指出,“反垄断法和著作权法在实现‘限制市场经营者集中、超竞争定价及排他许可’这些既定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是相通的”。[68]这其实也反映了前述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实现公平竞争、创新和效率以及维护消费者利益与公共利益方面,两者具有共同的立法目标。
(4)其他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
① 专利联营
在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中,专利联营又称为专利联盟,通过联盟形式运营专利,对于联盟内企业和其他专利权主体而言有一定的优势。[69]正如《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第26条所言,“专利联营一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许可效率,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但由于专利联盟在经营专利时有可能对于参与专利联营的经营者或者第三方施行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因而专利联营也有可能涉及权利滥用问题,需要规制。
《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第12条即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专利联营管理组织没有正当理由,利用专利联营实施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做了具体列举。这些被列举的行为由于限制了联营成员或者被许可人自由开展专利许可或研发竞争性技术,或者实施差别待遇等行为,违背了反垄断法的公平竞争原则,因而需要予以规制。
② 标准制定和实施中的滥用行为
前面在分析垄断协议部分论及标准制定中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与此相关的是标准必要专利制定中也涉及专利滥用问题。随着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迅猛发展,标准与专利的结合日益凸显,形成了“标准必要专利”这一新问题。拥有标准必要专利的经营者可能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为此,《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第13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利用标准(含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下同)的制定和实施从事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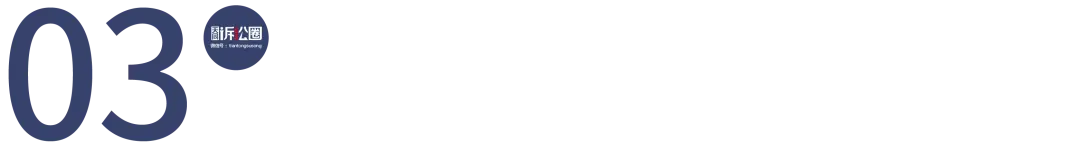
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立法、司法、行政及行业监管
在当前知识产权作为竞争性资源和获取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的背景下,知识产权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也正是基于此,在市场经济活动特别是开展市场竞争中,知识产权人为了最大化地牟取自身利益,就有可能违背知识产权立法宗旨和公共政策,实施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这些滥用行为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违背了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政策目标的不当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与正当行使知识产权的目的背道而驰。采取有效措施有力规制形形色色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就成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些措施,体现为从立法、司法、行政监管和治理方面多管齐下。以下分别进行探讨。
(一)立法应对
2021年10月,国务院公布《“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规划》。其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政策体系”部分,提出要“依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不断完善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相关制度”。在“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政策”规划中,提出要“完善知识产权反垄断、公平竞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从完善立法角度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是应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关键之一。基于前述知识产权滥用涉及知识产权制度内的滥用行为与知识产权制度外构成反垄断意义上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在立法应对方面,应当分别从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和反垄断立法入手。
1.以知识产权法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行为
由于相当一部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直接违背了知识产权立法宗旨和规定,在知识产权法中完善关于知识产权滥用方面的规定,是立法应对的重要措施。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即将“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列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之一,强调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界定知识产权的界限,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公众合法权益”。我国现行知识产权立法对于相关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也有规定。例如,2020年第四次修正的现行《专利法》第20条第1款即规定:“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此外,《专利法》第47条第2款关于专利权人因为恶意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予以赔偿的规定,以及第53条第(1)项和第(2)项分别关于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的强制许可以及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为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的强制许可的规定,也体现了对于滥用专利权的规制。2019年第四次修正的《商标法》也有多处涉及与“恶意”相关的滥用程序和实体权利的行为。[70]笔者认为,针对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一般性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在知识产权立法中作出原则性规定或者针对具体的恶意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具有必要性。就上述《专利法》和《商标法》的规定看,除了现有规定外,在以后进一步修改法律时还可以增加规制权利滥用的类型和表现形式,明确知识产权保护边界。例如,对于权利限制或例外的规定,适当增加相关内容。就《商标法》而言,可增加权利穷竭制度。对于恶意提起专利诉讼或者商标诉讼的行为,则可以增加相应的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就《著作权法》而言,则需要确立禁止著作权滥用的原则性规定。同时,针对著作权限制与例外制度做出完善,确立著作权保护的清晰边界。
2.反垄断法规制
前面对于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及表现形式的研究表明,以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是知识产权滥用法律规制最重要的内容。人们对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的认识在直觉上也是倾向于认为其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不过,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知识产权滥用并非都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反竞争行为,在相关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不构成排除、限制竞争时,则只需要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内加以规制。实际上,在美国专利司法实践中,尽管有法院基于专利权滥用行为对竞争的影响而强调专利权的滥用必然会违反反垄断法,[71]但更有法院主张需要遵循Morton Salt案的观点,即专利权滥用的认定不以违反反垄断法为依据。[72]易言之,只有当相关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构成排除、限制竞争时,才落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毫无疑问,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必然也是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美国有的法院即指出专利权行使行为违反反垄断法令可能构成专利滥用;[73]有的法院认为,专利权人从事的反垄断行为,不限于捆绑销售等反垄断行为,只要其违反反垄断法使用专利,就不能阻止他人的使用行为。[74]
从立法规制的目的看,如前所述,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法均具有促进公平竞争、创新与效率以及维护消费者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目标。单纯地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内的知识产权滥用,则不一定直接违反公共利益标准。不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基于其特有的立法宗旨,既包含了充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这一私权的基本考量,也包含了涉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考量。
比较知识产权立法与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知识产权立法强调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宗旨的公共政策,反垄断法则强调以维护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公共利益。由于知识产权滥用的相当一部分不涉及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可以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内部进行规制,国外即有学者对于以垄断法为基础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做法表示怀疑,并以著作权滥用为例,认为“严格遵守反垄断标准与著作权法所依据的公共政策原则相悖。著作权政策与反垄断公共政策存在潜在的不相容性,佐证了采取独立的权利滥用原则的合理性,而这一原则有利于实现作品创作和作品传播的著作权制度目标”。[75] 这一观点表明,对于著作权滥用之类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需要赋予权利滥用原则的独立地位。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看到,无论是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内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还是在反垄断法框架内规制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两者在增进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祉方面具有殊途同归的目的。尤其是针对构成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行为,通过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制,能够弥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内难以调整和规制的不足。有学者以著作权滥用的规制为例还指出,著作权法的规制和反垄断法的规制的目标均在于提高社会福祉。进言之,“反垄断法旨在打击垄断行为、寻租行为和促进竞争性定价,以增加消费者获得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机会来实现公共福利。基于这一观点,使用反垄断相关原则明确著作权这一专有权利的范围,对于实现著作权法促进创新和最大程度地增进利用作品带来的公共利益的立法目标具有助益”。[76]
从反垄断法的角度看,对于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反垄断法能够很好地弥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内解决的不足和局限性,特别是基于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功能与定位,能够针对知识产权滥用造成的反竞争效果进行有力规制。国外学者以美国《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为例,认为其是为了维护竞争过程中的整体上的正当性,保护消费者福利和提高经济效率需要维护激烈的竞争,故确立了有效遏制反竞争行为的中间目标。[77]
就我国反垄断法规制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反竞争行为而言,现行《反垄断法》第68条专门针对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的规制。其第9条针对新增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除此之外,前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的《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规定》是专门针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的规定。鉴于上述规范均是在现行《反垄断法》颁行之前公布实施的,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需要以现行《反垄断法》规定为基础,进行适当的修改和完善。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部门规章的改革,既要注意区分正当、合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界限,也要注意区分尚未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与构成了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排除、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在设计和完善相关制度时,一方面需要考虑行使知识产权对于实现权利人利益、促进创新与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与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行使知识产权行为对于经营者、消费者和市场竞争格局以及潜在创新的影响,特别是是否会形成垄断协议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经营者集中等为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情形。此外,总结近些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经验,将成熟的审判经验和做法吸收到规则制定和完善中,有利于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滥用法律规制制度的完善。
(二)强化知识产权滥用的司法审查
从法理学角度看,有权利就可能存在权利滥用。知识产权滥用作为权利滥用的范畴也不例外。近些年来,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看,如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已成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维护公平竞争的热门话题,时常可以见到典型案例。鉴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存在的客观性及其危害性,我国相关司法政策也对这种行为给予了否定性评价并进行了规范。例如,2007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法发〔2007〕1号)指出:要“正确处理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公众利益的关系、激励科技创新和鼓励科技运用的关系,既要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也要制止权利滥用和非法垄断。”针对禁止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具体内容则指出:“准确界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权利界限,依法审查和支持当事人的在先权、先用权、公知技术、禁止反悔、合理使用、正当使用等抗辩事由;制止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的行为,依法认定限制研发、强制回授、阻碍实施、搭售、限购和禁止有效性质疑等技术合同无效事由,维护技术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权利人滥用侵权警告和滥用诉权,完善确认不侵权诉讼和滥诉反赔制度。”
在涉及知识产权滥用的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应重视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重视案件反映的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政策。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其特有的公共政策,并且与反垄断法在促进公平竞争与创新、效率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基于此,在涉及知识产权滥用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仅构成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内的滥用行为,还是构成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都应当审视涉案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背后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对此,国外涉及知识产权滥用的相关案例即有明确态度,对我国相关知识产权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在前面提到的Morton Salt Co. v. G.S. Suppiger Co.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论被告是否遭受滥用专利权之害,原告此种违反授予专利权公共政策的行为,使其不再有资格主张侵权诉讼,且不能主张对所授予的专利权的保护。” [78]在后来的Lasercomb案中,法院依旧重审了公共政策的考量标准,即问题并不在于利用著作权的方式是否违反反垄断法,而是在于其是否违反了著作权保护所体现的公共政策。[79]在美国的著作权法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促进知识传播、保留公共领域和保护创作者这“3P”[80]政策。这些政策背后反映了著作权立法宗旨和功能。在涉及知识产权滥用的案件处理中,要求重视案件反映的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政策,本质上是要求对于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性质符合知识产权立法保护宗旨,不能以违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宗旨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而言,相关的公共政策涉及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与正当竞争,以及促进创新成果推广运用等内容,最终体现为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在涉及与知识产权滥用相关的案件的处理时,对于相关行为的定性,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出发,有利于法院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其二,注意区分一般意义上的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与滥用知识产权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正确适用法律。
从前面的讨论可知,知识产权滥用并非一定违反反垄断法,只有滥用知识产权行为构成排除、限制竞争时,才需要反垄断法介入。换言之,当滥用知识产权行为能够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内解决时,可以直接依据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解决,而不必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处理。从国外司法实践看,在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存在一种观点,即被告若利用著作权滥用理论获胜,必须证明原告行使著作权的方式违背了反垄断法的规定。[81] 有学者认为,在美国涉及知识产权滥用这一领域,通常被认为属于反垄断法领域,并且主要是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案(Sherman and Clayton Acts)的规制。[82]另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否接受基于公共政策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抗辩,美国很多法院都接受直接基于反垄断的抗辩,不同之处则在于反垄断抗辩所援用的是传统的竞争法原则。[83]不过,也有法院认为,如果缺乏违反反垄断法的证据,法院认定著作权人滥用其权利时,应当认定其以某种方式非法扩大其法定的垄断权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违背了著作权法赖以实现的公共政策。[84]
就我国涉及知识产权滥用的司法实践而言,笔者认为注意区分一般意义上的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与滥用知识产权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正确适用法律。实际上,如前所述,我国相关立法对于两者进行了区分,只不过前者规定较为分散,后者集中体现于现行《反垄断法》第68条规定以及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界定的部门规章中。对于前者,适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规定,明确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即可,如针对限制社会公众合理使用的权利的一般的滥用著作权的案件,直接判决被告侵权不成立。对于后者,则需要结合个案中的行使知识产权行为对于竞争、创新和效率的影响,尤其是是否存在通过垄断协议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公平地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及其后果。这种在司法实践中的“二分”,有利于明确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性质和定位,从而更准确地适用法律。
其三,慎重对待案件中被告的知识产权滥用抗辩。
前面对于知识产权滥用历史考察表明,包括专利权滥用、著作权滥用等知识产权滥用是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特别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产生和发展的作为被告抗辩侵权的主要理由之一。[85]一旦被告提出原告滥用知识产权并且获得法院支持,则在个案中相关知识产权将不再予以执行。当然,这种抗辩也只具有个案的效力。在其他案件中,知识产权人仍然能够根据侵权证据主张被告侵权。[86]从国外知识产权案件中涉及知识产权滥用抗辩理由的情况看,首先在专利案件中适用这一原则。[87]后来,权利滥用抗辩逐渐在著作权保护领域被引进,并且日益普遍化,甚至成为侵权诉讼被告对抗原告的一大武器。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Paramount Pictures, Inc.案[88]以及United States v. Loew's, Inc.[89]案中,法院都支持了被告提出的原告存在滥用著作权的抗辩。在前面提到的在Lasercomb America, Inc. v. Reynolds一案中,法院明确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应用于著作权领域。法院认为这一原则“天然地”存在于著作权法中,并认定原告在行使著作权时企图突破权利保护范围会构成对竞争的限制。[90]
值得指出的是,在涉及被告主张作为知识产权人的原告存在滥用知识产权行为时,对于原告是否真正存在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慎重把握。在相关学术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均提出了知识产权滥用抗辩主张可能被“滥用”的可能性以及这一主张对于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以著作权滥用为例,国内有学者指出:“版权滥用”一般仅为被告的抗辩事由。如果其成为独立的诉由,极有可能导致版权相对人滥诉。[91]国外学者则认为,著作权滥用抗辩理论的发展不仅打破了作者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而且对于著作权领域带来了较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因素。著作权滥用抗辩主张成功后,会排除对任何侵权人行使禁止权,而这可能导致著作权价值变得一文不值。[92]上述对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滥用抗辩可能被滥用及其负面影响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提起某一知识产权滥用抗辩主张,只要能够界分行使知识产权行使的性质,结合行为对竞争、创新和效率以及对不同主体的影响,就能够判别这一抗辩主张是否成立。总体上,对于被告提出某一知识产权滥用抗辩主张,应当慎重对待,既要防止被告滥用这一抗辩,也要排除真正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三)强化行政监管与行业协会监管
基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很大一部分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对于这类行为的规制,除了前述立法和司法适用中进行规制外,按照法律规定强化行政监管与行业协会监管也十分重要。从2022年修正的现行《反垄断法》规定看,在新增的内容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了对公平竞争审查、强化反垄断监管力量和对涉嫌垄断行为的依法调查。[93]这些新增加的规定,连同其他规定,构成了对垄断行为行政监管的制度体系。对于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而言,上述规定同样适用。强化对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政监管,利用行政强制力,必能在相当大程度上规制和遏制这类行为。
此外,在规制垄断行为方面,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现行《反垄断法》第14条规定:“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争,合规经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就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特别是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而言,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同样应当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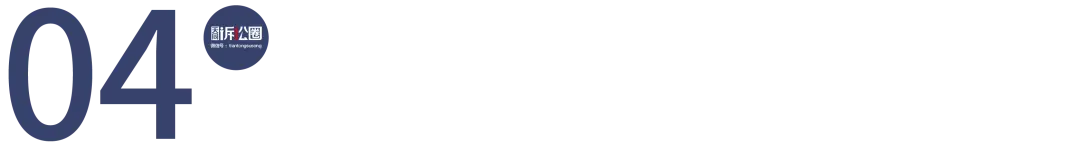
结 语
作为权利滥用范畴的知识产权滥用是伴随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副产品”。知识产权滥用既是一个在理论上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正常情况下,知识产权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其他任何人未经权利人许可、也没有法律特别规定时,都不得行使这一专有权利。但是,在滥用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直接违背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宗旨,并且有损于其他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乃至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此时就需要对这一行为进行干预,在个案中否定行使权利的效力。基于知识产权滥用对市场竞争的不同影响,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可以从一般意义上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内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和反垄断法意义上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两个层面加以考量。这两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均具有相应的表现形式和认定条件。在当前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还涉及数据、算法和平台规则中的权利滥用问题。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在促进公平竞争、创新和效率,以及维护消费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价值目标共通性,无论属于何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都可以基于公共政策目标加以界定。总的来说,在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司法保护中,需要合理界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边界范围,在充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滥用知识产权之间实现平衡,实现知识产权立法宗旨。
注释:
[1] 参见张以标:《知识产权滥用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科技与法律》2019年第2期,第52-60页。
[2] 参见费安玲:《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理念》,载《知识产权》2008年第3期,第3-10页。
[3] 参见Roger Arar, Redefining Copyright Misuse, 81 Colum. L. Rev. 1291 (1981).
[4] 李顺德:《知识产权保护与防止滥用》,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9期,第3-11页,第106页。
[5] 相关案例,参见Keystone Driller Co. v. General Excavator Co., 290 U.S. 240 (1933);Republic Molding Corp. v. B.W. Photo Utils., 319 F.2d 347 (9th Cir. 1963);Mitchell Bros. Film Group v. Cinema Adult Theater, 604 F.2d 852, 863 (5th Cir. 1979); F.E.L. Publications, Ltd. v. Catholic Bishop of Chicago, 506 F. Supp. 1127, 1137 (N.D. Ill. 1981).
[6] Keystone Driller Co. v. General Excavator Co., 290 U.S. 240, 245 (1933).
[7] 290 U.S. 240 (1933).
[8] 604 F.2d at 865.
[9] 314 U. S. 488,492 (1942).
[10] Morton Salt,314 U.S. at 488(1942).
[11], 352 U.S. 457, 465 (1956).
[12] [1940] SCR 218, [1940] 1 DLR 625.
[13] Martin Twigg, Copyright Misuse: Protecting Copyright in Canada from Overreach and Abuse, 21 Dalhousie J. Legal Stud. 31 (2012).
[14] 441 U.S. 1 (1979).
[15] 911 F. 2d 970 ( 4th Cir. 1990).
[16] 911 F. 2d 970,978( 4th Cir. 1990).
[17] 参见易继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第39-52页。
[18] U.S. Copyright Office, General Guide to the Copyright Act of 1976 1:1 (1977).
[19] Unites States v. Paramount Pictures, Inc.,334 U.S. 131(1948).另可参见Twentieth Century Music Corp. v. Aiken, 422 U.S. 151, 156 (1975).
[20] 347 U. S. 201, 219 (1954).
[21] 参见334 U.S. 131, 158 (1948).
[22] H. R. Rep. No. 2222, 60th, Cong., 2d Sess 7 (1909).
[23] 121 F.3d 516 (1997).
[24] 陈剑玲:“论版权滥用之判断标准”,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55-59页。
[25] 易继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第39-52页。
[26] C John T. Cross & Peter K. Yu, Competition Law and Copyright Misuse, 56 Drake L. Rev. 427 (2008).
[27] Aaron Xavier Fellmeth, Copyright Misuse and the Limit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nopoly, 6 J. Intell. Prop. L. 1 (1998).
[28] 卢海君、任寰:“版权滥用泛在之证伪”,载《知识产权》2022年第1期,第50-62页。
[29] 相关案例,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民终998号民事判决书。
[30] 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反思与完善 法理・立法・司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年版,第114-116页。
[3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11号行政判决书。
[32]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1) 一中知初字第343号民事判决书。
[33] 参见杜爱霞、冯晓青:“论侵害知识产权法中公有领域的民事责任”,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56-67页。
[34] 相关案例,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498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551号民事判决书。
[35] 我国现行《商标法》第7条即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3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96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82号: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37]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68号民事判决书。
[38]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7民终2958号民事判决书。
[39] 还有一种情况是,发出侵权警告的知识产权人获得的知识产权本就存在瑕疵,如知识产权人以不公平竞争为目的,通过窃取他人在先成果或者将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申请专利,在获得权利后即迫不及待地向众多生产经营者滥发警告函。这种情况,属于更明显的权利滥用行为。
[40]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66号民事裁定书。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5期。
[41] 其他案例,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407号民事判决书、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4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
[42] Competition Act § 79(5).
[43] 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保护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前言第1页。
[44]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中国语境解读》,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第15-26页。
[45] 冯晓青:《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之维》,载《现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171-190页。
[46] 参见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第四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47] 参见Aaron Xavier Fellmeth, Copyright Misuse and the Limit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nopoly, 6 J. Intell. Prop. L. 1 (1998).
[48] 参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40条。
[49] 相关研究,参见刘沐霖:“专利许可协议中回授条款的反垄断经济学分析”,载《当代经济》2016年第17期。
[50] 相关研究,参见张海涛:“美欧‘不质疑条款’效力比较及其借鉴”,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8期。
[51] 从国外司法实践看,限制经营者开发具有竞争性的产品也属于知识产权滥用的范畴。参见Practice Management Info. Corp. v.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21 F.3d 516 (1997).
[52] 相关案例,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151号民事判决书。
[53] 相关案例,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
[54] 邓林:“滥用知识产权及市场 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载《对外经贸》2019年第7期。
[55] 相关案例,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湘高法民三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民终字第489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1)桂民三终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等。
[56] 320 U.S. 661 (1944).
[57] 相关案例,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519号民事判决书。
[58] IMS Health GmbH v. NDC Health GmbH, Case C-418/01 (2004).
[59] 参见Dir. of Investigation & Research v. Warner Music Can. Ltd., [1997] 78 C.P.R.3d 321, 324 (Competition Trib.) (Can.).
[60] 参见Thomas M. Susman, Tying, Refusals to License, and Copyright Misuse: The Patent Misuse Model, 36 J. Copyright Soc'y U.S.A. 300 (1989).
[61] 314 U.S. 488 (1942).
[62] 166 F.3d 772(5th Cir. 1999).
[63] 356 U.S. 1, 5-6 (1958).
[64] 参见Jefferson Parish Hosp. Dist. No. 2 v. Hyde, 466 U.S. 2, 14-15 (1984).
[65]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47 (D.C. Cir. 2001).
[66] 相关案例,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1519号民事判决书。
[67] 相关案例,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4942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民终4295号民事判决书、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4122号民事判决书。
[68] 参见Ramsey Hanna, Misusing Antitrust: The Search for Functional Copyright Misuse Standards, 46 Stan. L. Rev. 401 (1994).
[69] 参见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第四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61-82页。
[70] 参见现行《商标法》第4条、第45条、第47条、第68条第1款。
[71] 参见Automatic Radio Mfg. Co.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 339 U.S. 827, 832-33 (1950).
[72] 参见Senza-Gel Corp. v. Seiffhart,803 F.2d 661, 668 (Fed. Cir. 1986).
[73] 参见American Securit Co. v. Hamilton Glass Co., 254 F.2d 889, 895 (7th Cir. 1958).
[74] 参见Hartford- Empire Co. v. United States, 323 U.S. 386, 4,5 (1945).
[75] Ramsey Hanna, Misusing Antitrust: The Search for Functional Copyright Misuse Standards, 46 Stan. L. Rev. 401 (1994).
[76] Ramsey Hanna, Misusing Antitrust: The Search for Functional Copyright Misuse Standards, 46 Stan. L. Rev. 401 (1994).
[77] John J. Flynn & James F. Ponsoldt, Legal Reasoning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Vertical Restraints: The Limita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Resolution of Antitrust Disputes, 62 N.Y.U. L. Rv. 1125, 1136-39 (1987).
[78] 314 U.S. 488(1942).
[79] Lasercomb Am., Inc. v. Reynolds, 911 F.2d 970, 978 (4th Cir. 1990).
[80] 即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author.
[81] 参见Saturday Evening Post Co. v. Rumbleseat Press, Inc., 816 F.2d 1191, 1200 (7th Cir. 1987);Basic Books, Inc. v. Kinko's Graphics Corp., 758 F. Supp. 1522, 1538-39 (S.D.N.Y. 1991).
[82] C John T. Cross & Peter K. Yu, Competition Law and Copyright Misuse, 56 Drake L. Rev. 427 (2008).
[83] Aaron Xavier Fellmeth, Copyright Misuse and the Limit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nopoly, 6 J. Intell. Prop. L. 1 (1998).
[84] 参见Lasercomb Am., Inc. v. Reynolds, 911 F.2d 970,978 (4th Cir. 1990); National Cable Television Ass'n v. BMI, 772 F. Supp. 614, 652 (D.D.C. 1991).
[85] 参见Melville B. Nimmer &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2009), § 13.09;illiam J;Nicoson, Misuse of the Misuse Doctrine in Infringement Actions, 9 UCLA L. Rev. 76, 77 (1962).
[86] 参见Alden-Rochelle, Inc. v. ASCAP, 80 F. Supp. 900, 904 (S.D.N.Y. 1948).
[87] 参见Walker Process Equip., Inc. v. Food Mach. & Chem. Corp., 382 U.S. 172, 176 (1965).
[88] 334 U.S. 131 (1948).
[89] 371 U.S. 38 (1962).
[90] 911 F. 2d 970(4th Cir. 1990).
[91] 卢海君、任寰:“版权滥用泛在之证伪”,载《知识产权》2022年第1期,第50-62页。
[92] Ramsey Hanna, Misusing Antitrust: The Search for Functional Copyright Misuse Standards, 46 Stan. L. Rev. 401 (1994).
[93] 参见现行《反垄断法》第5条、第11条、第54条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