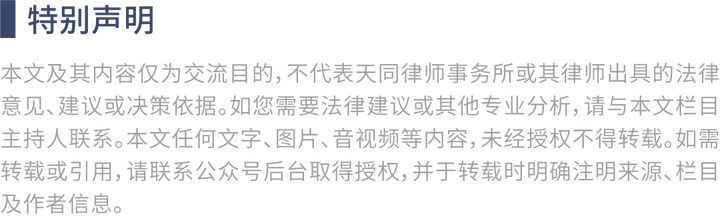本文共计35,387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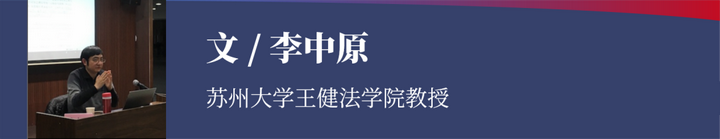
注:本文发表于《法学家》 2022年第2期,载第62页。
摘要:构建我国民法上有关连带债务人之间追偿权的法教义学体系应以《民法典》第519条为基础。此种追偿权应当是一种以公平为基础,以不当得利请求权和代位权为主要内容的复合型的债权请求权。追偿权行使条件的否定说模式在现行体制下难以实现。追偿权的行使范围包括履行债务人超过自己份额承担的债务本金、期内利息、共同的迟延履行利息、超出费损以及上述诸项的追偿利息。追偿权主要受到债权人的优先利益和其他债务人利益的限制。后者的限制主要表现为排除连带性和抗辩转移。抗辩转移效力应当适用于抵销权。
关键词:连带债务 追偿权 不当得利 代位权
连带债务包括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外部层面,任一连带债务人的履行(包括提存、抵销等替代履行形式)即导致全体债务人对债权人免责;但由此在内部关系上导致实际承担债务超过自己份额的连带债务人有权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78条第2款、第519条第2款、第520条第1款],此之谓连带债务人之间的“追偿权”。追偿权在性质上实为连带债务的外部债权关系实现后继发产生的“追偿债权”。此次《民法典》借鉴比较法上的一般做法为追偿权设置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519条。基于《民法典》第468条的规定,第519条乃是因合同或非因合同而产生的各种连带债务之内部追偿权的一般规则。不仅如此,鉴于连带债务在民法上的基础性地位,其内部追偿规则同样构成了其他类型的多数人之债以及民法其他领域中追偿关系的类推基础。因此,第519条将影响到整个中国民法上之追偿权的基本体制。但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于连带债务的内部关系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司法实务界对于第519条背后的解释论基础及其操作方案和特殊变例尚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比如,此种追偿权与代位(求偿)权是何关系?为什么只有在实际承担债务超过自己的份额时方可追偿?追偿的范围可能涉及哪些特殊利益?在连带债务人之一仅部分履行而其他债务人为两人以上时,前者对后者的追偿份额应如何分配?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事由是否均可对抗追偿权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予以澄清,势必影响到追偿权的司法实践效果。为此,必须在理论上以第519条为基础构建我国民法上有关连带债务人之间追偿权的完备的法教义学体系。总体来讲,这一法教义学体系可以从追偿权的理论基础、追偿权的行使条件与范围以及追偿权的限制等方面逐次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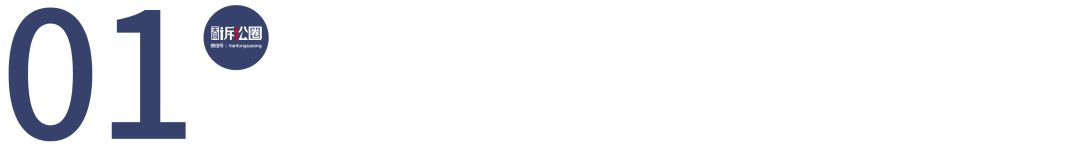
追偿权的理论基础
(一)理论现状和历史渊源
由于在绝大多数场合连带债务人之间并没有关于追偿的约定,为了解释连带债务人之间进行追偿的正当性依据,大陆法系的传统民法理论形成了众多学说,国内(包括台湾地区)学界自民国时期以来陆续引进,目前仍具影响的有六种学说,即当然存在说、主观共同关系说、相互保证说、无因管理说、不当得利说以及公平分担说。[1]对此国内学界多有介绍,此处不作赘述。在肯定追偿权的正当性的前提下,大陆法系的民法教义学还必须面对“双重请求权(基础)”的理论困惑。在传统民法上,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内部分担或补偿关系除了依据追偿权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请求权基础——代位权(或代位求偿权)。前者被认为是债务人自己固有的权利;后者则源自债权人的权利。确切地说,履行债务人向其他债务人请求分担或补偿乃是代位行使债权人的权利,亦谓之“债权的法定转移”。[2]这样的“双重请求权(基础)”结构——其实质就是“请求权竞合”(Anspruchskonkurrenz)[3]——给法律适用带来了不小的困惑。为此,大陆法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三种方案在当前中国大陆民法理论界也都拥有各自的支持者。其一,单一适用。这一方案在法国居于主导地位。法国最高法院在1977年6月7日的判决中采纳了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追偿诉权系基于自己权利的观点,[4]但法国学说上的主流观点则倾向于此种诉权不是独立的自己权利,而是基于对受害人权利的代位。[5]据此,该种方案实质上否认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分担或补偿关系存在双重请求权基础,而只承认单一请求权基础,只不过具体依据的是自己权利还是代位权尚有争议罢了。在中国大陆,有学者主张追偿权产生的基础是法律规定,而非债权法定转移的结果。[6]该观点与上述法国最高法院的观点基本一致。其二,择一适用。这一方案认为追偿权和代位权系基于同一目的而并存之请求权,权利人仅得择一行使。这一方案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意大利的民法理论界较有影响,[7]《欧洲侵权法原则》(PETL, 2005)也倾向于这一方案。[8]在中国大陆,择一适用的方案也为个别学者所支持。[9]其三,结合适用。这是目前大陆法系的主流做法,该方案主张追偿权人(即履行债务人)在追偿范围内相应享有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包括担保权利)和诉讼权利。[10]其要旨一方面在于将代位权作为追偿权的“补强”形式(体现为担保等从权利的转移),另一方面则在于将代位权的产生和效力限制在追偿权的范围内。代位权的行使以追偿权的合法成立为前提,没有追偿权的履行债务人也不得行使代位权;而代位权的效力范围以追偿权的范围为限,代位权(无论来自约定还是法定)不能使履行债务人获得超过其通过追偿应得的利益。[11]《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 2003)、《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 2009)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PICC, 2010)采用的也是这一方案。[12]在中国大陆,结合适用方案亦为学界的主流意见。[13]追偿权在理论基础上的复杂性实有其历史的渊源。由于早期罗马法认为任一连带债务人实施全部清偿系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原则上不承认连带债务人之间的追偿权。但是,如果连带债务人之间存在其他特定的法律关系,比如合伙、共有等,则可以依据这些具体的法律关系主张追偿。因此连带债务人之间的追偿最初乃基于具体关系中的不同诉权,比如合伙之诉、遗产分割之诉、共同财产分割之诉、委托之诉以及无因管理之诉等;古典晚期开始承认共同监护人之间的“诉权转让照顾”及其扩用之诉,这被认为是现代“债权的法定转移”(法定代位权)学说的渊源;同时期还出现了要式口约的共同允诺人之间具有相互保证关系的观点(出自法学家帕比尼安,D.45,2,11.)以及共同保证人之间的“诉权划分照顾”制度(优帝时期被扩用于共同监护人),这构成了“相互保证说”的源头;连带债务人之间的追偿关系可能直到优帝时期才得以普遍确立,但仍须借助于上述具体诉权的扩用形式(actio utilis)。[14]建立在这些诉权基础之上的追偿权理论经由中世纪的注释法学派的传承一直延续到近代法学。[15]17到19世纪,以朴蒂埃、萨维尼等为代表的法国和德国学者正是在这些诉权规则的基础上构建起了连带债务之内部分担或补偿关系的理论基础。[16]由此可见,追偿权复杂的理论基础实为罗马法传统的历史“遗存”:诸如无因管理、债权的法定转移、相互保证等现代法学上的解释学说都渊源于罗马法上的具体诉权理论;在此基础上,近代学者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学说,比如不当得利、当然追偿、主观共同关系以及公平分担;随着法定的追偿权在近代各国民法的确立,上述学说基本“沦为”证成追偿权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只有代位权(债权的法定转移)仍然保持独立,这就形成了目前“双重请求权(基础)”的法律构造。
(二)学说研判和理论基础的构建
以上诸种学说和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向具体民法规则寻求理论根据、向连带性本身寻求理论根据或者向民法基本原则寻求理论根据。相互保证说、无因管理说、不当得利说以及代位权(或债权的法定转移)理论属于第一类。相互保证说系将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类推保证关系,这基本可以解释追偿权所涉之问题,但类推方法的运用应以现行法规范存在无法涵盖之漏洞为前提;无因管理说的成立须以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为前提,而连带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系基于其法定的义务,难以成立无因管理;相形之下,不当得利说既可以在现行法体系中找到有效的规范渊源,同时又具有较为全面的解释力。[17]一方面,不当得利在法律上设有明确的规定,这就避免了诉诸类推或者民法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不当得利不仅可以解释追偿权的一般规则,而且它还可以解释追偿权在行使中的特殊限制规则(包括排除连带性和抗辩转移)。不当得利说唯一的缺陷在于,它不足以将追偿权的效力扩及至原债权之担保(该缺陷同样存在于相互保证说和无因管理说)——这只有通过代位权予以实现。但是,代位权理论也存在自身的理论瓶颈。其一,代位权不能解释追偿的排除连带性。既然履行债务人承袭了债权人对其他债务人的权利,而该权利是整体性的,那为什么履行债务人只能在其他债务人各自份额的范围内实施追偿呢?其二,代位权不能完全解释追偿的范围。履行债务人向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分担或补偿的范围原则上在债权人的权利范围内,但追偿中涉及的相关费用、损失或者利息则可能超出债权人的权利范围,这无法通过债权的法定转移学说予以解释。其三,代位权无法解释其本身的正当性。履行债务人为何可以代行债权人之权利,这是代位权本身所无法解释的。相形之下,前两点缺陷,不当得利说恰恰可以解释,而第三点缺陷则需要借助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予以解释——允许履行债务人代行债权人的权利,是为了确保前者与其他债务人之间的公平分担,尤其是在其他债务人欠缺偿还能力时充分保障前者之分担利益的实现。当然存在说和主观共同关系说属于第二类,二者实质上并无差异:均将追偿权的基础归于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内部份额关系。换句话说,连带债务的内部追偿权之所以“当然存在”,恰恰源于连带债务人之间基于内部份额的“主观共同关系”。[18]由于现代大陆法系的民法典(包括我国《民法典》)上都对连带之债的内部份额和追偿权设置了专门规定,[19]罗马法所面临的困境——必须到连带性以外寻求追偿的规范依据(或请求权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因此,第二类学说在表面上更加符合当今的法制状况。但如果深究此类规范依据背后的理论基础就会发现:连带之债作为一种整体性关系,其内部划分份额的正当性何在?为何实际承担债务超过内部份额的连带债务人“当然”有权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显然这两种学说均不足以解释,而这只能诉诸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和更为具体的不当得利规则。由此可见,第二类学说仅仅是对追偿权的现实规范基础的浅层反映,并不足以证成追偿权在理论基础上所谓的固有性和独立性。作为第三类的解释学说,公平分担说恰恰是将追偿权的理论根据上溯到民法基本原则之一——公平原则,这是唯一全面而根本的解释。实质上,公平分担的理念原本就蕴含在上述多种解释学说之中,[20]成为这些学说阐释追偿权之正当性的根本依据。但诉诸公平原则的缺陷在于它无法为构建追偿权的效力内容提供可操作的参考模型。法的原则的抽象性和非规范性决定了“公平”只能作为规范构建的价值基础,而无法提供具体的技术方案。总体来看,以上三类学说和理论均有着不同程度的解释力,但又都存在着各自的短板。相形之下,第一类学说中的不当得利说和代位权理论的结合较为完整的解释了此种分担或补偿请求权的效力内容,第三类学说则从公平原则出发佐证了此种分担或补偿请求权的正当性。因此,我国民法上追偿权之理论基础的构建应当主要以这三种学说和理论的结合为基础。就理论基础的构建,《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规定,履行债务人有权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并相应地享有债权人的权利。”该规定在追偿权之外同时承认了代位权的实质内容,就表述方式来看,立法明显倾向于上述“结合适用”方案。[21]但综合考虑以下诸方面的理由,传统民法上的双重请求权(基础)的解释构造在我国民法教义学的话语体系中有必要进行适当的统一化改造。首先,追偿权与代位权相伴而生、不可分离,这是二者实现统一的必要前提。以请求权竞合的典型形式——违约和侵权的竞合——为例,在实践上,违约并非必然伴随着侵权,反之亦然。相形之下,追偿权和代位权则正好相反。代位权的行使一定是以追偿权的合法成立为前提,而追偿权人也必然享有代位权。其次,追偿权内容的可塑性使其在理论构造上有了涵盖代位权的可能。传统民法用追偿权和代位权的相互补充(“结合适用”方案)来确定履行债务人主张分担或补偿时的权利范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代位权亦不失为追偿权的众多理论根据之一和补强形式。根据上文分析,“结合适用”系统中的追偿权,其效力内容存在多种解释学说,其中尤以不当得利说为佳,但仍须代位权予以补强,二者结合方得涵盖此种分担或补偿关系的总体内容。既然如此,更为简捷的方案是将追偿权作为此种“复合型权利”的总称,其运作机制通过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代位权的组合来实现,具体要点分述如下。(1)追偿权的成立基础取决于不当得利。在此组合系统中,追偿权的成立必须以履行债务人与其他连带债务人之间成立不当得利关系为前提,而代位权的行使又以追偿权的成立为前提,因此,代位权的行使也必须以不当得利的成立为前提。(2)追偿权的效力内容主要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代位权的结合。在此结合中,不当得利请求权基本确定了追偿权的效力范围,代位权作为追偿权的效力内容(或效果)之一,其首要功能在于补强不当得利请求权所欠缺的担保功能,二者可由追偿权人择一行使。就此而言,不当得利虽然不能涵盖追偿权的全部内容,但仍不失为整个追偿权的核心和基础,而代位权则是必要的补充。(3)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虽因理论基础的选择而在计算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在效果上差异不大。依不当得利进行追偿与依代位权进行追偿,诉讼时效在计算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我国而言,该差异主要体现在时效的起算点上:前者从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或履行债务人清偿日之中较后者开始起算,后者基于“债权法定转移”(或代行债权人权利)的属性,其时效起算点溯及至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之日。[22]相形之下,前者的起算点肯定不会早于后者,对追偿权人更为有利。但实际上二者在效果上的差异并不大——尤其是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依不当得利进行追偿,虽然独立的时效期间更有利于追偿权人,但由于抗辩转移规则的作用,追偿权仍然受制于债权的诉讼时效——其他连带债务人可以债权罹于诉讼时效为由对抗追偿;而依代位权进行追偿虽然在时效期间上必须延续债权的时效期间,但追偿权人的履行及其引发的债权转移将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这也将导致代位权的时效期间重新起算。[23]综合以上分析,我国民法上连带债务人之间的追偿权应当是一种以公平为基础,以不当得利请求权和代位权为主要内容的复合型债权请求权。此追偿权作为两种“元权利”的组合形式,其运作过程中的具体规则仍须借助不当得利理论或者代位权理论予以解释或证成。可见,经由统一化改造后的追偿权并未完全抛弃传统的双重请求权(基础)的解释构造,仅仅是将传统民法上追偿权与代位权的竞合关系改造为在追偿权的统一体系下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代位权的组合关系。需要补充的是,以不当得利请求权和代位权作为追偿权的理论基础并不排除在极其个别的场合,侵权和违约亦可成为追偿权的基础。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追偿权的理论基础仅适用于连带债务人之间没有特别约定的场合,如果连带债务人之间针对追偿有特别约定,则可以排除上述理论的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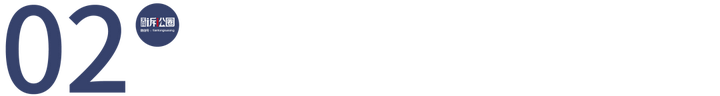
追偿权的行使
(一)追偿权的行使条件
根据《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之规定,我国对于追偿权的行使条件采用的是比较法上最为通行的一种模式:任一债务人的给付必须超过其内部份额,方可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采用这一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包括德国、瑞士、荷兰、美国,[24]此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欧洲合同法原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也采这一模式。[25]对于追偿条件,比较法上还存在另外两种模式:其一,任一债务人必须履行全部给付后方可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前)第1214条第1款和《意大利民法典》第1299条第1款采此模式,但两国在立法修改和司法实践中都放弃了这一做法,转而采用上述通行模式;[26]其二,即使任一债务人的给付低于其应负担之份额,也可以按照各自的分担比例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2017年修法后的《日本民法典》第442条第1款明确采用此模式,[27]该模式在我国台湾学界也颇有影响。[28]由此可见,主要矛盾存在于通行模式与以日本为代表的模式之间,争议的关键在于履行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是否必须以其实际承担债务超过自己的份额为前提。通行模式采肯定说(或积极说),日本模式则采否定说(或消极说)。我国《民法典》选择前者乃是明智之举,来自国内学界的解释理由通常强调否定说可能导致循环追偿,使法律关系复杂化。[29]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否定说模式下的追偿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理由如下。其一,在追偿“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现行体制下(《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其他连带债务人如资力不足,必须优先向债权人清偿,直至债权得以全部满足,方可向追偿权人(履行债务人)履行。而一旦该清偿完成,其他连带债务人亦可对履行债务人反向追偿,为避免反复追偿,势必进行抵销操作,而彼此抵销之后果与通行的肯定说实无差异。其二,如果债权人放弃对其他连带债务人的给付请求,则属于免除范畴,其他连带债务人可以此等对抗债权人的理由来对抗履行债务人的追偿权(《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履行债务人则必须在自己的份额范围内承担债务(《民法典》第520条第2款),追偿权仍将落空。其三,如果在履行债务人部分履行后(剩余)债权因罹于诉讼时效遭到各连带债务人的抗辩而事实上沦为无法实现时,有学者主张此种情况下,虽然前者的给付低于其应负担之份额,但应当例外的允许履行债务人向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分担。[30]此种假设成立的前提是当(剩余)债权罹于诉讼时效之际追偿权仍未罹于诉讼时效。但是,该前提是不成立的:在我国的诉讼时效体制下,履行债务人的部分履行导致债权的诉讼时效相对于该债务人中断,[31]而发生于连带债务人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必然导致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同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32]基于此,重新计算的债权的诉讼时效与履行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都将从前述之部分履行之日起算且期间相同。所以,债权罹于诉讼时效之际追偿权也必然罹于诉讼时效。最后,作为通行模式(肯定说)的例外,如果对于追偿权的行使条件连带债务人之间另有约定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则应当以该约定或者法定为准。
(二)追偿权的行使范围
《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仅仅规定,实际承担债务超过自己份额的连带债务人“有权就超出部分”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此种简略表述是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模式之一。[33]比较立法例上对追偿范围的表述还存在另外两种模式:其一,在“超出部分”之外,增加“合理费用”;[34]其二,将“超出部分”之外的“合理费用”进一步细化为“利息、费用及损失”。[35]此外,诸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对追偿范围的规定并不明确。[36]总体来看,履行债务人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的范围可能涉及如下项目:超出部分、相关费用和损失、追偿利息。1.超出部分。所谓“超出部分”是指履行债务人已经向债权人给付,但按照内部份额应当由其他连带债务人承担的债务部分,在范围上包括债务的本金、期内利息以及迟延履行利息这三项中应当由其他连带债务人承担的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期内利息仅限于借款债务领域,而迟延履行利息(或称逾期利息)尚须区分共同的迟延履行利息和单独的迟延履行利息。共同的迟延履行利息系连带债务人共同迟延所致,须由所有债务人按份额分担;而单独的迟延履行利息则系履行债务人个人原因所致。比如,履行债务人在法院判决指定的付款期间届满后拖延执行判决款项的迟延利息,该部分利息不得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2.相关费用和损失。相关费用和损失均为追偿权人因履行债务导致的财产减少,但由于并非流向债权人,所以有别于上述“超出部分”。费用与损失的区别仅在于前者系追偿权人自愿支出,而后者则非基于追偿权人的意思。[37]由于此类费用和损失系因履行债务而发生,因此对于超出追偿权人应当承担之部分须由其他连带债务人分担。在比较法理论上,费用涉及的范围主要包括:履行债务人为履行债务支出的汇费、包装费、运输费等履行费用。而损失涉及的范围主要包括:履行债务人在债权人提起的清偿诉讼中承担的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为履行债务而(低价)变卖财产或高利借贷所遭受的经济损失。[38]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费用和损失主要为学理和判例所发展,在立法上鲜有规定。[39]对于上述费用和损失是否均可纳入追偿范围,理论上尚须区分该费用或损失是否源自履行债务人应当单独负责之事由。[40]但该原则在具体认定上并不统一,目前大体存在三种不同的方案。其一,倾向于上述所有的费用和损失都可以追偿,因为它们均为清偿债务所“不可避免”。[41]其二,主张履行费用和损失中的诉讼费用、执行费用可以追偿,但(低价)变卖财产、高利借贷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不得追偿。[42]其三,主张客观上必须支付的费用可以追偿,“必须支付”的标准是其他连带债务人如果实施清偿或其他免责行为亦须支付;损失则须由其他连带债务人不履行其负担部分之协力义务所致方可追偿。[43]在上述三种方案中,汇费、包装费、运输费等履行费用被纳入追偿范围争议不大,但根据“不可避免”或“必须支付”的总体要求,第三种方案所提出的“其他连带债务人亦须支付”的标准应当坚持。这实质上是将履行费用的追偿限制在不当得利的范围内,这样也符合追偿权的理论基础。对于超出其他连带债务人“得利”范围的履行费用,一般不得追偿;但如系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过错所致,可依一般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进行追偿——在此,侵权和违约亦为追偿的基础。[44]就我国法院的审判习惯而言,如果连带债务人共同被诉(含被申请执行),诉讼费用、执行费用当然须分担并准予追偿;但如果只有连带债务人之一被诉(含被申请执行),诉讼费用、执行费用则一般不纳入追偿范围。[45]但从理论上讲,单独被诉(含被申请执行)与共同被诉(含被申请执行)实乃债权人的选择,如果因此导致连带债务人在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承担上的差异,大多数情况下难谓公允:单独被诉(含被申请执行)场合,实由一债务人承担了原本应由全体债务人承担的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这同样符合不当得利的追偿权基础。因此,无论连带债务人共同被诉或单独被诉,诉讼费用、执行费用原则上应当纳入追偿范围,除非完全系可归责于一债务人之事由而负担之诉讼费用或执行费用。比如债权人单独起诉连带债务人之一获得胜诉,后者在判决履行期限内未主动履行,导致前者申请强制执行所生之执行费用;或者连带债务人之一拒不履行全体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导致债权人起诉而产生之诉讼费用。履行债务人因贱卖财产或高利借贷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是争议的焦点。这两项损失虽系因履行债务而发生,甚至对履行债务人而言也属“不可避免”,但从追偿权的理论基础出发,这两项损失的发生并未导致其他连带债务人“得利”的增加——其他连带债务人因此获得的免责利益仍限于上述的“超出部分”;而如果要依据可归责于其他连带债务人的事由(即过错)进行追偿,那就必须以第三种方案中“连带债务人之间的相互协力义务”为前提,而此义务在我国尚无法律依据,也难以得到我国理论和实践的认可。正如反对意见所言,任一连带债务人承担全部给付本属其固有之债务,在资力不足时贱卖财产或高利借贷用以还债本属债务人所负无限责任的应有之义。[46]将此损失归咎于其他连带债务人之不(协力)配合,不仅缺乏现行法依据,在法理上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总之,只有不可避免的汇费、包装费、运输费等履行费用以及无法归责于连带债务人之一的原因导致的诉讼费用、执行费用才可以按照份额比例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下文统称为“超出费损”)。3.追偿利息。追偿利息是指其他连带债务人须向履行债务人返还的超出部分和超出费损的资金占用利息,该利息并不在履行债务人已向债权人给付的范围内。在比较法上,该种利息与上述费用和损失一样,主要存在于学理和判例,仅有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立法上明确肯定追偿范围包括该种利息。[47]我国法院针对追偿权的司法裁判在是否适用追偿利息的问题上并不统一。[48]因此,被追偿人是否需要支付此类利息尚存在较大的争议。(1)追偿利息的正当性。肯定追偿利息的主要依据在于,超出部分和超出费损实质上被用于清偿其他连带债务人的债务份额,这在理论性质上属于资金的占用,因此占用人必须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对此的质疑主要在于,占用他人资金是否必须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借款双方如果没有约定利息,则借期内视为没有利息。[49]但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该规定只适用于借款合同的期内利息,而追偿利息除了具有与期内利息相同的“资金占用”利息的性质外,还必须以被追偿人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为前提——这是期内利息所不具备的。因此追偿利息属于“逾期利息”的范畴,而逾期利息根据我国现行规定有法定的补充标准,并不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必要。[50]此外,就我国的司法裁判而言,虽然我国法院针对追偿权的多数判决不适用追偿利息,但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些案件中追偿权人的诉讼请求均未涉及追偿利息,而在追偿权人主张追偿利息的案件中,法院均予以了支持。[51](2)追偿利息的计算问题。首先,追偿利息的计息本金。问题在于,该计息本金,除了履行债务人超过自己份额承担的债务本金外,是否还应当包括履行债务人超过自己份额支付的利息(主要指借款的期内利息和共同的迟延履行利息)以及超出费损?其一,就前者而言,超出部分中的利息完全符合上述“资金被占用”的理论属性,如果计息本金不包括此类利息,那么在计算时就必须将此类利息从超出部分中析出并排除。这不仅缺乏理论正当性,而且在借款合同的履行债务人仅仅部分偿还的场合显然会增加计算负担——须在还款中区分债务本金和利息。而就我国法院的裁判实践来看,在支持追偿利息的案件中,法院所采纳的计息本金(除了债务本金外)大多包括期内利息或者迟延罚息。[52]因此,计息本金应当包括上述利息。其二,就超出费损而言,由于追偿权案件中涉及当事人主张追偿汇费、包装费、运输费或者诉讼费用、执行费用的情况极少,所以超出费损的包括与否尚缺乏判例佐证。但排除超出费损显然缺乏正当性依据,目前理论上的一般观点倾向于超出费损也应当加算追偿利息。[53]其次,追偿利息的起息时间。追偿利息的起息时间在比较法上通常体现为履行债务人的“清偿日”或者“免责日”,[54]这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基本一致。[55]但如果债务人之一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提前清偿,则从上述时点起算追偿利息对被追偿人略显不公平:因为按照原债务的履行期限,后者在上述时点尚不构成迟延,提前计息加重了后者的责任。公平起见,起息时间应当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或履行债务人清偿日之中较后者为准(同依不当得利进行追偿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最后,追偿利息的利率标准。对此,比较法上多采法定利率。[56]我国实践中存在两种逾期利率标准可供参照:其一是上述支持追偿利息的判决所采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57]其二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58]即在该基准利率的水平上加收30%~50%。[59]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将民间借贷逾期利率的最终标准调整为“逾期还款违约责任”[60]——从我国的实践来看,该“逾期还款违约责任”仍将按照上述两种逾期利率标准来计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调整,上述两种标准中的“基准利率”当前均应替换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简称LPR)。[61]由于LPR每个月都可能变化,所以对追偿利息的判决应当以上述b之追偿利息起息日的LPR为准;为了保障裁判的统一,有关逾期利率的上述两种实践标准(LPR或者在LPR的水平上加收30%~50%)应当尽快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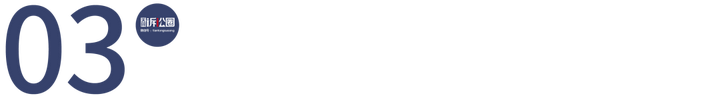
追偿权的限制
(一)债权人利益的限制
该限制是指追偿“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这主要体现为,当履行债务人的追偿权与债权人的债权发生冲突时,债权优先于追偿权。比如A和B对甲连带负债20万元,内部份额相同,A在清偿了15万元之后对B享有5万元的追偿权,但债权人甲对B也享有5万元的剩余债权,如果此时B的资产不足以完全清偿A和甲,则应当优先清偿甲的债权。如果B先向A作出了清偿,则债权人甲可以参照债权人撤销权规则(《民法典》第538条)主张撤销该清偿行为。如果B宣告破产,在破产债权的登记顺位上,A的追偿权应当置于甲的债权以及与甲的债权同顺位的其他普通债权之后。总之,在债权人甲没有得到足额清偿前A不得行使追偿权。该限制规则恰恰反映了连带债务的本质:确保全体债务人的资力优先用于满足债权人的利益。显然,该限制在履行债务人全部履行的情况下是不适用的。
(二)其他债务人利益的限制
来自其他连带债务人(或被追偿人)利益的限制主要表现为排除连带性和抗辩转移。首先,就排除连带性。追偿之债不具有连带性,根据《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的规定,追偿权人只能“在其他连带债务人未履行的份额范围内向其追偿”。该规定取自三部国际示范文本,[62]它意味着,内部份额是每一个被追偿的债务人承担追偿之债的最大范围;如果被追偿人已经全部履行了自己应承担的份额,将免于追偿责任;如果被追偿人已经部分履行了自己的份额,则仅在未履行的份额范围内对追偿权人负责。争议在于,如果A、B、C三个债务人连带承担了90万元的债务,内部份额相等,A履行了60万元,则超出其份额的30万元应当如何向B、C追偿?根据该规则的通行解释,A无须向B、C均分追偿(即向B、C各追偿15万元),而可以在30万元以内向B追偿,同时在30万元以内向C追偿,直至受偿30万元为止。[63]对此的疑虑在于,这是否使得B、C对A的追偿承担了连带责任?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债权优先性的限制,B、C只有先清偿剩余债权(30万元)才能履行追偿之债,这样,二者一定是在各自未履行的份额范围内对追偿承担责任——责任形式是按份责任或者单独责任。追偿之债排除连带性符合作为追偿权基础的不当得利规则:因为从终局意义上讲,其他连带债务人的不当“得利”仅限于自己的份额。更为重要的是,排除连带性乃基于对连带债务人平等对待的考虑——通过排除连带规则,每个债务人只须对自己的份额负责,这就确保了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排除连带性的例外存在于不真正连带债务领域。由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特点在于“多数债务人中存在某个债务人须承担终局责任,其他债务人承担的责任最终都可以向他追偿”;而且只有其他债务人可以向终局责任人追偿,反之不可。在此场合,如果终局责任人为两人以上,其他债务人在向这些终局责任人进行追偿时,后者须承担连带责任。该例外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终局责任人与其他债务人之间并非平等关系,而是处于“不同的义务层次或等级”。[64]该例外的典型例证是连带保证人对数名主债务人的追偿。其次,就抗辩转移。与债权向履行债务人的法定转移(即代位权)相伴,原本针对债权的抗辩也随之转移: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行使代位权的履行债务人主张。[65]抗辩转移规则为债权意定转移(即债权让与)的固有内容(《民法典》第548条),[66]进而被扩张适用于债权法定转移(即代位权)领域。[67]但传统民法基于双重请求权(基础)的结构,对该抗辩转移规则是否完全适用于独立的追偿权始终未有定论。为此,比较法上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但多停留在法教义学层面,像我国这样在立法上完全采用“抗辩转移模式”的做法(《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后段)并不普遍。[68]与此对立的则是理论上所谓的“抗辩切断”模式:针对债权人的抗辩不得对抗履行债务人的追偿权。但完全的“抗辩切断”模式在比较法上基本不存在,[69]目前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更为普遍的是介于抗辩转移模式和抗辩切断模式之间的形形色色的“折中模式”:有以抗辩转移为原则,只对个别抗辩事由适用抗辩切断的,比如荷兰;[70]有以抗辩切断为原则,只对个别抗辩事由适用抗辩转移的,比如英国;[71]也有区分共同抗辩事由与个人抗辩事由,分别适用抗辩转移和抗辩切断的,比如瑞士;[72]也有以追偿关系当事人之间的相互通知为前提来区分适用抗辩转移与抗辩切断的,比如日本和意大利;[73]在英美法系,针对个别债务人的判决是否可以对抗其他债务人的追偿还需区分判决事项的实体性质与程序性质。[74]这里将从以上各种模式的主要争点出发,结合我国的现行体制与上文构建之追偿权的理论基础,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民法典》所采模式的合理性。第一,判决和诉讼时效的抗辩效力是各种模式的争议焦点。其一,法院在债权人针对连带债务人之一的诉讼中所作出的生效判决可否被用以对抗履行债务人的追偿?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判决在解释上当然限于“与全体连带债务人有关的判决(或判决内容)”,否则讨论是无意义的。[75]该问题在实质上已经超出了实体法上的抗辩范畴,而进入程序法上关于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范畴。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在追偿诉讼中理当得到维护,因此无论法院是基于实体事由还是基于程序事由所作出的“与全体连带债务人有关”的生效判决(比如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76]当然可以被用以对抗追偿权(即抗辩转移),否则必将导致不同法院的“一事异判”,此种既判力冲突无论是显性的还是潜在的,都将削弱法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77]作为弥补,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如果履行债务人欲否定此类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只能以不可归责的案外人身份向既判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民诉法》第56条第3款),追偿诉讼的审理法院如果认为先在判决存在实体或者程序上的错误也只能向履行债务人作出上述释明,而不能违反既判力原则,径行作出切断抗辩的判决。[78]其二,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人之一的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可否被用以对抗履行债务人的追偿?这需要区分情况予以讨论。为讨论方便,设前一债务人为A,履行债务人为B。第一种情况,B履行债务之时(即追偿权发生之时),债权对A已罹于诉讼时效,此之谓“事前罹于时效”。这可以从追偿权的理论基础展开分析。从不当得利的基础出发,A以此为由不履行债权是其合法的权利而非“没有法律根据”的获利,因而排除不当得利,A可以据此对抗B的追偿。根据上文论证,代位权的行使须以不当得利的成立为前提,既然排除了不当得利,B的代位权也就相应失去了行使的正当性前提。退一步讲,即使B以代位权为基础进行追偿,此时B乃代行债权人的权利,依上文之债权转移的一般规则,A针对债权人的时效抗辩当然也可以对抗B。总之,无论追偿权基于何种基础,A均可对抗B的追偿(即抗辩转移)。作为对履行债务人B的救济,其因抗辩转移而遭受的不利,只能向债权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者损害赔偿。第二种情况,B履行债务之时(即追偿权发生之时),债权对A尚未超过诉讼时效,但在B向A追偿之时,债权对A则超过了诉讼时效,此之谓“事后罹于时效”。此种情况须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亚情况”。第一种“亚情况”,B并非全部履行,根据上文,该部分履行将导致债权的诉讼时效相对于A和B均发生中断。[79]据此,债权人对A的诉讼时效得以重新计算,在B向A追偿之时该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通常尚未届满,A并无时效抗辩权,也就无从“转移”对抗B的追偿。[80]第二种“亚情况”,B为全部履行,则债权相对于A、B均告消灭,诉讼时效也不再计算,由于在债权消灭前,A对债权人并无任何时效抗辩的理由,同样无从“转移”对抗此后B的追偿;从代位权的基础出发也同样如此:由于B的全部履行导致债权的法定转移,类推债权转让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则,[81]法定转移之债权(即代位权)的诉讼时效从转移生效之日(即B全部履行之日)起中断,中断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A亦无时效抗辩权。但这两种亚情况均非抗辩切断(因为无论是抗辩切断还是抗辩转移都须以抗辩权的有效成立为前提),与我国采用的抗辩转移规则并无矛盾。其三,对判决和诉讼时效采用抗辩切断模式的法域,往往将该切断模式与在这两项事由上采取的“相对效力”体制[82]相联系。德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德国民法典》第425条将包括判决和诉讼时效在内的众多事由归入相对效力范畴。据此,德国理论和实践中通常认为,针对连带债务人之一的生效判决或者罹于时效对其他债务人的外部关系(与债权人的关系)和内部关系(追偿权)均不产生影响——这正是抗辩切断的根源。[83]但是,对于可对抗债权人的抗辩事由采用相对效力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不宜在我国推广。理由如下。首先,相对效力体制与上文所述之我国的既判力体制和追偿权的理论基础是相互矛盾的。其次,判决和诉讼时效的相对效力与免除的限制绝对效力理论之间存在着难以自洽的逻辑矛盾。根据德国民法的主流理论,债权人与连带债务人之一达成的免除协议对于不知情的其他债务人具有限制绝对效力:外部导致其相应免责,内部则导致其追偿权丧失或受阻。[84]既然协议可以突破相对性而产生外部效力(恶意损害其他债务人的除外),那么,在债权人针对连带债务人之一的请求被判决驳回或者罹于时效的场合,债务人乃取得法定的抗辩理由,从举轻以明重的角度出发,此类法定的抗辩理由也应产生外部效力——阻却其他债务人的追偿;再次,严格的坚持相对效力并不符合连带债务的整体性特征(其实质是连带当事人之间的牵连关系),容易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实践效率较低。综上所述,在判决和诉讼时效的问题上,我国所采用的抗辩转移模式是妥当的。第二,区分共同抗辩(common defences)和个人抗辩(personal defences)[85]或者设置追偿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通知义务,其要旨均在于将抗辩效力限制在知悉抗辩事由的当事人之间,进而否定抗辩事由的“外部效力”(即对不知情的外部第三人的拘束力)。此种观点乃基于民法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一般倾向,但这并非一条绝对的原则,只要有合适的理由是可以被突破的——连带债务内部追偿权的理论基础恰恰为此提供了突破口。由于该追偿权以不当得利和代位权为基础,而当连带债务人之一基于有效的抗辩事由(无论是共同的还是个人的)可以合法对抗债权人时,追偿权的这两个基础即相应的被排除了:以债权人针对连带债务人之一的免除为例,后者以该免除对抗履行债务人的追偿乃基于不当得利的排除,即使追偿系基于履行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代位,依债权转移的一般规则,该免除亦可对抗代位求偿。其中理由同上述“事前罹于时效”的抗辩,这里不作赘述。总之,抗辩转移,即所谓抗辩事由的“外部效力”,其正当性基础乃在于该抗辩事由在实质上导致了追偿权基础的消灭或受阻,而与当事人是否知悉抗辩事由(以及主观过错)不存在必然联系。因此,区分共同抗辩事由与个人抗辩事由或者为抗辩转移设置通知前提的做法均非必要。第三,采用抗辩转移模式的立法例通常强调可转移的抗辩事由的“事前性”,即只有在追偿权(或被追偿人的分担义务)或者代位权发生之时已有的可以对抗债权人的事由——“事前的抗辩”——才可以对抗追偿权人;反之,在追偿权或者代位权发生后产生的可以对抗债权人的事由——“事后的抗辩”——则不得对抗追偿权人。[86]在操作中,此种追偿权或代位权的发生时间就是追偿权人履行债务的时间,即债务清偿时。仔细研判后不难发现,所谓“事后的抗辩”包括两种情况:其一,在法律上本就不具有抗辩效力,比如“事后罹于时效”因为发生时效中断或者债权消灭的原因,该抗辩并不成立;其二,在法律上仅具有相对效力,比如在债务清偿之后,债权已经消灭,此时债权人再对其他连带债务人实施免除的行为——“事后的免除”——实属无权免除,参照《民法典》第765条之规定只在免除当事人之间生效,对追偿权人“不发生效力”。[87]显然,对于第二种情况有必要强调可转移之抗辩事由的“事前性”。因此,《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后段中“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在法解释上应当限制于“事前的抗辩”。第四,《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的抗辩转移效力是否适用于抵销权,在比较法上争议较大。目前比较法上的一般观点倾向于否定,即针对债权人的抵销权不得对抗追偿权人。[88]但是,否定的理由缺乏说服力,其中最为重要的理由是,在抵销权行使前,追偿权人的履行已经使得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免责,这就导致其他连带债务人针对债权人的抵销权相应消灭,或者说其他连带债务人应当预见到上述结果并对此负责。[89]该理由在我国难以成立。其一,这一理由成立的前提是抵销权是否有效以其行使时的条件为准,但我国实践中则采用了“抵销的溯及力”理论:抵销权是否有效并非以其行使时的条件为准,而是以抵销适状时——双方债权符合抵销的要件时——的条件为准。[90]据此,只要在追偿权人履行之前抵销的条件已经具备,该抵销权即为有效。其二,这一理由等于要求其他债务人在追偿权人履行前尽早主张抵销,但前者并未受到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强迫其主动行使抵销权有失公允。其三,我国《民法典》第549条采纳了债权意定转移(即债权让与)场合的抵销转移规则,从类推的角度上看,因连带债务人之一的履行所导致的债权法定转移也应准用这一规则。[91]因此,第519条第2款的抗辩转移效力应当适用于抵销权。
注释:
[1]这些学说的介绍参见戴修瓒:《民法债编总论》,上海法学编辑社1948年版,第350—351页;胡长清:《中国民法债篇总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61—462页,第466页;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4页;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页;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32—733页;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页;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154页;王利明:《债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236页。
[2]关于“双重请求权(基础)”在大陆法系主要法域的立法依据,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26条第1款(追偿权)和第2款(法定代位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81条第1款(追偿权)和第2款(法定代位权),《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前)第1213—1214条(追偿权,2016年修订后第1317条)和第1251—1252条(法定代位权,2016年修订后第1346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298—1299条(追偿权)和第1203—1204条(法定代位权),《日本民法典》第442条(追偿权)和第499—504条(法定代位权)。
[3]出自拉伦茨的观点,参见张定军:《连带债务研究——以德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另参见注[1],胡长清书,第467页。
[4]See R. E. Cerchia, Uno per Tutti, Tutti per Uno: Itinerari della Responsabilità Solidale nel Diritto Comparato, Milano: Giuffrè, 2009, pp.178-179.
[5]See W. V. H Rogers, “Comparative Report on Multiple Tortfeasors”, in W. V. H Rogers (ed.), Uification of Tort Law: Multiple Tortfeasors,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p.292.
[6]参见注[1],王利明书,第235页。
[7]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玉波、孙森焱和黄立明确支持这一方案,参见注[1],郑玉波书,第405页;注[1],孙森焱书,第740-714页;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3页。在意大利,这一方案也得到了部分学者(比如Carpino)的支持,参见C. 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IV. L’obbligazione, Milano: Giuffrè, 1993, p.363.
[8]需说明的是,《欧洲侵权法原则》(PETL, 2005)第9:102条将本条之追偿权与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法定代位以及不当得利并列为连带债务人之间分担请求权的基础。在解释上,约定和法定居于优先地位,而追偿、法定代位与不当得利之间则处于平等选择的地位。参见欧洲侵权法小组:《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于敏、谢鸿飞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9]参见汪渊智:“《我国民法分则(草案)》合同编总则部分的修改建议”,《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9年第1期,第73页以下。
[10]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26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81条。意大利和日本在立法上并无此类规定,但其主流的法教义学理论采用的也是“结合适用”方案。参见注[7], Bianca书,pp.722—724;[日]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IV·新订债权总论》,王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92页。
[11]参见注[7], Bianca书,p.724;[德]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3页。
[12]参见《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0:106条第1款和第2款,《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107条第1款和第2款,《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1.1.10条和第11.1.11条第1款。此外,本文援引的以上三部国际示范文本及其评注的中译本分别为:欧洲合同法委员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三部分”,朱岩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0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1页以下;[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三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张玉卿主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13]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债权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第717条,该条起草者为渠涛教授);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债法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第1215条,该条起草者为尹飞教授)。另外,结合适用方案也为谢鸿飞教授所支持(谢教授称之为“一体适用”),参见谢鸿飞:“连带债务人追偿权与法定代位权的适用关系——以民法典第519条为分析对象”,《东方法学》2020年第24期,第139页以下。
[14]参见[意]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297页;[德]卡泽尔、克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84—585页;F. C. Savigny, Le Obbligazioni, Volume 1, trad. G. Pacchioni, Torino: UTET, 1912, pp.250-251.
[15]对于连带之债,中世纪注释法学理论尤其关心追偿权问题,具体参见Gerhard Wesenberg, Gunter Wesener, Storia del Diritto Privato in Europa, tradotta in l’italiano da Paolo Cappellini e Maria C. Dalbosco, Padova: CEDAM, 1999, p.68.
[16]朴蒂埃指出,连带债务人之一在清偿债务时必须主张代位权,方可依据法定让与而代位行使债权人的权利(无须债权人同意);连带债务人之一在清偿时如果没有主张代位权,则不再享有代位求偿权,但他仍然享有向其他共同债务人提起返还各自份额的自有诉权,该自有诉权的根据是债务得以建立的不同诉因,包括合伙之诉、委托之诉或者扩用无因管理之诉。参见M. Pothier, Treatise o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or Contracts, Volume I, translated by William David Evans, Philadelphia: Robert H. Small, 1826, p.141-147, §5§6, [280]-[282].萨维尼则分门别类地探讨了连带债务追偿权的法律基础,包括近代学者提出的不当得利基础以及罗马法上的具体诉权基础(合伙之诉、委托之诉、无因管理之诉、债权转移)。参见注[14], Savigny书,p.211.
[17]不当得利说在近代欧陆民法理论上影响很大,参见注[14], Savigny书,pp.214—215.当代意大利较为权威的学说仍将其作为连带债务内部追偿权的理论基础,参见Rubino, Obbligazioni alternative. Obbligazioni in solido. Obbligazioni divisibili e indivisibili, in Comm. Scialoja e Branca (Art.1285-1320), Bologna: Zanichelli, 1968, p.232.
[18]“主观共同关系”的说法出自日本,参见注[10],我妻荣书,第381—382页。德国传统解释理论上也称之为“共同利益关系”,参见注[1],史尚宽书,第664页。
[19]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26条第1款,《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前第1213—1214条和修订后第1317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298—1299条,《日本民法典》第442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80条和第281条第1项,我国《民法典》第519条。
[20]萨维尼将“不当得利说”的基础归于自然公平,参见注[14], Savigny书,pp.214—215.日本传统理论对“主观共同关系说”和“当然存在说”的阐述往往从公平原理出发,参见注[10],我妻荣书,第382页;胡长清先生也将追偿权当然存在的理论依据归于公平观念,参见注[1],胡长清书,第461、466页;20世纪以来荷兰最高法院也始终坚持在公平原则中寻找追偿权的基础,参见Willem H.van Boom, “Multiple Tortfeasors under Dutch Law”,载注[5], Rogers主编书,p.137.
[21]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1.1.11条第1款。
[22]诉讼时效上的差异参见注[1],郑玉波书,第405页;注[1],孙森焱书,第741页;注[13],谢鸿飞文,第137—138页。
[23]正因为如此,梅迪库斯指出,代位求偿的情形下,在债权让与之前已经经过的那部分消灭时效期间不损害代位求偿权人的利益。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14页。
[24]德国的法教义学明确采纳这一通行模式。参见注[23],第613页;注[11],罗歇尔德斯书,第422页。另参见《瑞士债务法》第148条第2款,《荷兰民法典》第6∶10条第2款以及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责任分担》(简称REST 3d TORTS-AL)第23条(b)。
[25]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1.1.10条,《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0∶106条第1款,《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107条第1款。
[26]参见《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后)第1317条第2款。意大利判例和学说的转变参见注[7], Bianca书,p.721.
[27]中译文参见《日本民法条文与判例》,王融擎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页。
[28]对于追偿权的行使是否必须以超过自己的分担部分为条件,我国台湾学者以肯定说为通说,但孙森焱、丘聪智、曾隆兴则基于公平之考虑而支持否定说。参见注[1],孙森焱书,第736页;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曾隆兴:《详解损害赔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4页。
[29]参见注[1],郑玉波书,第403页;注[1],王利明书,第237页;注[13],谢鸿飞文,第132页。
[30]参见注[13],谢鸿飞文,第132页。
[3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16条。
[32]参见法释〔2008〕11号第17条第2款。
[33]参见《瑞士债务法》第148条第2款、美国的REST 3d TORTS-AL §23(b)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1.1.10条。
[34]参见《荷兰民法典》第6∶10条第3款、《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0∶106条第1款以及《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107条第1款。
[35]参见《日本民法典》第442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80条和第281条第1款。
[36]法国、德国的法教义学上对于超出部分以外的追偿项目也不明确。参见注[4], pp.175—186;注[32],第612页;注[11],罗歇尔德斯书,第422页以下。但意大利的主流理论认为,追偿范围应当包括债务人超出自己的份额已经支付的本金、费用、利息。参见注[7], Bianca书,p.717.
[37]参见注[1],孙森焱书,第738页。
[38]参见注[1],孙森焱书,第737—738页;[日]於保不二雄:《日本民法债权总论》,庄胜荣校订,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29页。在意大利的主流理论上,“费用”则涵盖了上述履行费用和诉讼费用。参见注[7], Bianca书,p.717.
[39]在立法上有规定者参见注[34]和注[35]。
[40]参见注[1],郑玉波书,第403页;注[1],孙森焱书,第737页;注[7],黄立书,第590页。
[41]参见注[10],我妻荣书,第385页;注[38],於保不二雄书,第229页;注[1],郑玉波书,第403页。
[42]参见注[1],孙森焱书,第735、737—738页;注[7],黄立书,第591页。对于诉讼费用、执行费用,孙森焱进一步主张连带债务人之一因可归责于自己之事由与债权人涉诉而负担之诉讼费用或执行费用不应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
[43]参见注[1],史尚宽书,第669—670页。
[44]比如甲、乙两个单位连带承担煤炭供货义务,但由于乙的业务员工作失误,向甲提供了错误的供货地址和路线,导致甲的运输费用额外增加。此案中,甲正常的运输费用可依不当得利向乙主张分担,而额外增加的运输费用则可依侵权或者违约向乙主张赔偿。比较法上的讨论参见注[5], Rogers文,p.292.
[45]参见“英贸公司诉天元公司保证合同追偿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庆中民终字第384号民事判决书。
[46]参见注[1],孙森焱书,第738页;注[7],黄立书,第591页。
[47]参见《日本民法典》第442条第2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81条。此外,《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后)第1346—4条第2款则在代位权中承认了该种利息。
[48]多数判决不适用追偿利息,比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2)兵八民一终字第294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枣民二商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庆中民终字第384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902号民事判决书;“顾善芳诉张小君、林兴钢、钟武军追偿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10期;“英贸公司诉天元公司保证合同追偿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但有的判决则支持此类追偿利息,比如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2000)老经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368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366号民事判决书。
[4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25条第1款和《民法典》第680条第2款。
[50]比如,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时,民间借贷合同的逾期利息依法释〔2020〕6号第29条第2款确定,买卖合同中买受人逾期付款的法定罚息标准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24条第4款确定。
[51]参见注[48]。
[52]参见注[48]。
[53]参见注[1],史尚宽书,第669页;注[1],郑玉波书,第403页;注[38],於保不二雄书,第229页。
[54]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81条第1款规定为自“免责时”起算,《日本民法典》第442条第2款则规定自“清偿及免责日”起算,意大利主流教义则主张自“清偿时”起算,参见注[7], Bianca书,p.717.
[55]在支持追偿利息的案件中,我国法院通常判决被追偿人支付自追偿权人清偿之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损失。参见注[48]。
[56]参见《日本民法典》第442条第2款、《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第1346—4条第2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81条虽未明确采法定利息(率),但学理解释上认为此追偿利息应依法定利率计算。参见注[1],郑玉波书,第403页;注[1],孙森焱书,第737页。意大利的主流理论也认为该追偿利息适用法定利息。参见注[7], Bianca书,p.717.
[57]参见注[48]中支持追偿利息的案例。
[58]参见法释〔2012〕8号第24条第4款。
[59]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
[60]参见法释〔2020〕6号第29条第2款之(一)。
[61]参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及法释〔2020〕6号第26条。
[62]参见《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0∶106条第1款;《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107条第1款;《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1.1.10条。
[63]See Nils Jansen, Reinhard Zimmermann (eds.), Commentaries on European Contract Laws, New York: Oxford, 2018, p.2671.
[64]关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特点,参见李中原:“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的反思与更新”,《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40、45页。
[65]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抗辩应当作广义解释,除了民法上狭义的抗辩权(如诉讼时效的抗辩、同时履行抗辩以及不安抗辩)外,还包括债务人对抗债权人的其他合法手段(比如债的无效、免除等)。
[66]比较法上可参见《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后)第1324条第2款、《德国民法典》第404条、《日本民法典》第468条第1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99条第1款、《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9.1.13条第1款、《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1∶307条第1款以及《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5∶116条第1款。
[67]比较法上可参见《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后)第1346—5条第3款、《德国民法典》第412条。
[68]立法上完全采用抗辩转移模式的另一例证是《葡萄牙民法典》第525条第1款。
[69]仅有奥地利的体制与此较为接近:其在免除、和解、判决等事项上均采用“抗辩切断”模式。参见《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896条;Bernhard A. Koch, Peter Schwarzenegger, “Multiple Tortfeasors under Austrian Law”,注[5], pp.13,19,27.
[70]《荷兰民法典》第6∶11条第1款确立了抗辩转移的原则,但该条第2款到第4款对该原则设置了诸多限制(涉及免除和诉讼时效)。德国理论在总体上也倾向于这一模式,但针对连带债务人之一的诉讼时效和判决,则基于相对效力而不得对抗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追偿。具体阐述可参见Ulrich Magnus, “Multiple Tortfeasors under German Law”,注[5], p.99,102.此外,《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0∶111条第2款、第10∶109条、第10∶110条)和《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112条第2款、第3—4∶110条、第3—4∶111条)仅对个人抗辩原则上采用抗辩转移模式,《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1.1.12条、第11.1.7条、第11.1.8条)对个人抗辩和共同抗辩原则上都采用抗辩转移模式,但在涉及诉讼时效和判决时三者都设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71]参见Civil Liability (Contribution) Act 1978(英国1978年民事责任〔分担〕法案), sec.1(3), sec.1(5)以及W. V. H Rogers, “Multiple Tortfeasors under English Law”,注[5], p.75.只有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实体性事项(比如责任要件不具备)以及极个别的时效期间具有抗辩转移效力。
[72]参见《瑞士债务法》第145条第2款;C. Chappuis, G. Petipierre, B. Winiger, “Multiple Tortfeasors under Swiss Law”,注[5],pp.240,247,259.
[73]参见《日本民法典》第443条和注[7], Bianca书,pp.718—723.该模式的实质是在追偿双方之间设置抗辩事项的通知义务,以违反义务的过错为基础来判断是否适用抗辩转移。在具体方案上日本和意大利又有所不同。此种以过错为标准区分抗辩转移或切断的思路也影响到了我国,参见注[13],谢鸿飞文,第141页。
[74]参见W. V. H Rogers, “Multiple Tortfeasors under English Law”,注[5], p.75,82;M. D. Green, “Multiple Tortfeasors under US Law”,注[5], p.269.
[75]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1.1.8条第2款。
[76]基于程序事由的生效判决的典型例证是因证据不足导致判决驳回起诉。诸如债权人的起诉不符合管辖规则等程序原因所导致的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并不构成对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债权人可以依据管辖规则继续起诉),因而也不得用以对抗追偿权。
[77]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诉讼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所谓既判力或者判决的效力仅限于诉讼当事人之间的相对性理论已经被突破甚至被否认。参见吴明童:“既判力的界限研究”,《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第77页以下;吴泽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56页。该状况与《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所采取的抗辩转移模式是暗合的。
[78]在国内现有的研究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一般适用领域并不包括连带债务。参见张卫平:“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第170页以下;注[77],吴泽勇文,第148页以下。但《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所确立的抗辩转移模式则使得连带债务成为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可能发挥作用的又一新增领域。
[79]参见注[31]、[32]。
[80]需要补充的是,在极端情况下,如果B拖延至该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届满后方行追偿,则A仍可依对债权人的时效抗辩来对抗B的追偿(即抗辩转移),理由同第一种情况。
[81]参见法释〔2008〕11号第19条第1款。
[82]所谓连带债务的“绝对—相对”效力体制是传统民法关于连带之债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的要旨在于考察发生在连带债务人之一的事项所产生的效力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其他连带债务人。如果该事项对其他债务人产生相同效力,即为绝对效力;如果对其他债务人产生有限效力,即为限制绝对效力;如果对其他债务人不产生效力,即为相对效力。
[83]参见《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110条之注释[2]和第3—4∶111条之注释[1];注[12],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主编书,第864、865页;注[70], Ulrich Magnus文,pp.99,102.
[84]参见注[23],第615页;注[70], Ulrich Magnus文,p.95;[德]彼得·温德尔:“多数债务人与债权人”,李佳盈译,《交大法学》2020年第3期,第118页。
[85]就连带债务而言,共同抗辩乃基于所有债务人共同拥有的抗辩事由,比如导致连带债务的合同无效、对所有债务人共同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个人抗辩则是基于专属于个别债务人的抗辩事由,比如债权人与个别债务人达成的免除协议、对个别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86]参见《荷兰民法典》第6∶11条第1款;《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后)第1346—5条第3款。
[87]无权免除与无权转让不同。后者依目前通说是有效的;前者的典型情况是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后的免除,《民法典》第765条规定其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
[88]参见注[63], pp.2699—2700.此外,《欧洲合同法原则》和《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也未将抗辩转移效力扩及抵销。《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1.1.12条(a)则否认个人抵销权(专属于个别债务人的抵销权)可以对抗追偿权人。
[89]参见注[12],张玉卿主编书,第821页(《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1.1.12条的官方评注[2]);注[63], p.2699.
[90]参见“厦门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南悦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4期。另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54页。
[91]这在《法国民法典》(2016年修订后)第1346—5条第3款中可得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