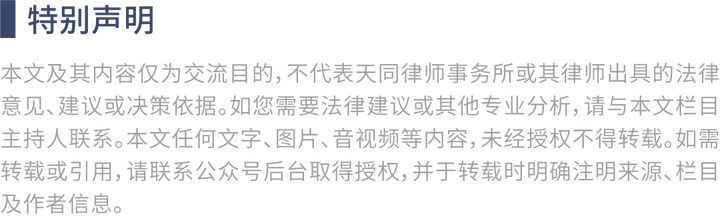本文共计24,372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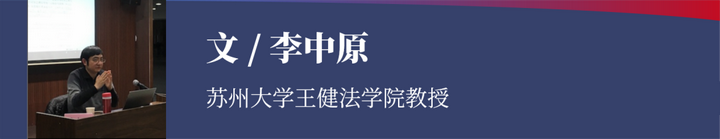
注:本文发表于《法学研究》 2019年第2期,载第42页。
摘要:关于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化,争议主要在于是否需要规定不可分之债或协同之债。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只是确定多数人之债实现方式的一种中间性的辅助手段,而且由于二者的区分在标准上存在歧义且操作复杂,该辅助手段的实用价值有限。围绕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所形成的传统规则大多与按份之债、连带之债以及协同之债密切相关。编纂中的我国民法典关于多数人之债的规定,应当不采传统大陆法系将可分之债、不可分之债与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并列或者混合规定的模式,而采取以债的实现方式为导向的类型化模式,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以外设置协同之债的规定。协同之债的本质特征在于共同实施性。在立法上设置协同之债的必要规则,既是基于多数人之债法律体系上的完备性要求,也是基于审判实践之需。
关键词:多数人之债 可分之债 不可分之债 协同之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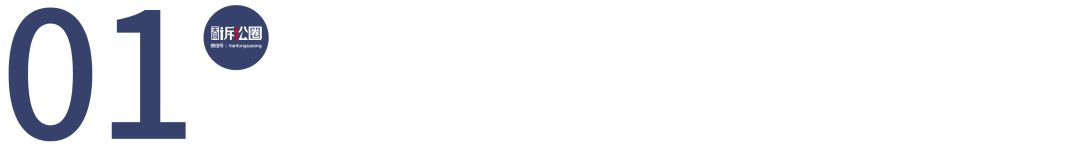
问题的提出
在大陆法系的民法传统上,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化存在两种方案:一是划分为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二是区分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由于可分之债在传统上以按份为原则,所以传统民法典往往在可分之债中规定按份原则,从而将后者涵盖其中,这就形成了传统民法典中通常采用的三分模式:可分之债、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1]我国自民法通则以来,在立法上只设置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并未设可分之债和不可分之债。目前我国立法机关正在审议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基本延续了这一方案。[2]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该草案的准备过程中,学界曾提出过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主张在连带之债与按份之债以外对不可分之债作出专门规定;另一种则主张不规定不可分之债,而对与其相关的另一范畴——协同之债——在连带之债和按份之债之外并行规定。[3]前一种方案接近于上述大陆法系的传统模式,后一种方案则是2000年以后陆续推出的三部国际示范文本《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2003)、《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2009)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2010)的做法,[4]代表了一种新的范式。从我国立法和理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来看,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作为多数人之债的两种基本类型,毋庸置疑。争议主要在于,是否需要规定不可分之债,抑或是规定协同之债。中国大陆的民法理论界对于不可分之债重视不够,现有研究在不可分之债的核心问题上也缺乏共识。[5]基于立法与理论上的欠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不可分之债的规则运用多有讹误。[6]而协同之债在中国大陆的民法理论和实践中更是鲜有提及。[7]因此,要想回答未来中国民法典在上述领域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方案,我们必须对该领域尤其是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理论脉络和实践状况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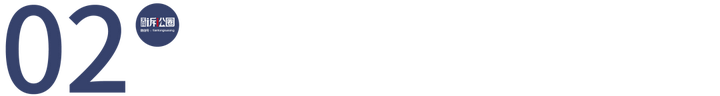
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
现代民法上关于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理论源自罗马法。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一区分理论最初主要产生于遗产继承领域,而且与债的主体的复数化相关。根据《十二表法》第5表第9条的规定:债权和债务在数个共同继承人之间按照继承的份额是“当然”(ipso iure)可分的。[8] “因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应被划分为多个权利和义务,而且每个人的标的都是原始标的的一部分。”[9]由此可见,可分之债(obligatio divisibilis)与按份之债(obligatio pro parte)在此并无区分。同样,根据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直至古典罗马法时代,不可分之债(obligatio indivisibilis)与连带之债(obligatio in solidum)也是一回事,二者混同不分。[10]转变发生在优士丁尼时期。优士丁尼法将不可分之债作为按份之债处理。这突出体现在,当不可分债务因为不履行而转变为损害赔偿义务时,债权人向共同债务人主张金钱价值的权利即从不可分之债转化为可分(按份)之债。[11]据此,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的古典同一性出现了裂缝。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的正式分离出现于晚近的共同法时代。[12]这一时期法国的法学家朴蒂埃(Pothier)对此作出了突出贡献。朴蒂埃在总结16世纪法国习惯法学者杜穆林(Dumoulin)的学说[13]的基础上,将连带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彻底分离:连带之债被归于“债的缔结条件和方式”的范畴,不可分之债(以及可分之债)则归于“债的标的”的范畴。[14]19世纪的德国共同法学者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思想:将连带之债归于“债的主体”范畴,而将不可分之债(以及可分之债)归于“债的标的”(即给付)范畴。[15]在此基础上,朴蒂埃及其后的德国学者对可分之债和不可分之债所作出的阐述基本确定了近现代民法在此领域的理论和立法范式。这一传统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与实现方式。本部分先讨论两者的区分标准。
(一)共同法
根据朴蒂埃的基本思路,[16]债的分割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事实分割,即对债的标的的物理分割,另一种则是观念分割(或法律分割,in iure et intellectu),即按照债的标的的权利份额进行分割。可分之债系指债的标的在事实上可分或者在观念上可分:前者如金钱之债,后者如给付一个奴隶或一匹马。不可分之债系指债的标的在事实上和观念上均不可分。在此,朴蒂埃沿袭杜穆林的理论,将不可分性分为三类。前两类属于不可分之债的范畴,即“缔约不可分”(individuum contractu,或“性质不可分”,individuum natura)和“债不可分”(individuum obligatione)。前者为绝对不可分,比如一项通行地役权的负担,其特点是,债的标的就“性质”(natura,包括事实和观念两个方面)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分,因此不可能通过分部分“缔约”(contractu)得以实现。后者如一项建筑房屋的债务,其特点则是,建房这样的工作可以通过分别缔约来完成房屋的各个部分,但当其作为债的标的时,从缔约当事人的看法来考虑是不可分的。[17]第三类不可分性是“清偿不可分”(individuum solutione)。该类型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可分之债的范畴,只是在清偿或履行上不可分割,必须全体当事人共同履行或共同接受履行,否则将导致不公平,因而该类型被视为介于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之间的中间形态。清偿不可分包括三种具体情况:单一种类物(替代物或不特定物)之债,约定共同履行之债务,以及根据债或标的物的性质或者合同的目的(也就是合同当事人真正的意图)不得分部履行之债。[18]就这三类不可分性之间的关系而言,第一类不可分性必然导致第二类和第三类不可分性,第二类不可分性也必然导致第三类不可分性,反之则不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于第一类的绝对不可分,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不可分性都与所谓“当事人的真正意图”——即债的目的——密切相关,二者的区别并不明晰,此乃朴蒂埃理论的缺陷。综上,朴蒂埃区分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标准主要是债之标的的事实性质和权属性质,债的目的的考虑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据此,可以将朴蒂埃的相关分类体系归纳如下:(图略)萨维尼沿袭了朴蒂埃关于事实分割和观念分割的标准。[19]但萨维尼指出,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主要针对多数人之债,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为一人的单一之债领域,该区分的实践意义不大。[20]在此基础上,温德夏特进一步明确指出,给付在性质上虽然可分但分割违背当事人的意志或法律的规定,亦为不可分之债[21]——类似于上述第二类不可分性(“债不可分”);但温德夏特所谓的“给付性质”并非给付标的物的“物理或自然”属性,而主要是指给付在“观念上”的属性。[22]综上所述,近代早期法国和德国的共同法学者对于给付乃至债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区分标准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考量因素:给付的事实性质(或物理性质或自然性质)、给付的观念性质(或权属性质或权利份额)、债的目的(包括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
(二)现代法
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遵循了朴蒂埃的上述思路,不可分性的三种类型分别被其第1217条、第1218条和第1221条所采纳。据此,不可分之债包括两种情况:一为债的标的(或者给付)在性质(包含事实和观念两方面)上不可分(第1217条),即“缔约不可分”。二为债的标的(或者给付)在性质上可分但从“债的关系考虑”不能部分履行(第1218条),此乃对“债不可分”理论的继受。这里所谓债的“关系”(rapport)实系债的目的,涵盖了债在不同情况下的功效、用途以及缔约人的意图。[23]朴蒂埃理论中的“清偿不可分”则被作为可分之债在效果(即实现方式)上的五种例外情况之一加以规定:根据债或标的物的性质或者合同的目的可知合同当事人的本意是该债务不得分为若干部分履行(第1221条第1款第5项)。[24]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将债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区分标准归结为给付性质和债的目的两个方面的考量因素,前者包括给付的事实性质和观念性质。在朴蒂埃理论中尚不够明确的债的“关系”或“目的”被明确作为区分债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因素。但朴蒂埃理论的缺陷也被延续下来:第1218条(不可分之债)与第1221条第1款第5项(可分之债实现方式的例外)同样基于债的目的,二者之间的区分缺乏说服力。2016年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删除了上述规则,且新设的第1309条和第1320条不再对区分标准作出规定。由此,该问题完全被归入法教义学的解释范畴。而当代法国的主流学说在该问题上基本沿袭了上述传统理论,将不可分之债概括为两种情况:债的标的(或者给付)在性质上不可分,或者在性质上可分但依法定或约定不可分。[25]但是,修订后的“不可分之债”(第1320条)被明确规定在了“多数人之债”的类型中,根据当代法国主流学说的解释,所谓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不仅在于债的标的(或者给付)可否分割,而且在于债的标的(或者给付)可否“在复数债权人或者复数债务人之间进行分割”[26]——这显然背弃了可分性同样适用于单一之债的传统(修订前的第1220条第1款),转向了德国民法典的范式。意大利民法典第1316条在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上沿袭了法国的传统思路,将不可分之债归为两种情况,即“作为给付标的的物或行为依其性质或者依缔约当事人的看法不适宜分割的,债即为不可分”。[27]这一表述显然更接近于朴蒂埃。意大利当代学理将给付不可分性的标准概括为实质不可分、经济功能不可分、法律不可分、协议不可分。前两者是指分割面临过大的困难或经济成本过高,属于给付的事实性质范畴;后两者则是指给付依法定或者约定不可分,属于债的关系或目的范畴。意大利主流理论强调给付的分割必须落实到标的物的某一部分,因而抵制观念分割——反对以权利的可分性作为给付可分性的一般标准。尽管如此,观念分割仍然在买卖共有之不可分物的规则中得到了认可。[28]德国民法典始终将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限制于“多数人之债”范畴。德国民法理论在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区分标准上除了坚持传统的考量因素外,还引入了“人”的因素:仅仅“给付”可分还不足以导致债之可分,只有当给付可以按照债务人或者债权人的人数分割为不同部分,并由各个债务人分别履行或者向各个债权人分别履行时,该债方为可分,否则为不可分。这一观念突出地体现在不可分之债与共有关系之间的关联性上——德国将共有人的共有债权和共同共有人给付共有财产的共有债务视为不可分之债的重要内容。[29]由于此类不可分之债的关键在于给付在观念(即权利份额)上不可分,而不论在事实上是否可分,这就进一步证成了温德夏特的上述观点:作为区分债之可分性与不可分性之标准的“给付性质”的关键是给付的观念性质,而非给付的事实性质。在上述一般标准之外,拉丁法系的某些法域在立法上还针对债的各种具体形态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问题进行列举式规定。这些规定内容庞杂,缺乏统一性,[30]某些规定在学理上还存在较大争议。[31]
(三)小结
就大陆法系的传统而言,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可以从形式标准和实质因素两个方面予以分析。传统民法以“给付的分割”即“债可否部分履行”作为区分二者的形式标准:只要可以部分履行(或部分给付),准确地说,只要部分履行可以相应地导致债的部分消灭,即为可分,否则为不可分。[32]但现代德国和法国的民法理论上增加了“人的分割”的要求:债仅可以部分履行还不足以导致其可分,只有当分割的“部分”可以由各个债务人分别履行或者向各个债权人分别履行时,该债方为可分,否则为不可分。传统做法可以简称为“分部标准”,相形之下,德国和法国的现代做法可称为“分人+分部标准”。二者导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协同之债的归属。协同之债(详见下文)要求各个债务人必须共同履行,各个债权人必须共同受领履行。依现代标准,协同之债因排除“人的分割”而归属于不可分范畴,可分之债则排除协同形式;但依据传统标准,虽然协同之债不得进行“人的分割”,但仍可以进行“给付的分割”——各个协同债务人或者各个协同债权人可以共同履行部分给付或者共同受领部分给付,因此可分之债也可以采用协同形式。[33]其二,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适用范围。相形之下,现代做法缩小了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适用范围,将该区分限制在多数人之债的范畴内。这虽非传统民法的做法,但由于在单一之债领域,传统民法通常也将可分性视同不可分性,[34]所以,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区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主要适用于多数人之债领域[35]——本文的探讨也主要集中于该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在单一之债领域,给付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区分并非毫无意义:在给付可分的场合,如果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部分履行(甚至部分撤销)是允许的;[36]而在给付不可分的场合,则不允许部分履行(或部分撤销)。基于此,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概念也经常被运用于单一之债领域。[37]总之,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式标准,而且各有其意义。无论采用上述哪种形式标准,考量给付在法律上可分与否的实质因素在比较法上包括两个方面,即给付性质和债的关系。[38]给付性质涵盖了给付的事实性质(或物理性质或自然性质)和给付的观念性质(或权属性质或权利份额)两个因素。二者之中孰为决定给付性质的关键,比较法上的观点并不统一。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债的目的,对此须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法律的规定以及习惯加以判断。就给付性质和债的目的在具体考量中的相互关系而言,理论上一般认为,给付在性质上不可分,则在法律上不得依法定、约定或习惯进行分割,[39]而给付在性质上可分,尚须结合债的目的来确定其在法律上是否可分。此外,如果给付在性质上不够明确,比如完成一项建筑工程,则其在法律上是否可分也需要结合债的目的予以判断。总体来看,比较法上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并不统一,辅助考量的实质因素也较为复杂、抽象,操作难度较大。具体列举式规定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陷,但缺乏国际普遍性,内容不统一甚至存在争议。因此,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规则不适于在立法上统一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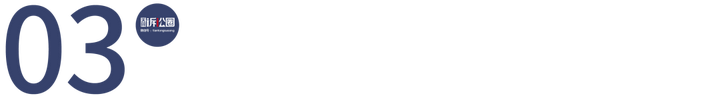
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实现方式
(一)共同法
在朴蒂埃的理论中,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可分之债原则上采用分割实现的方式(即按份之债),但也存在很多例外的情况须采用连带方式。[40]不可分之债基本上采用连带方式。就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共性在于二者都具有整体性:每个债务人都须对整体负责或者每个债权人都对整体享有权利。[41]差异在于整体性的产生基础不同:不可分之债的整体性乃基于债的标的的性质,连带之债的整体性则基于债的主体的性质。因此,连带之债并非以不可分性为必要——连带性并不妨碍债的标的在连带债务人或者连带债权人之间可能进行分割。[42]反之,不可分之债也可能采用连带以外的实现方式:不可分债务如果在产生时不是连带的,比如数个继承人从死者处继承而来的不可分债务,则任一继承人(或债务人)在被起诉后都可以主张暂停诉讼程序以传唤其他共同继承人一起进入程序——类似现代法上的“协同性”理念。[4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协同性”理念在性质上属于可分之债范畴的清偿不可分领域也有类似体现:债权人既不能诉请债务人的继承人之一承担全部债务,清偿的不可分性也不允许继承人之一进行部分给付,除非其他共同继承人同时给付剩余部分。[44]据此,可以将朴蒂埃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实现方式归纳如下:(图略)有所不同的是,萨维尼虽将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归于共同之债(correalit?t),即连带之债,[45]但针对不可分债权,所谓的共同之债或者连带之债的实现方式则被简化为:多数债权人之间应当达成共识,就如同任命了一个共同代理人,从而只要一次审判就可实现他们的权利[46]——这也隐含了现代民法上的“协同性”理念。在此基础上,温德夏特更加明确地指出,连带性在不可分债权的场合并非严格适用:如果向共同债权人之一给付无法带来其他债权人的满足,债务人只有在被担保无须对其他债权人的份额负责的情况下,才应当向共同债权人之一给付;连带性对不可分债务则基本适用:每个债务人即使没有得到类似的担保,也必须对债权人负担全部债务;但不可分债务领域也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任一债务人并不对整体债务负责,而仅仅承担特定的协作义务。[47]可见,在德国的共同法学说中,不可分债权和不可分债务领域都存在现代民法意义上的“协同性”问题,但可分之债领域不存在。据此,可以将德国的共同法学说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实现方式大体归纳如下:(图略)综上所述,就实现方式来看,可分之债和不可分之债都可采连带方式。近代早期法国和德国的共同法学者在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上已经认识到了“协同性”的存在,但该“协同性”尚未从连带性概念中独立出来。
(二)现代法
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对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所确立的规则基本承袭了朴蒂埃的理论:可分之债以按份方式为原则(第1220条第2款),但在清偿不可分领域,数继承人则须承担连带债务(第1221条第1款第5项);不可分之债则以连带方式为原则(第1222-1224条),但数人继承的不可分债务在实现方式上则具有协同性(第1225条)。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第1221条第2款最后一句的规定,在清偿不可分的场合,各继承人均得被诉请清偿全部债务,但对其他共同继承人有求偿之权利。此种连带性的规则显然背弃了朴蒂埃的“协同性”理念。而2016年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320条则进一步抛弃了原第1225条的“协同性”规则。因此,在当代法国法上,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统一采用连带性模式。据此,可以将当代法国法上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实现方式归纳如下:(图略)意大利民法典在总体方向上回归了古典罗马法的方案:将不可分之债基本归于连带之债。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及其主流解释理论,在多数债权人或者多数债务人的场合,给付的可分性导致按份之债的关系,除非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支持连带关系(第1314条);而给付的不可分性本身就意味着连带关系——适用连带之债的规则调整(第1317条)。因此,多数人不可分之债构成连带之债的一种亚类型。[48]尽管如此,不可分债权在实现方式上须适用特殊的协同性规则:为实现全部债权而提起诉讼的债权人的继承人应当为其他共同继承人提供担保(第1319条)——该规则源自温德夏特。据此,可以将当代意大利法上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实现方式归纳如下:(图略)德国民法典及其法教义学理论则明确引入了“协同之债”作为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49]在德国民法上,可分之债在传统上以按份方式为原则(第420条)。但是,由于在共同的合同债务领域(第427条)和多数人侵权领域(第840条第1款)普遍适用连带债务,该原则已经被颠覆。不可分债务依据第431条的规定适用连带规则,但这只是原则,基于协作关系或者以共同共有财产为给付标的的多数人债务则适用“协同债务”(gemeinschaftliche Schuld,也译“共同债务”)规则。不可分债权同样存在连带和协同两种实现方式,但依据第432条的规定,“协同债权”(gemeinschaftliche Forderungen或Mitgl?ubigerschaft,也译“共同债权”)显然是原则。据此,可以将当代德国法上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的实现方式归纳如下:(图略)
(三)小结
对于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传统民法以按份之债为原则,[50]例外的情况适用连带之债。[51]但在现代民法中,连带之债的适用范围日益扩大。以德国为例,无论是依合同产生的多数人之债还是由侵权导致的多数人责任都普遍适用连带之债,所以可分之债以按份为原则的思路已经与实践相脱节。此外,主要法域的民法典上没有出现过对可分之债采用协同实现方式的规定,但依传统理论未为不可:在可分与不可分的区分仅采用“分部标准”的场合,各个协同债务人或者各个协同债权人可以共同履行部分给付或者共同受领部分给付。因此,从理论上讲,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可否包括协同之债,取决于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采用何种标准。但比较法上的现实情况表明,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主要采用的乃是“分人+分部标准”,在此体制下,可分之债排除协同形式。就不可分债务而言,绝大多数法域将其实现方式归为连带债务,[52]个别法域则不同程度地承认不可分债务的“协同性”。[53]就不可分债权而言,其实现方式同样包括连带和协同两种方式,多数法域倾向于协同方式。[54]总体来看,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可分之债一般以按份或连带作为其实现方式,而不可分之债则以连带和协同作为其实现方式。中国法学会提交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建议稿”与2016年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320条类似,对不可分之债统一采用连带性模式。[55]这不仅在理论上有失偏颇,而且也与我国的司法实践不完全吻合。在我国的相关案例中,固然不可分债务都采用连带方式,但在有关不可分债权的案例中,我国法院的裁判却与协同方式更为吻合。比如,在刘晓光等诉王和平股权转让及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数人各自拥有的股权和债权被打包出售后,该数人共同享有的价款债权构成不可分债权。由于债权人之间无分配约定,出售财产的总价虽约定明确但各项股权和债权的价值很难进行评估,法院据此裁定驳回部分债权人主张全部价款的请求。[56]在高晓莉与上海莘闵荣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史俊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中,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共同购买人请求出卖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债权构成不可分债权,在债权人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法院认为任一债权人无权单独请求债务人履行约定的过户义务,而且任一债权人迟延,债务人不得向其他债权人履行该义务。[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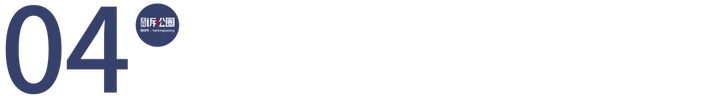
多数人之债的体系和协同之债的确立
(一)多数人之债的理论体系与立法模式的选择
综合以上分析,现代民法关于多数人之债的理论体系主要借助于两种类型化方案:一种是基于债的标的(给付)的视角,根据其可否分割,区分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另一种则是基于债的主体的视角,根据复数主体(数个债权人或者数个债务人)之间的牵连程度,区分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和协同之债。按照比较法上的主流观点,两种方案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归纳如下:(图略)就立法模式的选择而言,在确立了多数人之债的立法体系以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为主要类型的基本格局下,若同时设置不可分之债,在实践和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其一,从实践功能来看,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和协同之债乃是实践中实现多数人之债的最终方式,而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并不具有终局的实践意义。它只是确定多数人之债的实现方式的一种中间性的辅助手段,而且由于二者的区分在标准上存在分歧且操作复杂,该辅助手段的实用价值有限。其二,从逻辑上讲,不可分之债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不处于同一逻辑层面,因此,在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之外平行规定不可分之债,在逻辑上存在缺陷。其三,从内容上讲,围绕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所形成的传统规则也大多与按份之债、连带之债以及协同之债这三种实现方式密切相关,[58]因此,规定不可分之债在内容上与连带之债存在重叠,容易引发矛盾。综合上文研究,未来中国民法典关于多数人之债的立法,应当不采传统大陆法系将可分之债、不可分之债与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并列或者混合规定的模式,而采取以债的实现方式为导向的类型化模式: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以外,设置“协同之债”的规定。[59]根据这一总体思路,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划分仅宜作为法教义学上的一种辅助性的解释模式,而协同之债则应在理论和立法上予以确立。
(二)协同之债的理论体系与立法建构
1.协同之债的概念。协同之债作为一种与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并列的多数人之债的实现方式,是现代民法理论的产物。德国现代民法教科书对于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已明确采用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和协同之债的三分法;[60]意大利的权威学说也采纳该三分法。[61]在本文开篇提及的一系列国际性的示范文本中,协同之债及上述三分法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可见,承认协同之债的法律地位已经成为现代民法的一种趋势。中国民法学上关于“协同之债”的概念源自史尚宽的《债法总论》,这一概念在我国台湾学界仍在沿用。[62]但是,与德国现代民法上的“协同之债”相比,我国台湾民法理论上的“协同之债”是在狭义上使用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多数人之间存在协作关系的领域,比如数人协作建房或协作演奏,而多数人之间存在(按份或共同)共有关系的领域则属于另一独立的范畴“共有之债和准共有之债”。[63]德国现代民法上的“协同之债”则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除了适用于协作关系领域外,也适用于共有关系领域,只要共有人之间在债的实现上存在协同性。[64]意大利法学的一般观点倾向于狭义说,但也有观点支持广义说。[65]基于理论上的争议,国际示范文本在此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从国际示范文本的条文来看,“协同之债”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概念,其根本特征是多数债务人或者多数债权人在债的实现上存在协同(即协作)关系,共有关系并非必须,但也不被排斥。[66]从上述示范文本的评注中所举到的例证来看,“协同之债”虽以协作关系的案型为主,但个别例证也涉及到共有关系。[67]综合上述情况,从理论的统一性来看,广义说更为可取。协同之债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协同性”(或“协作性”),即“共同实施性”,它要求给付必须由全体债务人或者为了全体债权人而共同实施。在多数债务人的场合,给付必须由全体债务人共同履行,任一债务人不得单独履行该给付,此之谓“协同债务”;而在多数人债权的场合,给付必须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主张和履行,任一债权人不得单独受领该给付,此之谓“协同债权”。据此,由任一债务人或者为了任一债权人而单独履行,不能导致债的消灭并且可以被依法拒绝,这正是所谓“共同实施性”的理论实质。就复数主体(数个债权人或者数个债务人)之间的牵连程度来看,较之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协同之债的牵连性最强——必须全体共同参与债的实施(履行或受领);连带之债次之,无须全体共同参与实施,但复数主体之间却互享权利、互担责任;按份之债的牵连性最弱,复数主体彼此独立行使各自的权利、承担各自的义务。“共同实施性”要求多数债务人或者多数债权人之间协同配合,这在实践中可以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履行或受领由全体债务人或全体债权人共同参与,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全体债务人或者全体债权人就实施方式达成协议,表现形式就是共同委托代理人来实施履行或受领。2.协同之债的类型。由上文可知,协同之债的发生乃基于两种情况。其一是基于多数债务人或者多数债权人之间存在协作关系。其中,协同债务的典型例证包括数人共同承包建筑,数人合作演出或者合作创作作品,数名保管人分持秘钥共同保管一保险箱以及房屋的共同承租人对出租人承担的到期返还债务等。协同债权的典型例证包括排演戏剧的数名演员根据与摄影师的协议要求其拍摄成影片的债权,结伴旅游中旅游成员对旅行社所享有的服务性债权,房屋的共同承租人对房屋的租赁权,共同寄存人要求返还寄存物的债权、联名账户的数个拥有者对银行享有的债权以及共同购车人所享有的车辆交付请求权等。其二则是基于多数债务人或者多数债权人之间存在共有关系,包括按份共有人对不可依数量进行分割的给付标的所共同享有的债权,共同共有人所共同享有的债权以及共同共有人以共有财产为限所负担的债务(包括给付共有物的债务和以共有财产负担之给付金钱的债务)。分析上述协同之债的典型情况不难发现,所谓的“协同性”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当然的协同性”和“推定的协同性”。根据给付的性质和债的目的,只有协作给付才是实现债的目的的唯一方式,此之谓“当然的协同性”,协同之债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此类。但在多数人债权的场合,如果债的目的不够明确,则给付究竟采用哪种方式(按份、连带或协同)也就无法确定,比如共同寄存人要求返还寄存之大米的债权和联名账户的数个拥有者对银行享有的金钱债权,债的目的或者债权人的利益所在是债权人(共同寄存人、联名账户拥有者)按份享有利益还是共同享有利益?如果是共同享有,是连带性共享还是协同性共享?再如数人共同出资购买一辆汽车,该数名购买者所共同享有的车辆交付请求权,依给付的性质可排除按份债权的可能性,但究竟是连带债权还是协同债权亦无法确定。这些情况既无当事人的约定,也无法律的规定,交易习惯也不够明确,从理论上讲,按份、连带或协同之中至少有两种方式均可实现债权。此时,对履行方式的选择应当顺次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何者对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最有利;其二,何者对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最稳妥。在债权总量恒定的情况下,基于各个债权人利益的不明确和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对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最有利的方式”无法确定,于是,只能诉诸对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最稳妥的方式”:由于按份方式须确定各个债权人的份额,而连带方式则须确定任一债权人可否行使或代理行使全部债权,在这些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协同方式既无须划分份额,又是在所有债权人参与下实施的,实乃履行此类债权最为稳妥的模式。此之谓“推定的协同性”。相形之下,在多数人债务领域,如果出现了上述给付方式上的不明确,比如数人共同出资购买一辆汽车,该数名购买者所共同负担的付款债务,则应当推定以连带债务为原则。理由是,在此场合,债权人的利益是明确的,而连带方式最有利于实现债权人的利益。由上文可知,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上,类似的推定仅限于不可分之债:不可分债务适用连带债务规则,而不可分债权则适用协同债权规则。但基于连带债务在可分债务领域的适用范围日益扩大,而多数人债权又通常以不可分为主——因为多数债权人结合于同一债权往往基于协作关系或者共有关系,[68]所以,将传统上适用于不可分之债领域的推定扩张到整个多数人之债领域,也符合该领域的发展现状。[69]3.协同之债的效力。与连带之债类似,协同之债的一般效力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协同之债在对外效力上的“协同性”或“共同实施性”乃是协同之债独有的特性。协同之债的共同实施性可以概括为两种实现方式:数人(债权人或债务人)协作实施或者由共同委托的人实施。正是由于协同之债的共同实施性,多数债权人或者多数债务人内部往往无追偿和分担问题。[70]这里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协同债权的对外行使方式上:该种债权可否由任一债权人单独主张?[71]该争议的实质在于,协同债权实现方式上的“协同性”或“共同实施性”是否体现在给付的请求上?从比较法上的通行模式来看,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无论是传统的不可分债权(采协同方式)还是现代的协同债权,给付的请求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任一债权人仅得请求债务人向全体债权人履行给付;[72]其二,任一债权人仅得为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请求债务人履行;[73]其三,任一债权人得请求全部给付,但须提供担保。[74]在上述三种形式中,任一债权人均得单独主张债权,[75]尽管在确保该主张系基于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方面有不同形式的要求。根据主流理论,“协同性”或“共同实施性”并非体现在给付的请求上,而是体现在给付的受领上。[76]据此,任一债权人都可以单独向债务人主张乃至单独起诉。但该通行模式在司法实务上则存在障碍:如果允许一人起诉,由于多数债权人之间缺乏协调,所以判决书所确定的履行时间、地点、方式等具体内容对未参加诉讼的其他债权人将是不公平的,而不确定上述内容则将大大降低法院判决书的可执行性。因此,基于诉讼实践的考虑,似乎只有起诉得到全体债权人的参与或同意,法院判决方可对全体有效。但如果据此改采全体债权人共同主张说,则一旦部分债权人懈怠,其他债权人的给付请求即无法产生法律效力,这对后者的利益保护极为不利。综合考量之下,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更合理的方案仍应当是遵循通行模式,允许任一债权人单独主张或起诉。[77]但是,基于判决的公平和实效,法院应当通知其他债权人参加诉讼,如果其他债权人拒绝参加诉讼,则法院的判决对其他债权人仍旧有效。[78]4.增设协同之债的实践必要性与立法建议。除了基于多数人之债法律体系上的完备性要求,从我国审判实践的需求来看,在立法上增设协同之债规则也是非常必要的。以上文提及的两起案件为例,实际上协同之债的问题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已经出现,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立法规定,导致法院在裁判依据上的混乱和欠缺。在“刘晓光案”中,法院以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起诉条件)为依据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意指原告的起诉资格不符合条件。作为理由,法院援引了“不可分债权”理论:不可分债权人之一无权诉请合同价款之全部——这实属采用协同形式的不可分债权(即协同债权)。但该理论显然不能作为否定原告起诉资格的理由。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项的规定,原告只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即为合格。本案的原告大多数都是被转让之债权的债权人和被转让之股权的股东,尽管个别股东未起诉,起诉的股东中部分人也仅仅系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但这些缺陷并不妨碍已经起诉的债权人和股东都“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和上述理论解释裁定驳回起诉是不合适的。“高晓莉案”中,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合同法第107条(违约责任的构成),意指共同购房人中仅一人向卖房人主张过户(实为要求过户到该一人名下),卖房人拒绝配合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作为理由,法院同样援引了“不可分债权”(实为协同债权)理论:不可分债权人之一在债权人内部意见并不一致的情况下无权单独请求债务人履行。以此排除被告构成违约是有理论依据的,但这并非法定依据。鉴于我国合同法采用严格责任原则,被告的不履行行为没有法定的免责依据,尚不足以排除违约。因此,本案在裁判依据上仍显得不够充分。对这两个案件的裁判依据的分析表明,仅凭现有的法律规定不足以裁判此类案件,而且容易导致解释上的混淆。只有不可分之债或者协同之债才是统一此类案件裁判的有效依据,而根据上文的研究结论,协同之债显然是更优的选择。此外,两案裁判对于协同债权人之一单独请求债务人履行所持的否定观点,根据上文的研究,也并非理论上最合理的方案。因此,尽快在立法上确定“协同之债”的必要规则,一方面可以为此类案件的裁判和解释提供统一、有效的实定法依据,另一方面则可以避免或减少实践和理论上存在的分歧。基于协同债务和协同债权的相关理论特点,参考三部国际示范文本的做法,未来民法典对协同之债的规定宜采用概括性模式。综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建议增设如下条文:“二人以上承担协同债务的,应当由全体债务人协作履行或者由全体债务人委托的人履行。二人以上享有协同债权的,任一债权人仅得请求债务人向全体债权人或者全体债权人委托的人履行。多数人之债的实现方式无法确定的,多数债务人承担同一给付的,为连带债务,多数债权人享有同一给付的,为协同债权,但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习惯的除外。”
注释:
[1]参见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1197-1225条和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309-1320条。根据法国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的《关于合同法、债法一般规则与证明的改革法令》,前者被后者取代,尤其是原法国民法典有关“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九条规则(第1217-1225条)被简化至修订后的第1309条和第1320条之中(修订后的条文中译本,参见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债之渊源(准合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页以下)。基于修订前的条文在历史传承和比较法上的重大意义,本文仍将详细分析,对修订后的变化也将作出说明。另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20-432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292-1320条,我国台湾民法第271-293条。
[2]由于我国未来民法典不设置“债法总则”,有关多数人之债的规定将被置于“合同编”的“合同的履行”一章中。2018年12月份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在该章中只规定了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第308-312条),但第308条对按份之债的界定添加了“标的可分”的条件:“债权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的,为按份债权;债务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负担债务的,为按份债务。”这一将“可分性”与“按份之债”融合规定的做法有借鉴大陆法系传统模式的旨趣,但又非将后者作为前者的实现原则,这就导致该添加的实践意义不大,在解释适用上甚至略显多余:因为从逻辑上看,“标的可分”实乃“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或各自分担债务”的应有之义。[3]中国法学会提交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建议稿”第73条规定:“数人分享同一债权或者分担同一债务,其给付不可分的,则各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全部债权,各债务人也应当向债权人履行全部债务。债务履行后,各债权人或各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内部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处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交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建议稿”第126条分三款分别界定了连带债权、按份债权和共同债权(即“协同债权”)。其第3款规定:“在多数债权人中,任何一个债权人只能基于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请求履行,债务人必须向全体债权人履行债务的,为共同债权。”[4]《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0-101条和第10-201条将多数债务人或多数债权人分为三种类型:连带债务或连带债权(solidary obligations or claims)、按份债务或按份债权(separate obligations or claims)、协同债务或协同债权(communal obligations or claims)。中译本参见欧洲合同法委员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三部分》,朱岩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0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1页以下。《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102条和第3-4:202条基本沿袭此前完成的《欧洲合同法原则》,也作出了类似的分类:连带债务或连带债权(solidary obligations or rights)、按份债务或按份债权(divided obligations or rights)、协同债务或协同债权(joint obligations or rights)。中译本参见[德]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三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43页,第868页。《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1.2.1条将多数债权人分为三种类型:按份债权(separate claims)、连带债权(joint and several claims)、协同债权(joint claims)。中译本参见张玉卿:《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第827页。[5]目前,中国大陆在该领域仅有齐云的专著,王利明在其债法著作中对不可分之债也有论述,此外则是各民法教科书中的简单介绍。这些著述涉及了不可分之债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分标准、不可分之债的实现方式、一人所生事项之效力。在第一个问题上,张广兴主张给付是否可分的根本标准在于给付的分割是否会影响债的目的(给付的价值)的实现,具体则须结合给付在性质上、物质上的特点以及当事人约定等因素判断;王利明主张应当根据给付的性质、债的目的、当事人的意思、交易习惯和用途等因素综合考量;齐云主张根据所谓的“整体观念和整体价值”区分客观可分与客观不可分,客观可分仍可因当事人的特别约定或者立法规定而归于主观不可分。在第二个问题上,王利明主张不可分债权以协同实现为原则,而不可分债务则应当以连带履行为原则;齐云的观点则倾向于不可分债权和不可分债务都采协同实现方式。在第三个问题上,在不可分债权领域,王利明和齐云均同意债权人受领迟延具有绝对效力,而免除则只具有相对效力,但在不可分债务领域,王利明则未予讨论。参见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以下;王利明:《债法总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以下;齐云:《不可分之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第168页,第177页,第181页。[6]讹误主要体现为将不可分债务与连带债务相混同。大量案例表明法院将发生在欠款、欠薪、损害赔偿领域的给付金钱的数人连带债务认定为不可分债务。参见吴贺军、侯翠荣与邳玉明民间借贷纠纷案,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5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书;庞郡与蒋学元等债权转让案,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8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杭州蓝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与叶茂洪、叶爱锦、杭州胖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474号民事判决书;刘玉东、张春义与张连杰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2012)沈民初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书;李建兰诉江西武功山中山脆鲩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申请支付令案,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2017)赣0323民督1号民事裁定书。[7]理论上仅有的论述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5页以下。该书参照当代德国的理论,将协同之债称为“债务人共同体”和“债权人共同体”。[8]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页。拉丁文本中的ipso iure也可以译作“依法”,比如徐国栋等《〈十二表法〉新译本》(《河北法学》2005年第11期,第2页)就将该条译为:“继承的债权和债务,依法按其继承的遗产份额分配给继承人。”[9]同上书,第291页。[10]该观点出自意大利罗马法学者彼德罗·彭梵得:“不可分之债对于罗马法学家而言就是连带之债”,“真正的不可分性就是连带性”。See Pietro Bonfante, La Solidarietà Classica delle obbligazioni indivisibili, in Scritti Giuridici Varii, III, Torino: UTET,1926, pp.368-369.[11]同上文,第369页以下。除此以外,彭梵得认为,在不可分债务场合债务人要求延期履行的权利和在不可分债权场合债务人要求提供保证的权利,也体现了按份之债的特点。参见前引[8],彭梵得书,第292页。但根据下文分析,延期履行和提供担保这两种情况体现的更主要是不可分之债实施上的“协同性”。[12]前引[10],Bonfante文,第375页。[13]杜穆林在此领域的代表作为《解开可分与不可分的迷宫》(Extricatio labyrinthi dividui et individui)。关于此书的基本内容参见前引[5],齐云书,第71页以下。[14]See M.Pothier, Treatise o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or Contracts, Volume I, Translated by William David Evans, Philadelphia: Robert H.Small,1826, Contents (Part II, Chapter III and IV) and p.92(paras.[176] and [178]).[15]See F.C.Savigny, Le Obbligazioni, Volume 1, trad.G.Pacchioni, Torino: UTET,1912, Indice (Capo 1,§III,§IV); B.Windscheid, Diritto Delle Pandette, trad. C.Fadda e P.E.Bensa, Volume 2, Parte 1, Torino: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1904, Indice (Libro 4, Capitolo 1,§II,§IV).[16]以下关于朴蒂埃的学说参见前引[14],Pothier书,第152页以下。[17]朴蒂埃还举了一个“转让土地用以建设酒庄”的例子:土地本身在性质上是可分的,但作为债的标的,该土地特定的建设用途决定了该土地是不可分的。参见前引[14],Pothier书,第155页以下。[18]对于清偿不可分的第三种情况,朴蒂埃举出的示例为出售和出租地产的不可分性、给付救人出狱的赎金的不可分性。参见前引[14],Pothier书,第169页。[19]参见前引[15],Savigny书,第295页,第306页。[20]同上书,第325页。[21]参见前引[15],Windscheid书,第141页以下。[22]温德夏特指出,给付在性质上的可分性虽然可以从给付标的物的自然属性(比如数量、性状)去判断,但更主要应根据其“在观念上而非物质上”(intellectu magis partes habeant quam corpore,D.45,3,5)的属性去判断——其实质是给付标的的权利份额。参见前引[15],Windscheid书,第13页,注[4];B.Windscheid, Diritto Delle Pandette, trad. C.Fadda e P.E.Bensa, Volume 1, Parte 2, Torino: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1925, p.12。[23]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的相关中文和英文译本也将第1218条中的“债的关系”译作“债务的本旨”或“债的本意”。参见《拿破仑法典》,李浩培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24]以上观点参见C.Demolombe, Traité des Contrats ou des Obligations Conventionnelles en Général, Tome 3, Paris: Auguste Durand,1870, p.457。[25]参见张民安:《法国民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页。[26]前引[25],张民安书,第289页。[27]需要说明的是,意大利民法典的中译本(费安玲等译)将“缔约当事人的看法”译为“缔约双方确定的给付方式”,在含义上实有偏差。[28]由于意大利法采按份共有原则(意大利民法典第1100-1101条),因此不可分物的共有人可以通过分别出售各自份额的形式出售该共有物,也可依据买回协议按份额买回已经出售的共有物(意大利民法典第1507条、第1508条)。关于不可分之债的意大利法教义学理论,参见C.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IV.L’obbligazione, Milano: Giuffrè,1993, p.754。[29]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02页,第617页。[30]比如,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1219条、阿根廷民法典第668条、魁北克民法典第1521条、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1820条均规定,约定连带之债不等于不可分;意大利民法典第1318条规定数人继承之债不可分;西班牙民法典第1151条规定不作为之债依其特点确定是否可分;阿根廷民法典第669-672条和第679-684条还针对给予之债、作为之债、不作为之债、特定物之债、选择之债、地役权之债、共有物之债乃至抵押和质押的可分性或不可分性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内容多渊源于共同法学说。[31]比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18条规定数人继承之债不可分,但我国法理恰恰相反,数个继承人原则上按各自的继承份额分担债务。阿根廷民法典第679条和第669条分别规定给予特定物之债不可分而给予数量物之债可分,但这只是原则,特定物如果可以度量也是可分的,数量物的分割如果违背债的目的则将沦为不可分。此外,阿根廷民法典第682条还规定了抵押的不可分性,这在学理上更是不妥。姑且不论抵押权非属债权,即使是类推债权,抵押权的不可分性仅指在主债履行完毕之前抵押权始终及于抵押物的整体,但该“整体性”并不排斥抵押权的部分实现——抵押权人仍可就抵押物之部分实现其利益,这一特点与不可分债权相反。[32]立法上明确的表述参见西班牙民法典第1151条、阿根廷民法典第667条。[33]意大利法学家布斯奈利即持此观点。Busnelli, L’ obbligazione soggettivamente complessa, Milano: Giuffrè,1974,p.85.[34]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1220条第1款、西班牙民法典第1149条、阿根廷民法典第673条、魁北克民法典第1522条以及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1816条均规定:在单一之债领域可分之债应如同不可分之债履行之。[35]正如阿根廷民法典的起草者萨尔斯菲尔德(Sarsfield)所言:“债仅在有数个债权人或数个债务人时,才分为可分之债或不可分之债。在只有一个债权人和一个债务人时,债即使可分,也始终应予整体履行,而绝不能部分清偿。”参见《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徐涤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注释[1]。[36]参见我国合同法第72条。[37]参见重庆市博海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鑫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合川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终45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海源机械有限公司与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嘉商终字第386号民事判决书;周雁桂与台山市佳顺物业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7民终1134号民事判决书;贺艳、严嗣杰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38]值得一提的是,“债的关系”在继受法国传统的法域表述上差异较大:意大利民法典第1316条将其表述为“缔约当事人的看法”,魁北克民法典第1519条、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1815条以及日本民法典第428条则将其简化为“当事人的约定”,巴西新民法典第258条则将其表述为“经济秩序之目的”或“法律行为的特殊性质”。[39]参见前引[5],张广兴书,第121页;[日]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IV·新订债权总论》,王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争议在于,如果两个共同共有人出售共有的两头牛,该合同给付在权属性质上是不可分的,但合同约定每个共有人向买方交付其中的一头牛,该可分性的约定是有效的——因为共同共有规则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此存在两种解释:一是,该约定将原来的共同共有关系变更为分别所有,两头牛的权属性质也由不可分变更为可分;二是,该约定被视为共同共有人之间的相互授权,据此每个共有人系代表全体实施部分给付,两头牛在权属性质上的不可分性并未变更,只是变通了不可分给付的履行方式。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此场合下的约定都不违背给付的权属性质。因此,理论上的一般观点是正确的。[40]这些例外情况包括抵押债务,特定物债务,物的返还之债,继承人之一的行为或过错导致标的物灭失的责任,根据协议、遗嘱或者判决须由继承人之一负责的债务以及清偿不可分之债。这些例外情况在实现方式上除了涉及连带之债外,前五种情况还可能仅仅表现为单一之债。参见前引[14],Pothier书,第159页以下。朴蒂埃的上述理论也影响了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1121条的规定。现在看来,这五种情况(单一之债)的理论实质是“债务人(或责任人)的认定”问题,不宜与多数人之债的实现方式混为一谈。[41]20世纪初的法国法学家吉拉尔德(Girard)的观点与此类似,也将债的分割实现(即按份之债)的对立面即不分割实现的债归纳为债的标的不可分和债的主体之间具有连带性两种类型。参见前引[5],齐云书,第22页。[42]参见前引[14],Pothier书,第173页。[43]同上书,第177页。[44]前引[14],Pothier书,第169页。[45]须说明的是,萨维尼一方面看到了“连带性”(solidum)在用法上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指出,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当与分割实施之债(即按份之债)相反对时,连带之债(solidarit?t)与共同之债(correalit?t)是同义的。参见前引[15],Savigny书,第131页。[46]参见前引[15],Savigny书,第348页。[47]参见前引[15],Windscheid书,第168页以下,第172页。[48]参见前引[28],Bianca书,第754页以下(§§385-387)。布斯奈利认为,意大利民法典第1317条和德国民法典第431条的规定说明立法者对于连带性和不可分性的关系回归到了古典罗马法的混同传统。参见前引[33],Busnelli书,第67页,注[128]。[49]参见前引[29],梅迪库斯书,第597页以下。[50]除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的上述规定外,比较法上的类似规定参见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1817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889条、葡萄牙民法典第534条、阿根廷民法典第674-675条、巴西新民法典第257条、我国台湾民法第271条。其中,德国、葡萄牙、阿根廷、巴西、我国台湾的上述规定还明确以均分为原则。[51]比如,依债或标的物的性质以及合同目的可知缔约人的本意是债务不得分为若干部分履行(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1221条第1款第5项),或者依债的设定依据或遗产分割决定任一债务人或继承人应承担全部债务的(阿根廷民法典第676条),或者依合同产生的可分债务(德国民法典第427条),则数债务人或数继承人应当承担连带债务。[52]除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的上述规定外,比较法上的类似规定参见魁北克民法典第1520条、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1818-1819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890条前段、瑞士债务法第70条第2款、阿根廷民法典第686条、巴西新民法典第259条、日本民法典第430条、我国台湾民法第292条、荷兰民法典第6:6条第2款、俄罗斯民法典第322条。[53]除了法国(2016年修订前)和德国的上述情况外,葡萄牙民法典第535条更是明确将“协同性”作为不可分债务的履行原则:债权人仅得要求全体债务人或全体继承人履行给付。相反,连带性则仅适用于约定或法定的场合。[54]除了意大利和德国的上述规定外,比较法上的类似规定参见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890条后段、瑞士债务法第70条第1款、阿根廷民法典第687条、日本民法典第428条、我国台湾民法第293条第1款、巴西新民法典第260-261条。但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1224第1款、修订后第1320条第1款以及荷兰民法典第6:15条第2款采用连带方式。[55]参见前引[3]。[56]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字第12179号民事裁定书。[57]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五(民)初字第1803号民事判决书。[58]比如,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绝对效力和相对效力规则主要用以解决发生于多数债权人或者多数债务人之一的事项对其他债权人或债务人产生何种效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结合可分之债或者不可分之债的具体实现方式(按份、连带或者协同)区别对待。[59]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协同之债是这一类型化体系中的主要形态。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连带之债包括不真正连带债务。此外,根据我国理论和实践的情况,补充债务则属于该体系中的次要形态。[60]参见前引[29],梅迪库斯书,第597页以下;[德]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5页以下。德国法学上称“协同之债”为“协同债务”(gemeinschaftliche Schuld)、“协同债权”(Mitgl?ubigerschaft或gemeinschaftliche Forderungen)。中译文中也译作“共同债务”“共同债权”,但考虑到共同债务、共同债权(或“共同之债”)的用法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已经泛化,往往涵盖所有的多数人之债的形态,所以不宜采用该译法。[61]参见前引[28],Bianca书,第691页,第767页以下;前引[33],Busnelli书,第85页。意大利民法学将“协同之债”表述为obbligazioni collettive(也译“集合之债”)或obbligazione (soggettivamente complessa) ad attuazione congiunta(也译“联合实施之债”)。[62]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9页;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70页。史尚宽使用的“协同之债”的概念可能源自日本,日本民法学理论上承认在共有之债、不可分之债以外还存在着“协同债权关系”,其适用范围与史尚宽和我国其他台湾学者的理论相同。参见[日]於保不二雄:《日本民法债权总论》,庄胜荣校订,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8页,注[5]。[63]参见上引史尚宽书,第699页;上引孙森焱书,第770页。[64]参见前引[29],梅迪库斯书,第603页,第616页。[65]在意大利权威教科书中,“共有之债”(obbligazione in comunione)是“协同之债”以外的多数人之债的独立类型;协同之债的例证也主要是数人协作建房或协作演奏等,而不包括共有之债。参见前引[28],Bianca书,第767页以下;前引[33],Busnelli书,第14页以下。但也有学者(比如E.Grasso)支持广义说:“协同之债”规则也适用于共有之债。转引自前引[28],Bianca书,第773页。[66]《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0-101条(3)规定:“所有债务人必须一同履行并且债权人仅得向全体债务人要求该履行的,该债务为协同债务。”第10-201条(3)规定:“债务人必须向所有债权人为履行并且任何债权人仅得基于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要求债务人履行的,该债权为协同债权。”需说明的是,朱岩的中译文(载前引[4],梁慧星主编书,第651页,第654页)将协同债务和协同债权译为“共同一并之债”和“共同一并请求权”,在此根据英文本(http://www.jus.uio.no/lm/eu.contract.principles.parts.1.to.3.2002/)作出修正。《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102条(3)规定:“若各个债务人须协力一同履行债务,且债权人也仅得请求全部债务人协力一同履行方可实现债权,则为协同债务。”第3-4:202条(3)规定:“当任一债权人仅得为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要求债务人履行,且债务人须向全体债权人履行时,该履行请求权为协同债权。”参见前引[4],巴尔等主编书,第843页,第868页。《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1.2.1条(c)规定:“如所有债权人必须共同请求清偿,则该请求权为共同债权。”参见前引[4],张玉卿书,第827页。[67]参见《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102条和第3-4:202条的评论(前引[4],巴尔等主编书,第843页以下,第869页以下)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1.2.1条的注释[3](前引[4],张玉卿书,第831页)。只有《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202条的评论中举到的合伙人在银行开立联名账户的协同债权(示例1)涉及合伙人的共有关系。[68]德国的主流理论认为多数债权人之间几乎总存在共同共有关系或者按份共有关系,而基于共有关系的多数人债权多属不可分范畴。参见前引[29],梅迪库斯书,第602页。[69]比较法上的另一种做法则对多数人债务和多数人债权均采按份之债的原则,参见日本民法典第427条、荷兰新民法典第6:6条第1款和第6:15条第1款、俄罗斯民法典第321条。《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203条将此原则仅限于多数人债权。笔者认为,按份的做法不符合对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最有利”或者“最稳妥”的原则。[70]参见前引[28],Bianca书,第770页。我国台湾学理认为,协同之债的各个债权人或者各个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依据约定或者协同行为的性质定之,无法确定的,平均分担或分受之。参见前引[62],史尚宽书,第699页;前引[62],孙森焱书,第772页。仔细分析,需区分协同债务和协同债权:协同债务只有在转化为连带债务或者按份债务后才有内部追偿或分担问题,协同债务本身不存在该问题;协同债权人乃共同享受服务或者共同受领财产,共同享受服务后不存在内部关系问题,共同受领财产后则存在内部关系问题,处理方案需根据产生协同性的基础关系来确定,无法确定的,各个债权人之间应平均分享。[71]我国台湾的理论和实践围绕“公同共有债权之行使”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司法界的意见认为不得单独主张,只有所有债权人作为共同原告起诉方为适格;而理论界的多数意见则倾向于任一债权人均可单独主张债权。参见王千维:《公同共有债权之行使》,《月旦法学教室》第160期(2016年2月),第64页以下;吴从周:《公同共有债权之行使》,《中德私法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页以下。我国大陆地区的相关裁判倾向于前者的意见,参见前引[56]、〔57〕及下文详解。[72]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32条第1款、瑞士债务法第70条第1款、我国台湾民法第239条第1款。[73]参见日本民法典第428条、《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202条第3款。[74]参见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890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319条。[75]作为例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1.2.1条(c)要求“所有债权人必须共同请求清偿”(见前引[66])。[76]参见前引[29],梅迪库斯书,第601页;前引[7],王洪亮书,第489页。[77]我国台湾学者吴从周提出对于“公同共有债权之行使”原则上应由全体债权人共同主张,但在“事实上无法得同意”的例外情况下允许各债权人单独起诉,其他共有人反对或者共有人之间利害关系相反也属于该例外范围。参见前引[71],吴从周文,第161页以下。由于上述例外的范围较宽,这在实际上无异于认可各债权人的单独起诉原则。而且,允许单独起诉也更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78]作为补充,如果该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的规定,其他债权人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判决的履行或执行阶段,如果债权人之一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的,应视为放弃,其他债权人仍得请求受领全部给付,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应适用不当得利规则予以补救。如果债权人之一不受领系有正当理由,则可以由其他债权人代为受领,如有必要,可以由其他债权人在受领给付时向债务人提供担保。这里还可能涉及其他制度的配合,比如在债权人之一失踪的场合,需通过宣告失踪程序为其指定财产代管人。此外,协同之债的效力还涉及两个特殊问题。其一,针对协同债务人之一或者协同债权人之一发生的事项对其他债务人或者其他债权人具有何种效力。理论上存在三种可能性:绝对效力(即对其他债务人或债权人产生相同效力)、限制绝对效力(即对其他债务人或债权人产生有限效力)或者相对效力(即对其他债务人或债权人不产生效力)。其二,由于协同之债的给付标的往往指向特定行为或者特定物,因此,当特定行为或者特定物的给付不再可能从而导致损害赔偿时,协同之债在实现方式上是否会发生转化,理论上也存在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转化为连带之债或者按份之债或者其他形式。以上问题所涉情况复杂,立法上不宜作全面统一的规定,而应留由司法裁判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