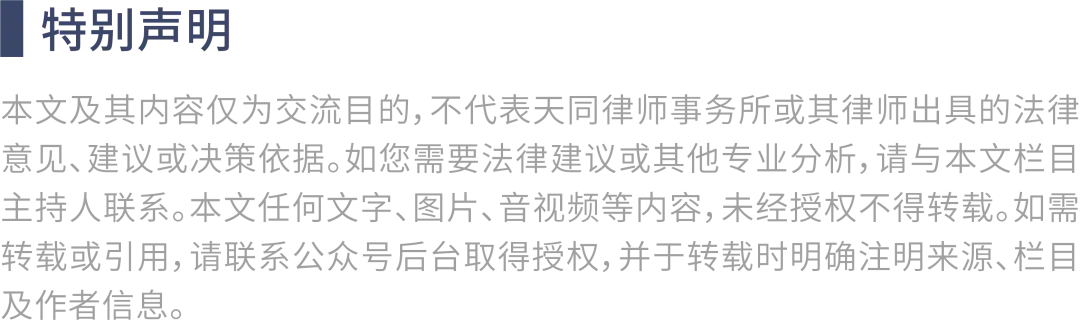注:本文原载于《南大法学》2022年第6期。
摘要:各类组织法行为存在效力瑕疵时,我国多数观点认为应当排除瑕疵之溯及力,这主要继受自欧陆各国广泛存在的“瑕疵组织理论”。但该理论的正当性值得讨论。在外部关系中,表见代表、表见组织、股权善意取得、商事登记公信力等权利外观理论在功能上可以替代瑕疵组织理论,且更具个案灵活性。在组织内部关系中,财产清算的复杂性并非排除无效溯及力的正当理由;组织设立无效时通过认定组织财产为成员按份共有,组织增资无效时通过认可不当得利法上的获利返还规则,均可克服无效溯及后财产返还的不公平问题。内部关系重在成员间合理分配经营风险,实现意思瑕疵救济与成员平等保护的务实协调,瑕疵组织理论僵化地按投资比例分配经营风险,在意思瑕疵救济方面有所不足。
关键词:相对信赖保护;绝对交易安全保护;清算困难;风险共同体;投资者竞赛
目录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外部关系:权利外观理论替代瑕疵组织理论?
三、 内部关系:清算困难与经营风险分配
四、 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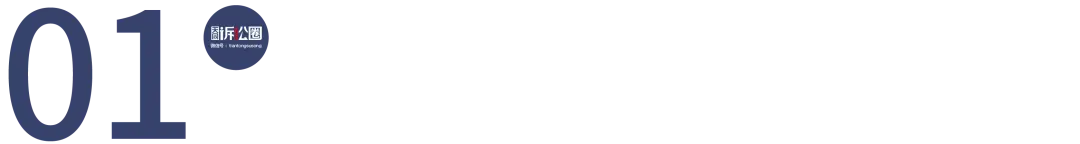
问题的提出
例1(有限公司设立):杨立鑫、阮奇恩和郑定银发起设立中欣公司。由于阮奇恩故意隐瞒了法国籍身份,杨立鑫以受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公司设立合意。[1]
例2(有限公司增资):鑫控公司是一家民企,为融资便利,与国企中科建公司达成挂靠约定:中科建公司虚假增资入股鑫控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名为股权、实为债权”),并完成工商登记。后中科建公司陷入破产,鑫控公司起诉请求确认中科建公司不享有鑫控公司股权。[2]
例3(合伙企业份额转让):中融国际将其持有的中绒圣达(普通合伙企业)10亿元份额转让给灵武公司。灵武公司主张中绒圣达向其出具的财务报表和承诺函中存在虚假陈述,请求法院撤销转让行为。[3]
例4(合伙合同):张光明与欧长生订立合伙合同,约定张光明加入欧长生的“黄金冠”桃树种植事业。后桃树结果,双方才发现欧长生当初种植的并非“黄金冠”,而是外表十分相似的其他品种果苗。张光明主张基于重大误解撤销合伙合同。[4]
例5(基金合同):洪利与信文公司签订私募基金合同。2年后,基金遭遇亏损,洪利以信文公司当初未依约回访确认为由,主张行使约定解除权,请求返还全部投资本金。[5]
以上案例均系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从它们涉及的现象可以概括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各类组织法上的行为[6] 而言,无效、可撤销等效力瑕疵是否具有溯及力?这些行为是否适用法律行为一般规则,从而无效应系自始无效,抑或应当依据“组织法的特殊性”仅面向未来地无效,或根本排除无效之可能?
对此问题,我国法院立场不一。例如,对于案例1中的公司设立瑕疵,有的法院认为“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公司自始未设立,发起人未取得股东资格;[7] 有的法院则认为,“为保持公司主体的存续和稳定,维护公司、无过错一方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受欺诈方应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实现退出,[8] 这实际上排除了组织行为的无效性。又如,对于案例2中的股东通谋虚伪增资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5次法官会议纪要认为,增资行为可适用法律行为一般规则,自始无效;[9] 而有的法院则认为,考虑到“从保护公司稳定性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出发,不宜认定增资无效”。[10]
我国学说多数观点认为,应对组织行为效力瑕疵的溯及力进行限制。[11] 近来更有有力学说主张应从“自始无效+外部关系适用表见代表”的“民法范式”[12] 转换至“组织法范式”:为维护组织关系的安定性,原则上在内外关系中均应排除无效之溯及力。[13]
实际上,这一观点已十分接近欧陆法上的“瑕疵组织理论”(Lehre der fehlerhaften Gesellschaft)。该理论认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要件——组织行为已真实成立、经商事登记或进入执行(in Vollzug gesetzt)、不存在更优位的利益值得保护(优位利益如未成年人保护、严重违法或背俗,但不包括欺诈、胁迫等[14]),即使组织行为存在瑕疵,也不会归于无效或可撤销,相关情事仅构成公司解散、减资或退伙之事由,在反向行为生效之前,相关组织法行为仍完全有效。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极广,不仅适用于资合公司,也适用于合伙企业、合作社、财团法人,乃至合伙合同等;不仅适用于组织设立行为,也适用于组织运行中的各类结构变更行为,可谓“组织法的一般原理”。[15] 欧陆各国法上基本均存在类似理论,[16] 其在《欧盟公司法指令》[Directive (EU) 2017/1132]第12条中也有所体现。在英美法上,也存在实质相似的“事实公司”(de facto corporation)理论。[17] 事实上,我国学理很早就在个别问题点上对瑕疵组织理论有过引介,例如公司法学者大多支持严格限制公司设立无效事由以及主张无效的期间;[18] 前已述及的学者对决议瑕疵问题积累的丰富讨论,其实也是瑕疵组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我国学理在限制无效继续性关系的溯及力、事实合伙关系、事实劳动关系等问题上,也受到了瑕疵组织理论的重要影响。[19]
不过,瑕疵组织理论或者排除组织行为无效溯及力的观点,仍然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主流观点认为,瑕疵组织理论的实质正当性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在组织外部关系中,认定组织行为自始无效会波及对外交易行为,难免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其二,在组织内部关系上,组织关系在长时间内已经发生多次变动,清算返还不但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而且依据所有物返还或不当得利规则清算经常不尽公平。但是,在外部关系中,善意第三人已经可以受到商事登记的公信力、股权善意取得、表见代表等外观主义制度的保护;一律排除组织行为无效的溯及力,反而会使恶意第三人也受到保护。看起来,瑕疵组织理论不仅是不必要的,更是超出规范保护目的的。
在内部关系中,瑕疵组织理论的适用也颇成疑问。首先,很多案例中的清算并不复杂,意思瑕疵之人可能在组织行为作出后很短时间内即主张无效,清算并无障碍。其次,清算困难本质上乃证明问题,若意思瑕疵之人可举出大量证据证明每一笔组织行为的存在,法官又有何理由拒绝清算?很多大型商事交易或建设工程交易中,“算账”的难度恐怕远在组织行为瑕疵之上。最后,更重要的是,组织行为存在瑕疵,意味着相关成员的意思自治存在瑕疵,例如增资或入伙时受到欺诈,要求投资人承担经营风险,如此大幅度地偏离意思瑕疵救济的一般规则,是否具有充足的正当性?
基于以上疑问,本文将讨论重点放在瑕疵组织理论的规范目的或正当性方面。下文将先从外部关系开始,讨论多种信赖保护规则是否足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其与瑕疵组织理论优劣几何;然后集中于内部关系,检讨在成员关系中排除无效溯及力的各方面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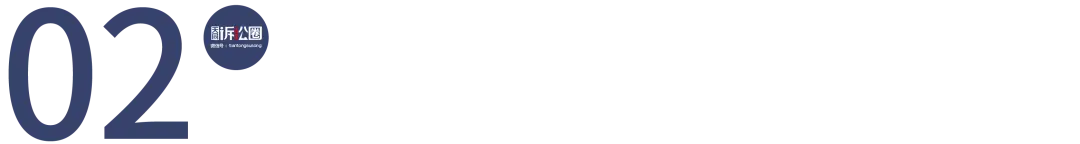
外部关系:权利外观理论替代瑕疵组织理论?
据德国学者考察,瑕疵组织理论的提出受到了法国学理的影响,其被创设出来的初衷正是为了保护组织外部的债权人。[20] 不过,某一理论在历史上发展并不代表其在今天仍然必要,特别是权利外观理论经卡纳里斯的推动有了大幅发展后,瑕疵组织理论的意义值得重新检讨。[21] 下文将区分资合组织(公司)和人合组织(合伙企业),结合对组织法领域中各类善意第三人保护必要性的辨析,比较瑕疵组织理论和权利外观理论的优劣。
(一) 资合组织领域中的信赖保护
在典型的资合组织有限公司中,会波及外部第三人利益的瑕疵组织行为主要包括公司设立行为、增资行为和影响对外代表权分配的组织行为(如法定代表人任免)。就最后一类行为而言,第三人可以受到《民法典》第65条商事登记公信力或第504条表见代表的保护,并无疑问。值得讨论的是,公司设立或增资无效时,第三人(包括股权受让人、股东的一般债权人以及公司的债权人)应否以及如何受到保护。
1. 公司增资无效
首先,当公司增资无效时,从增资股东处受让股权之人(或就股权设定担保的质权人),应当能够基于对工商登记之信赖而善意取得股权。[22] 或有观点认为,股权善意取得的前提是股权真实存在,而公司增资无效时,股权从未被有效创设出来。这一观点应系对善意取得制度本身的误解,善意取得虽然以处分客体存在为常态,但并不以此为必要,例如我国《民法典》第763条虚构应收账款保理中,参与通谋虚伪之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对抗保理人,实际上就是例外的有关客观上不存在的债权的善意取得规定。[23] 债权仅是相对人间的法律关系,并不指向物理世界中的实物,因此善意取得不存在之债权的法律效果可以理解为直接在双方间创设出债务关系。[24] 股权是组织法上的相对权,同样可以作此理解,受让人的善意取得可以使其与公司间直接产生股权关系。比较法上,虽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6条第3款仅允许既存股权之善意取得,但学说多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此种立法将使减轻受让人查询负担的政策目标大打折扣,每一次股权变动中,买受人都将不得不调查以确保股权最初曾被有效创设。[25] 因此,股权受让人应当可以受到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
其次,对于股东的一般债权人而言,其对债务人名下享有股权这一责任财产的信赖不值得受到保护。王泽鉴先生早已指出,一般人之责任财产变动不居,信赖某人始终保持特定数额的责任财产,显然过于盲目。[26] 该观点后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6条所采。[27] 不同观点认为,保护一般债权人,有助于减少他们缔结交易时的信息验证成本。[28] 但本文认为,这应属对一般债权人的行为理性预估不足。实际上,即便将信赖保护延伸至一般债权人,其也并不会因此放弃调查,调查的范围和负担不会有任何减轻。例如,甲经瑕疵增资加入某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即便拟制增资行为相对于甲之一般债权人为有效,允许其可执行甲名下错误登记的股权,但由于该股权嗣后可能发生处分或被其他一般债权人抢先执行,理性的一般债权人仍有必要对甲的资信状况作调查,不会仅根据甲名下存在登记即放弃调查。[29] 仅在例外情况下,若公司和其他股东对增资无效和错误外观具有故意程度的高度可归责性,或许可以正当化不甚合理的对一般债权人的信赖保护,[30] 此时可以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认为,错误的股权登记不得对抗股东的一般债权人,即其有权执行尚登记在增资股东名下的股权(因同为登记对抗主义,还可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54条第3项)。在本文开头所列案例2的情形中,即便认为中科建公司的一般债权人值得受到保护,有权执行登记中的股权,法院也不应认定增资有效,而是应当在个案中审查特定债权人是否为善意、信赖保护需要有多强烈。因此,鑫控集团有关增资无效的请求仍可得到支持,只是该无效不得对抗特定的适格第三人。
最后,公司的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的处理类似。若公司以股东实缴的财产为债权人设定他物权,则增资行为无效后,公司债权人可以受到善意取得制度保护。而公司的一般债权人原则上不应受到保护,因为资合公司的股东享有有限责任,几乎不会与公司债权人发生关系,公司的股东登记对其并无意义,重要的仅是公司本身的财产基础是否充实。[31] 不过,我国判例学说大多认为需要对此种债权人施与一定保护,[32] 由于出资数额、实缴期限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对外公示,出资请求权同样构成公司现有的责任财产,债权人完全可能基于登记股东资产充足而缔结交易。本文认为,此种信赖值得保护,相比于前述股东的一般债权人对股权登记的信赖,公司债权人对出资义务公示的信赖更加合理,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规定出资义务并不会随股权让与而消灭,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对比之下,股权嗣后变动的可能性大得多)。此外,当登记股东的可归责性很高时,令登记股东承担补充责任也更加合理。此时,可以适用《公司法》第32条第3款,错误之增资登记不得对抗公司的一般债权人,后者有权主张瑕疵增资股东被拟制为真正的股东,从而负有出资义务。
2. 公司设立无效
当公司设立行为无效时,公司人格自始不存在,此时可以考虑适用所谓“表见组织”(Scheingesellschaft)理论:在与善意第三人的关系中,组织人格被拟制存在,各类善意第三人从而可以得到相应保护。以公司的一般债权人为例,根据表见组织理论,其可以执行外观看上去属于表见公司的特定财产,[33] 这样,由于该部分财产被拟制归属于表见公司,而不再属于股东,因此可以排除股东个人债权人对该部分财产的执行和破产申请。表见公司的一般债权人的信赖,与前述股东之一般债权人的信赖一样,同样是薄弱的,不过,在后种情形中,需衡量的两方利益主体是“股东之一般债权人”与“公司和其他股东”,前者对责任财产的信赖无法正当化后者的利益减损;而在表见公司情形中,需要衡量的两方是“表见公司的一般债权人”与“股东的其他一般债权人”,由于“一般债权人本来就无法禁止债务人向一个有效的公司出资,因此同样无权禁止债务人向一个表见公司出资”(详见下文)。因此,优先保护表见公司的一般债权人具有正当性。
总结而言,资合组织领域,善意第三人通过股权善意取得、股东登记对抗、表见公司等权利外观理论可以得到保护,未必需要诉诸瑕疵组织理论。
(二) 人合组织领域中的信赖保护
在合伙企业这一典型人合组织中,法律状况基本相同。首先,合伙份额的善意取得尽管未见诸实证法,但在理论上并无障碍,与判例创设股权善意取得时一样,可以《民法典》第65条规定的商事登记之公信力作为制度依据,我国司法实践中也不乏明确承认合伙份额善意取得的判决。[34] 其次,由于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负有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的责任基础乃是合伙人的个人信用,所以企业债权人对合伙人身份的信赖原则上均可得到保护,相关保护工具即为表见合伙人(Scheinmitgliedschaft)制度,拟制负有相关外观之人为合伙人,从而负担连带债务。表见合伙人的思想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35]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76条(有限合伙人表见为普通合伙人)对此亦有体现。[36] 最后,合伙企业设立无效时,表见组织理论在人合组织领域的适用更是毫无障碍,表见合伙实乃表见组织理论的典型案型,例如民事合伙合同的当事人冒充合伙企业对外交易。不过,理论上对表见合伙企业的效果尚存在疑问,有必要对此展开详论。
德国通说认为,表见合伙企业并无诉讼当事人资格,也不具有破产能力,换言之,权利外观理论仅可实现权利减损或债务发生,但无法拟制产生权利能力或主体地位。这一立场遭到了卡纳里斯的猛烈批评,卡氏认为此种观点属于概念法学式的思考,未能根据表见组织理论之目的得出妥当的解决方案;表见组织理论既是信赖保护之工具,就应当根据与信赖保护思想的内在关联程度来决定哪些规范可以得到拟制适用。就消极当事人资格而言,《德国商法典》第124条第1款赋予合伙企业被告资格,正是为了便利债权人诉讼,债权人可以仅起诉合伙企业本身,并以针对合伙企业的胜诉判决执行相关财产。若不赋予表见合伙企业被告资格,那么债权人只能根据表见合伙人制度请求所有成员承担连带责任,这需要分别提起诉讼,管辖法院可能各不相同,且执行相关财产也需取得针对所有成员的胜诉判决(《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36条),这将极大增加债权人负担。因此要使债权人的信赖保护真正得到有效贯彻,就必须承认表见合伙企业的消极当事人资格。更进一步,根据诉讼法上的武器平等原则(Grundsatz der Waffengleichheit),应同时赋予表见合伙企业积极当事人资格,至少应容许其提起反诉。[37]
我国法下,合伙企业责任和合伙人责任在程序法上同样存在一定区别,不承认表见合伙企业的当事人资格,也会增加债权人的负担。若表见合伙企业无法成为被告,那么债权人只能根据表见合伙人制度主张所有成员承担连带责任,按照近来有力学说关于连带责任应为普通共同诉讼的主张,[38] 当被告不同意合并诉讼时,债权人也需要分别提起诉讼,甚为麻烦。[39]
除诉讼程序外,赋予表见合伙企业主体资格,在执行和破产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拟制出表见合伙企业的主体地位,使得对其提起执行程序或适用独立的破产程序成为可能,这可以将表见合伙人的个人债权人排除在外,斩断他们对表见企业财产的掴取力。这并无任何不平之处,反而更为妥当,理由在于,“债权人本来就无法阻止债务人向一个有效的合伙企业出资转移财产,因此其同样无权阻止债务人向一个表见合伙企业转移财产,表见状态下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不应比有效状态下更高”[40]。
本文认为,肯定表见合伙企业主体地位的立场值得赞同。组织法的独特功能在于构建具有独立性的组织财产,[41] 通过赋予组织区别于成员的主体地位,组织债权人在交易时可以只关心组织本身的财产和经营状况,无须担心成员个人债权人前来执行组织财产,这才使组织债权人有效率地评估风险和分散投资成为可能。[42] 要实现这样的效果,维持债权人与组织的交易安全,就必须使表见状态下债权人的地位被拟制与组织有效成立时的地位相当,切断成员债权人对表见组织财产的执行力。从成员债权人一端观察,组织设立无效之原因,往往并非要保护他们,令组织财产回复到各成员名下,所有债权人一起平等受偿,反倒超出无效规范之意旨,于成员债权人而言构成意外之财(Windfall)。因此,应肯定表见组织具有主体地位。事实上,这正是表见合伙企业理论与表见合伙人理论区分的意义所在:前者是对组织主体地位方面(所谓“积极防御”)的拟制,后者是对成员连带责任(所谓“消极防御”)方面的拟制。
总结而言,在本文开头所列案例3等人合组织领域,善意第三人可以通过合伙份额善意取得、表见合伙人、表见合伙企业等权利外观理论得到保护,未必需要诉诸瑕疵组织理论。
(三) 两种理论的优劣比较
瑕疵组织理论通过排除法律行为效力瑕疵规则在组织法上的适用,权利外观理论通过拟制信赖内容为真,都可以同等地实现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但比较之下,两种理论在以下情形仍然存在重要不同:
其一,恶意第三人。权利外观理论性质上仍然是一种相对的信赖保护(relativer Vertrauensschutz),仅在与善意第三人的关系中才拟制信赖为真;而瑕疵组织理论是一种绝对的交易安全保护(absoluter Verkehrsschutz),并不区分善恶意。[43] 初看之下,瑕疵组织理论一并保护恶意第三人,似属过度,不过,忽略第三人之善恶意可能正是更高强度的信赖保护所必需。由于第三人主观状态往往需要个案事后认定,这就导致当事人有动力尽力搜集各种证据,尝试争讼第三人为恶意,此种调查成本和诉累对各方都是一种负担,第三人即便确信自己为善意,也需预想将来或有他人质疑自己为恶意。不要求第三人具体信赖之存在,可自始杜绝一切针对第三人主观状态的争讼,增强了第三人的交易信心。[44] 以相对信赖保护和绝对交易保护为两端,形成了程度渐变的信赖保护谱系。[45] 某种情形应当处于该谱系中的何处,取决于法律想要对第三人给予多大程度的保护。
其二,效力瑕疵面向未来的影响。权利外观理论的相对信赖保护属性决定了其需满足第三人有所处分或投资(Disposition oder Investition)的要件。善意第三人处分的利益越重大、处分过去的时间越久、事物发展越不可逆,其信赖就越值得保护。极端情况中,甚至可以完全排除效力瑕疵事由的一切影响,当事人不得请求缔结回复性的法律行为。而根据瑕疵组织理论,瑕疵事由仍会构成公司解散或减资事由,这可能会导致救济不足。[46]
其三,一般债权人。权利外观理论还要求第三人之信赖与信赖处分间具有因果关系。据此,在加入普通合伙企业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时,根据瑕疵组织理论,入伙仍为有效,该投资人须经退伙程序才可退出,投资人必须对入伙前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7] 而按照权利外观理论,企业债权人作出信赖处分(缔结负担行为)时,信赖外观(投资人登记为合伙人)尚不存在,不应得到保护。[48] 对比之下,债权人在计算与合伙企业交易的风险时,只会考虑合伙企业现有合伙人的状况,未来是否会有新的投资人入伙、新合伙人有多少财产都是高度不确定的,理性之人不应对此有所信赖。在意思瑕疵之投资人与并无任何信赖值得保护的老债权人之间,瑕疵组织理论竟然选择优先保护后者,属实难谓公平。基于相似道理,瑕疵组织理论对侵权债权人的保护也属不当。
其四,权利外观理论具有“动态体系”(bewegliches System)的特点,要件认定具有强弱分别,可以相互补强;而在瑕疵社团理论中,各要件的认定只能“全有或全无”,即便是具有衡平性质的“不存在更优位的利益值得保护”这一要件,也只关注到了瑕疵事由的种类,而无法涵盖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强度、组织成员的可归责程度等因素。德国司法实践中也是整齐划一地适用瑕疵社团理论,哪怕效力瑕疵事由被发现时才过去一周的时间,也会一律排除无效。但从个案正义的角度看,很难理解第三人在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利益值得保护。[49]
总体而言,瑕疵组织理论追求一种更高强度的绝对交易安全保护,通过忽略第三人的具体信赖事实,来避免任何争讼可能性;相较之下,权利外观理论比瑕疵社团理论更加灵活,更加注重个案正义。商事交易固然需要一定的确定性,但《民法典》第65条确立的商事登记公信力体现出的基准仍然是相对的信赖保护,对于组织交易必然涉及的代表权限问题,法律尚且要求第三人之善意,在该价值判断面前,瑕疵组织理论的保护范围显然过广。在组织外部关系中,应当采用权利外观理论等相对信赖保护原理,以更好地实现个案正义和交易安全的平衡保护。
(四) 基于资本维持原则的区分适用?
卡纳里斯反对德国通说整齐划一地适用瑕疵组织理论,而认为应当区分资合组织和人合组织处理:在资合组织中,应当适用瑕疵组织理论;而在人合组织中,则应当适用权利外观理论。区分适用的理由在于:资合组织法领域奉行资本维持原则,“组织的责任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得到维持”,这一原则构成法律行为效力瑕疵规则的特别法;而在人合组织中,成员负无限责任,并不要求资本维持,因而溯及无效+权利外观理论已足。[50]
本文认为,卡纳里斯的观点并不可取。一方面,如前所述,公司经营变动不居,一般债权人对公司登记中的注册资本额原则上不值得保护。另一方面,资本维持原则旨在控制公司财产不正当地流向股东,而当组织行为原本无效时,投资人恰恰并非公司之股东(加入公司时),或者针对增资部分而言投资人并非公司股东(增资时),此时公司财产向投资人的流动属于公司对债权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而非股东抽逃出资。认为公司的责任财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持,是过于极端的,例如某人被强按着手在增资认缴协议上签字并完成了工商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8条的价值判断,不能要求其承担出资义务。同理,当存在欺诈胁迫等意思瑕疵时,也不应以资本维持为由禁止投资人请求公司返还投资款。

内部关系:清算困难与经营风险分配
如上文介绍,德国早期判例仅在组织外部关系中适用瑕疵社团理论,认为该理论的正当性在于交易安全保护,这实际上与权利外观理论区分不大。但自帝国法院的相关奠基性判例之后,德国通说转向认为,组织内部关系也有适用瑕疵社团理论的必要,其中的正当性被概括为“组织存续保护”(Bestandsschutz der Gesellschaft),具体的论证包括清算困难、风险共同体、投资者平等保护等不同面向。下文将结合我国实践对这些理由展开检讨。
(一)克服清算困难:向内部关系扩展
1. 瑕疵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
瑕疵组织理论在组织内部关系中的适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其中被反复提及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论证是,如果认定组织行为溯及无效,将导致严重的财产清算困难。
1897年德国新《商法典》首次规定了股份公司设立无效之诉,[51] 彼时,立法者仍然坚持具有溯及力的“无效”概念:“无效这一瑕疵的本质(Natur)决定了,瑕疵股份公司在法律上并不存在,股东得随时主张无效”,无效判决在性质上属于确认判决。[52] 根本变革出现在1935年。在奠基性的判决RGZ 148, 225中,帝国法院提出:“被告合作社在28年的时间中聚集了财产,制作年报有年,注册资本变动不居。特别是已缴纳的出资不应作为非债清偿处理,否则会产生‘严重的困难’。”据此,帝国法院得出结论,在无效宣告之前,合作社在内部关系中也是有效存在的,无效判决在性质上应属形成判决。
在人合组织领域,德国通说也经历了相似的向内部关系拓展的历程。帝国法院一开始秉持无效溯及+权利外观理论立场。[53] 直到1940年的奠基性判例(RGZ 165, 193 ff.),帝国法院才开始有意识地参照资合组织领域内的1935年判决。作为类推依据,法院指出,尽管合伙企业不像公司那样具有法人资格,但它们都具有独立的财产,正是独立财产之存在导致了相同的清算困难:“按照不当得利法来清算已经事实上拥有生命的合伙企业,会带来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导致严重的法律混乱以及非常不公平的结果。”
总结来看,德国判例提出的“清算困难”可以分解为两点理由:其一,清算之事实困难;其二,清算之不公平。[54] 下文将分别依据这两条线索展开检讨。
2. 清算之事实困难:设立无效时的财产归属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证明或审计困难不应成为瑕疵组织理论的正当性。原告的诉讼请求必须具体明确,因此其请求确认组织行为无效时,必须指明具体的行为,而不能笼统地称“公司设立或某个时点后的所有行为”。此项证明有时确实较为困难,不过,问题之解决应当通过程序法给予当事人帮助,而非在实体法上提出某种理论彻底禁止原告争辩过往行为无效。特别是当原告能够一一证明出资、分红等行为存在时,法院更无理由拒绝对此加以审查。必要时,法院还可进行司法审计,复杂程度未必比一些商事交易更大。因此,所谓事实上的清算困难,指的应当是现有清算规则无法适用所带来的困难,不应包括清算规则适用本身无问题,只是实际计算较为麻烦。
德国学者卡斯滕·舍费尔(Carsten Schäfer)教授指出,在真正的清算困难中,最突出的困难是组织设立无效时“主体资格消灭导致组织财产归属不明的问题(Zuordnungsprobleme)”。组织关系相比于其他继续性关系最大的不同在于,认定组织设立行为无效后,主体资格的溯及消灭将导致一切组织关系均不成立。[55]
就成员出资而言,实缴出资行为不成立后,出资财产仍归属于成员,在实物出资情形下,成员得请求更正相关登记、其他成员返还占有;在金钱出资情形下,成员一般将资金汇入组织的银行账户,各成员的出资相互混合,根据添附法理,因不存在主从关系,此时宜按实缴比例认定为所有成员按份共有。在此范围内尚不存在严重的清算困难。
不过,由于组织外部交易因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而被视为有效,组织从第三人处取得之财产、赚取之利润等,仍会留存在组织中,此时会产生特别的难题。当组织以出资财产交换第三人之财产(如购买原材料)时,如果认为此类交易代位物(commodum ex negotiatione)亦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61条物上代位规则,那么或许可以认定这些代位物归属于原出资之成员。但困难在于,很多时候无法将组织支出的财产与特定成员的出资一一对应,例如5个股东每人出资2万元,公司用其中4万元购买机器一套,很难认定该机器究竟对应哪两个股东的出资。此外,如果认为交易代位物无法为第461条涵盖,那么从第三人处取得之财产更将处于无主体资格依附的悬空之中。这一问题在利润归属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由于我国通说原则上不认可获利返还,[56] 组织经营所获利润既不得返还给提供出资财产之成员,也不得返还给执行组织事务之成员,利润飘浮于空中,无所依归。亏损同样会成为问题,若剩余财产不足以覆盖所有成员的返还请求,调减哪些成员的返还数额也会是棘手的问题。[57]
本文认为,针对此类困难,可以将无主体归属的财产一律认定为所有成员按份共有。舍费尔教授反对按份共有方案,认为由于缺少产生按份共有的事实(Entstehungstatbestand),很难理解这些财产如何经法定或约定成为成员共有。[58] 但相较之下,瑕疵组织理论其实同样是一种特殊规定,无论是排除无效之溯及力,还是将财产归属认定为成员共有,都属于偏离一般法理的特别规则,因此共有方案应不会面临比瑕疵组织方案更大的障碍。[59]
至于共有份额的确定,当组织经营存在利润时,本文认为应适用以下公式:成员共有份额比例 = (该成员实缴出资数额 + 利润数额 × 该成员对利润的贡献比例)÷ 组织财产总额,其中“对利润的贡献比例”应根据各成员投入公司之生产要素对利润的贡献力大小确定。[60] 例如,某瑕疵设立的有限公司有股东甲乙丙3人,约定各出资3万元,丙负责公司经营,约定利润分配比例为3∶3∶4;甲实缴出资3万元,乙实缴1万元,丙尚未实缴;公司取得净利润2万元。按照共有方案,三人对公司利润的实际贡献力大小为3∶1∶X(丙的经营贡献只能酌定),应分得财产:3+2×[3÷(4+X)]、2×[1÷(4+X)]、2×[X÷(4+X)]。按照瑕疵组织方案,适用解散程序,三人应按约定利润分配比例分配剩余财产[61]:3+2×30%、1+2×30%、2×40%。两种方案的区别在于,约定之利润分配比例是否仍应得到遵守。瑕疵组织理论排除了组织行为的无效性,进而须遵守该约定,但很难理解的是,既然该约定存在效力瑕疵,以之作为分配之标准又有何正当性可言?相较之下,认定行为溯及无效,并灵活地根据实际贡献度确定分配比例,似乎更加合理。
当组织经营失败出现亏损时,共有份额的确定应仔细衡量经营风险如何分配。以本文开头所列案例1为例,杨立鑫、阮奇恩、郑定银三人发起设立中欣公司,约定出资比例为500万、400万、100万,杨负责经营公司,后杨发现阮恶意隐瞒了法国籍身份,法院支持了杨撤销公司设立行为的请求(撤销的前提是郑知道或应当知道阮欺诈杨[62])。假设中欣公司发生亏损,剩余财产800万元,且阮已破产。按瑕疵组织理论,杨只能请求解散公司,分得剩余财产400万元,阮、郑各分得320万、80万,杨所受100万元损失可依侵权法请求欺诈人阮赔偿,但因阮已破产,最终杨能取回的全部出资仅为400万元。本文认为此种分配方案极不合理,杨系受欺诈而参与设立公司,法律行为一般规则赋予其撤销权,正意味着其应当可以从股东身份所蕴含的公司经营风险中脱身。瑕疵组织理论令杨承担100万元的亏损,实际上是将本属于杨的财产分配给了阮、阮的破产债权人、郑,在欺诈人/恶意第三人与受欺诈人之间,瑕疵组织理论竟然选择保护前者,显然是严重的利益失衡。在共有方案下,合理的份额比例应当是:杨应当可以取回全部的出资500万元;在阮和郑的关系中,并不存在意思瑕疵,应按照约定分配比例,二人各可分得240万、60万。
总而言之,组织设立行为存在效力瑕疵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各成员间分配组织经营的利润和风险。上文提出的共有份额认定标准,或许可进一步细化和修正;不过,瑕疵组织理论一律以组织行为有效时的约定比例安排分配,显然过于僵化。
3. 清算之不公平:增资无效时的利润返还问题
主体资格消灭导致的财产归属问题仅存在于组织设立行为,对于本文开头所列案例2中的增资等组织结构后续变动行为,组织人格不受效力瑕疵影响,按照所有物返还或不当得利规则要求组织向成员返还增资财产,并不存在任何事实上之困难。此时德国学说从其他角度对瑕疵组织理论的正当性提出了论证。
拉伦茨提出,“不当得利法的出发点是一方当事人‘以另一方当事人为代价’而得利,合伙合同(等共同行为)并非双务合同,各合伙人的出资并非互相给付,而是共同向合伙财产所为之给付”,因此,以双方法律行为为原型的不当得利法未能兼顾共同行为之特殊性,就此存在法律漏洞,瑕疵组织理论追求的按照合伙合同有效时的分配比例进行分配,正是一种合适的漏洞填补方法。[63]
以公司增资无效为例,若增资认缴协议及物权变动无效,在实物出资情形下,投资人得向公司主张所有物返还(实物被处分后可主张交易对价之不当得利返还),在金钱出资情形下,投资人通常仅得向公司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若公司出现亏损,由于投资人的地位乃所有权人或不当得利债权人,不负担公司经营风险,公司应全额返还增资款,并无任何不平。但当公司取得利润时,则将出现难题。由于我国通说不承认获利返还,公司仅有义务向投资人返还增资款之本息,而无须分配利润。但如此处理,意味着公司可以无代价地利用他人财产获利,确实不甚公平。
不过,问题的解决也许并不必须借助瑕疵组织理论,而是可以在不当得利法内部进行变通。事实上,德国即存在有力学说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应一般性地包括获利,因为按照权益归属原理,使用物获取利润乃所有权之典型权能,不当得利债务人有义务返还所有权时,也应当返还由所有权之权能内容派生出的其他利益;当然,如果可以认定获利来源于得利人自身的特殊知识或才能时,则其并不派生于所有权,此时无须返还。[64] 按此推论,若获利之产生既有得利人方面的特殊才能运用,也与受损害人财产密不可分,则应衡酌各自贡献力大小在双方间合理分配利润。在公司增资情形中,投资人的增资款对于公司扩大生产是十分关键的,但公司经营也与执行公司事务一方股东的信息和商业能力挂钩,因此双方都与利润的产生存在因果关系,应根据原因力大小合理分配。
事实上,这一点在我国司法实务中或许早已不是问题。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3条规定,待返还之实物出现增值时,法院应“综合考虑市场因素、受让人的经营或者添附等行为与财产增值之间的关联性,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来源于“市场因素”(如市场波动)的增值毫无疑问应当归属于财产权人,来源于“受让人经营行为”的特殊才能增值则应归属于其自身,因此,法院应按二者“关联性”的比例合理分配,这一思路与德国有力说之立场可谓异曲同工。[65] 在实质功能上,瑕疵组织理论可以弥补禁止获利返还式的不当得利规则的缺陷;而如果能认识到此种功能关联,直面问题所在,直接对不当得利法的通说立场进行修正,更能实现问题的妥当处理。
总而言之,经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无论是组织设立瑕疵时财产归属不明、无清算规则可供适用的问题,还是组织增资瑕疵时适用传统不当得利规则不公平的问题,均可通过灵活认定按份共有份额、允许请求不当得利获利返还解决;两种清算困难都不足以成为支撑起瑕疵组织理论的正当理由。
(二) 风险共同体思想:向非组织性合同扩展
传统上,瑕疵组织理论的适用被限制于具有独立财产的组织或具有组织性的合同关系之中。[66] 这一限制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通说举出的正当性是为了克服财产清算困难,而只有具有独立财产的组织才存在财产清算困难。不过,自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70年的经典判例BGHZ 55, 5开始,瑕疵组织理论也被扩张适用至无独立财产的非组织性合同关系中,典型者如隐名合伙,隐名合伙中的财产纯粹系显名合伙人之个人财产,[67] 隐名合伙人对显名合伙人之合同债权,与其他继续性关系如借贷并无本质区别。为此,德国判例提出了相对于财产清算困难独立的其他理由。
联邦最高法院1970年判例提出的新理由是,隐名合伙的合伙人之间构成事实上得到履行的“风险共同体”,合伙人不得借助主张合伙合同无效而向其他共同体成员转嫁风险:“在经济衰退时,将经营风险完全分配给执行合伙事务的显名合伙人承担,将导致严重的不公平;在经济上行时,将建立在隐名合伙人出资基础上的经营成果完全分配给显名合伙人,而只赋予隐名合伙人一项数额低得多的不当得利请求权,这也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此,隐名合伙也如同组织形式一样,值得受到组织存续的保护。”判例提出的这一论证为德国通说接纳,成为支持瑕疵组织理论向非组织性的合同行为扩展的一大理由。
不过,德国学界对此也不乏反对声音。弗卢梅认为,组织人格之存续、成员与组织间关系、成员之间的关系,应当区分对待,特别是在成员相互关系中,应根据个案事实衡量存续保护必要性与效力瑕疵规范之目的,确定是否适用瑕疵组织理论。例如在受欺诈加入隐名合伙的案件中,欺诈撤销规则正旨在让受欺诈人从欺诈行为的不利后果中解脱出来,因此投资人以欺诈撤销为由将“经济衰退时的经营风险推卸给显名合伙人”恰恰是他的权利,最高法院认为这不公平,显然理据不足。[68]
本文认为弗卢梅的观点值得赞同,风险共同体思想不足以支撑瑕疵组织理论的一般性适用,而应只是一个参考因素而已。风险共同体思想的适用前提应当是,投资人愿意参与构筑分担风险的共同体,而当其意思表示存在严重的效力瑕疵时,向其分配风险恰已失去正当性。只有在本文开头所列案例4(隐名合伙)中,张光明所发生的意思瑕疵系重大误解,此时特别禁止其转嫁投资风险,认为其与欧长生处于一个事实上履行中的风险共同体中,才具有正当性。因此,经营风险分配应当具有个案性,需结合具体意思瑕疵类型认定,不应一般性地认为意思瑕疵之成员即应绝对地承担风险。
(三) 投资者平等原则:向基金合同扩展
在基金合同领域内,德国判例还为瑕疵组织理论的适用提出了另一项基于投资者平等原则的论证。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2008年的判决NZG 2008, 460中,投资人在家中缔结了一份入伙合同,加入某封闭型不动产投资基金;后由于亏损,管理人对该基金进行了清算,并要求该投资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德国民法典》第739条);该投资人主张行使消费者撤回权,撤回自己的入伙意思表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本案中的投资人有权撤回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撤回的效果为消费者被免除一切合同所生之债务,这样就产生了“有溯及力的撤回权”和“旨在斩断溯及力的瑕疵组织理论”之间的冲突。由于涉及欧盟《上门交易撤回指令》(85/577/EWG),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遂将该案移送欧洲法院进行解释。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移送决定中认为,应优先适用瑕疵组织理论,否则的话,“投资者就将被置于‘猎犬赛跑’(Windhundrennen)的境地,谁的动作更快,谁就可以取回所有本金,将不利后果转嫁给其他投资者。当合伙财产因履行对某一投资者的返还之债而陷入破产时,对其他在赛跑中落后的投资者将尤其不利。这与组织法上平等对待所有成员的原则不合”。[69]
欧洲法院对此表示了肯定,并指出“消费者保护不是绝对的”,“消费者撤回权规则应当根据民法的一般原则尽力实现公平的风险分配,特别是,消费者不应通过撤回权来推卸投资活动中固有的风险”。[70] 有学者甚至上升到了保护投资自由的高度,认为投资者根据经营态势投机性地选择撤回,会导致“其他投资者无法估算自己的投资将如何发展”,从而打击人们参与此种形式投资活动的积极性,构成对投资自由的限制,有违《欧盟条约》第56条第1款规定的投资和支付自由限制禁止;此外,其他投资者也很可能享有撤回权,适用瑕疵组织理论、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反而能最大化地落实全体消费者的撤回权。[71]
在我国实证法上,尽管并不存在金融消费者撤回权的法律规定,但经由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定,“投资冷静期+回访确认+解除权”的安排实际上在各类私募基金合同中极为常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中基协发〔2016〕7号)第29—30条规定,各类私募基金合同应约定,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签署完毕且交纳投资款后有不少于24小时的投资冷静期;投资冷静期满后,募集机构应当进行回访确认;投资者在回访确认成功前有权解除合同,解除的效果为募集机构应退还全部认购款项。
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这一安排实际上发挥了与消费者撤回权相同的功能,由此也诞生出了相同的理论难题:在本文开头所列案例5的此类纠纷中,投资者在投资的数年后眼见基金爆雷而主张解除,试图以此转嫁投资风险,已经不符合反悔权的初衷,[72] 不过由于很多募集机构操作不规范,并未回访确认,导致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也未起算,这就给法院如何论证驳回投资者请求带来了难题。[73] 有的法院简单依据合同文义支持单个投资者的请求,[74] 更是没有考虑到此种裁判对私募基金行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猎犬竞赛”中手慢的投资者将单独承受全部损失,必定影响公众未来对此类投资活动的信心。更加合理的处理方法应是,借鉴前述欧盟法院立场,对此类纠纷适用或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78条,投资者仅能请求按比例分配剩余财产。
总结而言,投资者平等原则或保障投资自由尽管可以证成瑕疵组织理论,但存在限度。按约定比例分配剩余财产的处理仅限于地位平等、均享有撤回权的无辜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若其他投资者不享有撤回权/解除权,再在他们的关系中平等分配投资风险,就欠缺合理性了,此时应当优先保护享有撤回权的投资者。[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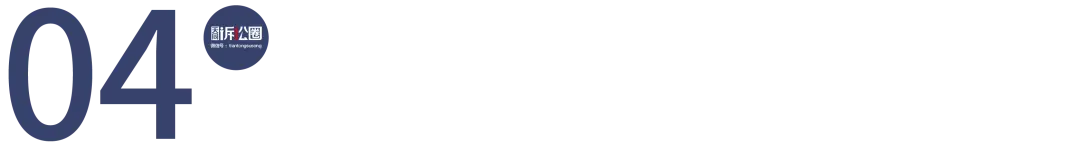
结论
我国多数观点基于善意第三人保护、清算困难、组织关系安定性等,主张排除组织行为效力瑕疵的溯及力,这已十分接近比较法上的瑕疵组织理论,但该观点的正当性存在疑问。在组织外部关系中,各种权利外观理论已足够保护善意第三人之信赖,瑕疵组织理论一律排除无效性,反而会不当保护到恶意第三人、一般债权人,不如权利外观理论灵活,也与我国实证法的评价基准存在矛盾。资本维持原则也无法正当化瑕疵组织理论对第三人的过度保护。
在内部关系中,证明困难并非拒绝溯及清算的正当理由。当组织设立无效时,可以通过认定财产为成员按份共有解决因组织丧失主体资格而无规则可适用的事实上之清算困难;经营存在利润时,共有份额应按实缴出资比例确定;经营出现亏损时,份额之确定,应根据意思瑕疵规则之意旨,判定经营风险应由何方成员承受。当组织增资无效时,可以对不当得利法上的获利返还采按贡献度大小分配的立场,由此可以解决溯及清算不公平的问题。
清算困难不是拒绝对意思表示瑕疵之成员提供充分救济的正当理由。成员内部关系本质上涉及如何分配组织经营风险的问题,组织行为溯及无效,意味着意思瑕疵之成员可以取回全部出资,将经营风险分配给其他成员,此种做法在受欺诈、胁迫等场合具有正当性;在错误或消费者撤回权等场合,则可能对其他不可归责之成员造成过重负担,诱发无效率的“猎犬竞赛”等公地悲剧,此时成员平等原则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应仅允许按约定比例分配剩余财产。无论如何,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意思表示瑕疵救济和成员平等原则等多种目标的务实协调(praktische Konkordanz),一律排除效力瑕疵溯及力的做法过于僵硬。
瑕疵组织理论作为瑕疵继续性关系理论在组织法场景下的具体化,引发了对瑕疵继续性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反思。本文的讨论表明,涉及主体资格的组织关系尚且可以克服清算困难问题,其他继续性关系中的无效溯及排除的处理似乎更无理由偏离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
注释:
[1]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四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133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终4252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民终368号民事判决书。
[5]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浙民再79号民事判决书。
[6] 案例4和案例5涉及的并非组织法行为,但如下文所述,相关原理(瑕疵组织理论)亦可类推适用于这些情形中,因此本文也将它们一并列入。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922号民事裁定书。
[8]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四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贺小荣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会议纪要》,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10]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商初字第255号民事判决书。
[11] 主张一律排除溯及力的观点,参见殷秋实:《法律行为视角下的决议不成立》,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第167页;许中缘:《论意思表示瑕疵的共同法律行为———以社团决议撤销为研究视角》,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第62页。主张在组织外部关系中排除无效溯及力的观点,参见徐银波:《法人依瑕疵决议所为行为之效力》,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56、160、167页。
[12] 支持适用信赖保护的“民法范式”的观点,参见李建伟:《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类型及其救济体系再构建——以股东大会决议可撤销为中心》,载《商事法论集》2008年第2卷,第90页。
[13] 参见丁勇:《公司决议瑕疵立法的范式转换与体系重构》,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83—88、92—93页。
[14] Vgl. BGHZ 63, 345 f.
[15] Vgl. Schmidt, Gesellschaftsrecht, 4. Aufl., 2002, S. 141.
[16] Vgl. Fleischer & Thoma, Fehlerhafte Personengesellschaft und Scheingesellschaft: Eine rechtsvergleichende Gegenlese, FS Canaris zum 80. Geburtstag, 2017, S. 841 ff.
[17] 参见[美]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第5版),齐东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James D. Cox & Thomas Lee Hazen, Treaties on Law of Corporations, Vol. 1, 3rd ed., Thomson Reuters, 2021, § 6.
[18] 德国的瑕疵组织理论正是从旧《商法典》规定的对资合公司设立无效的限制出发,逐步一般化得出的理论建构。
[19] 参见王泽鉴:《事实上之契约关系》,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7页;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9页。
[20] Vgl. Oechsler, Die Geschichte der Lehre von der fehlerhaften Gesellschaft und ihre Stellung im europischen Gesellschaftsrecht, NJW 2008, 2472 f. 我国法院也有相似观点,参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02)沪高民三(商)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
[21] Vgl. Schmidt,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4. Aufl., 2016, § 105 Rn. 232.
[22] 当其他股东放弃增资优先认缴权之表示受到增资无效的影响时,股权善意取得的构成以其他股东的可归责性为前提,反之则不需要,因为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将受到稀释。
[23] 同旨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05条。其他例子还包括预告登记之善意取得,例如土地错误登记名义人为恶意买受人设定预告登记,该恶意之人又将买卖债权连同预告登记让与善意第三人,该第三人得以预告登记对抗其他买受人。Vgl. BGH NJW 1957, 1229.
[24] 德国通说持相同观点,参见Roth & Kiening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8. Aufl., 2019, § 405 Rn. 9.
[25] Vgl. Heiding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GmbHG, 4. Aufl., 2022, § 16 Rn. 350, 392; Stefan Klöckner, Praxisprobleme beim gutgläubigen Erwerb von GmbH-Geschäftsanteilen, NZG 2008, 844.
[26] 参见王泽鉴:《“动产担保交易法”上登记之对抗力、公信力与善意取得》,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1页。
[27] 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页。相似立场更见诸公司法领域,公司债权人不应信赖公司始终保持等同于注册资本数额的财产。参见陈甦:《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的学说分析及规范分野》,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第41—54页。德国法和美国法的情况完全相同,参见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1971, S. 168; James D. Cox & Thomas Lee Hazen, Corporations, Vol. 2, 2nd ed., Aspen Publishers, 2003, p. 1105.
[28] 参见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11—14页;庄加园:《动产抵押的登记对抗原理》,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90页;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05页;龙俊:《中国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7—151页。
[29] 基于相同原理,美国著名财产法学者拜尔德(Baird)教授指出,动产担保的声明登记制度仅对担保权人有意义,对一般债权人并无帮助。See Douglas G. Baird, Notice Filing and the Problem of Ostensible Ownership,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3, 12 (1),pp.6061. 相似观点,参见Canaris (Fn. 27), S. 171.
[30] 多数判例认为股权代持中,实际投资人具有故意程度的可归责性,相较之下,名义股东的一般债权人即值得保护。参见张弘毅:《〈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评注(有限公司股东姓名登记的对抗力)》,载《法大研究生》2020年第2辑,第129—132页。
[31] 参见张双根:《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第143—144页。
[32] 参见李建伟、罗锦荣:《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的对抗力研究》,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第155—156页;胡晓静、崔志伟:《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对〈公司法解释(三)〉的解读》,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4期,第38页;范健:《论股东资格认定的判断标准》,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6年第2期,第69页。
[33] 需注意的是,此处要求股东表示某个特定的财产如某不动产属于表见公司,而不能是一般性地宣称表见公司拥有多少数额财产。Vgl. Canaris (Fn. 27), S. 168.
[34] 参见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常民一终字第282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4民终1281号民事判决书。
[35] Vgl. Fleischer & Thoma (Fn. 16), S. 841 ff.
[36] 参见石一峰:《民法典背景下表见合伙人责任的类型与体系》,载《法学》2021年第12期,第105页。
[37] Vgl. Canaris (Fn. 27), S. 169 f.
[38] 参见袁琳:《多数人之债的诉讼构造与程序规则》,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6期,第1547页;任重:《反思民事连带责任的共同诉讼类型——基于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第150—154页。
[39] 不过,与德国通说认为连带债务系普通共同诉讼不同,我国实证法上有多个法条将连带债务规定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0条、第63条、第71条),若认为表见合伙人之间构成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进而债权人可在任一合伙人的住所地提起共同诉讼(《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3款),所有合伙人必须一同应诉,且一致做出诉讼行为,那么这对债权人而言也并不是太大的麻烦。
[40] Vgl. Canaris (Fn. 27), S. 171.
[41] See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The Essential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aw, The Yale Law Journal, 2000, 110 (3), 387-440.
[42] See Richard Squiret, Strategic Liability in the Corporate Group,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11, 78 (2), 612-614.
[43] 德国也有观点认为,瑕疵组织理论并非一律不考虑第三人之善恶意,而是可以根据恶意抗辩(Einrede der Arglist)制度阻止恶意第三人主张瑕疵组织行为有效。Vgl. Flume, Die Personengesellschaft, 1977, S. 19.
[44] 参见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03页;Canaris (Fn. 27), S. 173 ff.
[45] Vgl. Krebs,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HGB, 4. Aufl., 2016, § 15 Rn. 10.
[46] Vgl. Canaris (Fn. 27), S. 450 f.
[47] Vgl. Schmidt (Fn. 15), S. 160..
[48] 如果老债权人在新投资人入伙后,基于对此之信赖而同意延期债务,那么就可以满足信赖责任的各要件,此时投资人应对老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Vgl. Canaris (Fn. 27), S. 511.
[49] Vgl. Canaris (Fn. 27), S. 449.
[50] Vgl. Canaris (Fn. 27), S. 174.
[51] 德国新《商法典》第309条至第311条的规定总体上接近于瑕疵组织理论在公司外部关系适用之结果。
[52] 判例初期也完全遵循了《商法典》的无效具有溯及力的观念,例如帝国法院在1926年的判例RGZ 114, 77中认为,不应否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无效之诉程序外主张无效的可能性。
[53] 如帝国法院1933年的经典判例RGZ 142, 98。
[54] 以上内容参见Schäfer, Die Lehre vom fehlerhaften Verband, 2002, S. 24 f., 63 f.
[55] Vgl. Schäfer (Fn. 54), S. 79 ff.
[56] 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255页;杨代雄主编:《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852页。
[57] 对于不影响财产变动的纯粹组织法上行为,如选举董事或变更利润分配比例(未实际分红时)的决议,直接认定为无效即可。Vgl. Flume (Fn. 43), S. 28.
[58] Vgl. Schäfer (Fn. 54), S. 79 f.
[59] 财产归属难以确定时认定为相关当事人共有,其实不乏例证。例如,英国《货物买卖法》(Sale of Goods Act)第20A条第4款规定,多个买受人向同一出卖人购买一批(bulk)货物中的特定数量,但尚未特定化时,他们按照各自到期且已付款的比例共有这一批货物。
[60] 类似的根据原因力大小确定分配比例的思路,可见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3条。
[61] 注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2条第1款。
[62] 参见马强:《论决议行为适用意思表示瑕疵规则》,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121—122页。
[63]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7. Aufl., 1965, S. 312.
[64] 参见[德]约瑟夫·威灵:《德国不当得利法》(第4版),薛启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65—67、75—76页。
[65] 相似思想,参见吴至诚:《违法无效合同不当得利返还的比例分担:以股权代持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3期,第620页。
[66] 包括公司、合伙企业、合作社、民法典中的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以及外部合伙合同(Auβengesellschaft)等。
[67] 参见[德]怀克、[德]温德比西勒:《德国公司法》(第21版),殷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8、34—35页。
[68] Vgl. Flume (Fn. 43), S. 27 f.
[69] NZG 2008, 463.
[70] EuGH, Urteil vom 15. 4. 2010-C-215/08.
[71] Vgl. Oechsler (Fn. 20), S. 2474 f.
[72] Vgl. Christian Armbrüster, Gesellschaftsrecht und Verbraucherschutz-Zum Widerruf von Fondsbeteiligungen, 2005, S. 26.
[73] 有法院指出,投资者仅根据未回访确认主张解除合同“显失公平”,但无法给出具体论证。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申4737号民事裁定书。
[74] 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终275号民事判决书。
[75] 还存在其他支持瑕疵组织理论的论证,但说服力均不强,此处仅再简要讨论卡纳里斯提及的“合一处理的必要性”(Notwendigkeit einer einheitlichen Lösung)论证。其认为,当合伙合同当事人对部分债权人如实陈述自己为合同关系,而对其他债权人假称自己为合伙企业时,应当对所有债权人统一适用合伙企业的破产程序,否则部分债权人适用合伙合同破产程序、部分债权人适用合伙企业破产程序,将十分复杂;此外,在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形中,“注册资本只能被完整地筹集和维持”。Vgl. Canaris (Fn. 27), S. 171, 174, 451. 不过,本文认为,分开处理并非不可想象,特别是注册资本的情形,认为登记股东仅对公司善意债权人负补充责任,对恶意债权人不负责任,似乎不存在任何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