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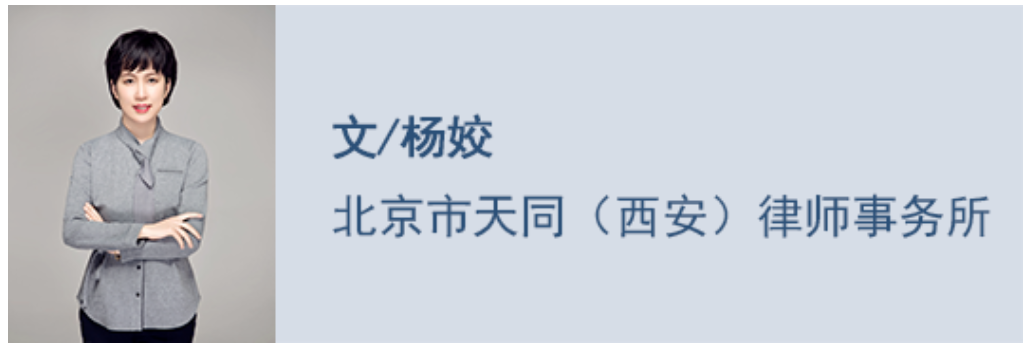
一、问题的提出
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是股东基于作为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享有的一种股权权能。股东投资公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通过分配获得利润是实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途径。我国《公司法》在第4条、第34条、第166条等分别对股东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实践中,因不少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攫取不当利益,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以自己意志取代公司意志,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利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操纵股东会拒绝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或作出不分配利润决定或违法分配的决定,借以排挤和欺压中小股东。出现了许多公司即便存在可分配利润却拒绝分配的情形,极大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引发不少股东与公司间的诉争。
自2017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下称《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规定:原则上,股东请求分配利润应以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为前提,但存在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情形时例外。该司法解释的出台,一方面正如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保护股东权益的一项重大的积极举措,是对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救助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弥补,为中小股东提供区别于解散公司、回购股份等传统救济手段的另一条道路。但另一方面,该但书条款仍较为笼统,指向性并不清晰,射程范围存在含混,尤其对于股东强制盈余分配的适用条件、举证责任、司法后果等诸多问题尚未明确。
为探究该条规定的实践适用,本文以“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为关键词,通过对该解释颁布至今最高院及各地高院的裁判案例进行检索分析,仅有如(2016)最高法民终528号公报案例“庆阳太一热力有限公司、李昕军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等个别适用《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进行强制盈余分配的判例,绝大多数案例仍以“原告股东对该条但书规定的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的情形无法举证”,或其“举证的情形不能被认定为例外情形”而被驳回起诉,使该条司法解释在实践适用中存在被虚化和搁置之虞。
为此,本专题拟分两篇或三篇对该制度的价值目的、准用条件、适用边界、司法效果、举证责任等进行探析,以期明确该条司法解释的旨意与适用,以避免其沦为具文,也为实务工作提供可资参考批评的分析意见。
二、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的制度价值
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权利性质多有争议,一般认为,盈余分配请求权包括两个层面,即抽象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和具体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具体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是指当公司存有可以分红的利润时,根据股东会分红决议而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其持股类别和比例向其支付特定股利金额的权利。抽象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公司股东的地位和资格而享有的一种权利,本质上是期待权,当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形成分红决议时,该抽象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即转化为具体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有德国学者认为盈余分配请求权属于债权,该权利在两个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在公司作出分红决议之前,盈余分配请求权只是一项未来的、数额不确定的债权。而在公司作出决议之后,该权利成为数额确定的到期债权。[1]
基于盈余分配请求权的不同类型,公司法给予的救济措施亦不相同。对于具体盈余分配请求权,因与普通债权并无二致,故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明确的救济途径,股东依法可提起给付之诉。本文所指的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实为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时的一种救济手段,主要是指在缺乏公司分红决议的前提下,由于股东的合法利益遭受严重损害而向人民法院请求对公司利润进行分配的权利。一般认为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是一种消极权利,通常情况下不得个别地、积极地行使该权利。在2017年《公司法解释四》出台前,司法实践中极少支持缺乏分红决议支撑、请求分配利润的判例。而《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的规范表明,在特殊情况下,抽象的盈余分配请求权也并非完全不具有可诉性,否则,只要股东会不对分配利润作出决议,或者作出不分配利润的决议,该期待权就无法转化形成具体的盈余分配请求权,股东在此项权利上就没有任何救济渠道。[2]
实践中,频繁出现的大股东为追求自身利益,利用资本多数决原则进行关联交易、修改公司章程、不进行清算、长期不召开董事会等,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此时赋予股东特殊情形下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就颇为必要,这种必要性体现为:
1.公司正义原则的要求
虽公司自治原则被看作是公司法的重要原则,公司盈余分配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形式之一。根据《公司法》第37条及第46条的规定,董事会负责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是否分配利润、应否提取盈余公积、以何种形式分配、分配比例及分配的具体金额等事项的最终决定权由股东会掌控。换言之,公司利润分配决定权是典型的公司自治和商业判断。
但公司自治并非不受任何管束,也不意味着绝对排除司法权的必要和适度的介入。公司法作为法律,同样需要遵循法律正义的基本价值。也就是说,除了公司自治之外,公司法还应该遵循公司正义原则。
公司正义原则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借鉴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中得到启示。众所周知,合同法是自由的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治是其基本原则。但是,法律并非不干预,在合同自由原则之外,还存在公序良俗原则。更有学者指出,合同正义原则的历史比合同自由原则更为悠久。公司正义原则也存在于公司法的各个角落。[3]
2.股东权益的切实保障
针对股东滥用权利、侵害其他股东收益权的情形,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多种救济措施,分为组织法上的救济措施及契约法上救济措施。组织法上的救济措施主要是指基于《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可通过请求公司回购、转让股份解散公司等方式退出公司。契约法上的救济措施,则主要是指公司自治的范围内,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形式就利润分配事项进行自治,待出现争议时通过仲裁、诉讼等手段进行救济。
对于公司司法解散这一救济方式而言,其结果是公司解散并进入清算程序,对公司原有组织造成毁灭性破坏。为此,《公司法解释一》第一条规定,股东以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在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时,通过解散公司来实现中小股东摆脱公司“锁定的”可能性。在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诉讼实践中,法院多以公司对外经营情况作为裁判时考量的核心因素,而几乎不考虑公司在正常经营状态下,股东受到“严重压制”提起解算公司、寻求救济的情形。同时,相较于解散公司,回购受压制股东的股份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救济方式,但《公司法》赋予股东回购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极为严苛,即要求公司连续五年盈利且连续五年不分红[4],从公司运营实践的角度观察,该条规定极易以公司进行少量象征性分红的形式而被彻底规避适用。[5]
基于现有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退出机制的缺陷,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行使的结果是通过司法介入对公司的盈余进行分配,一方面使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转化为具体的债权;另一方面,该制度不涉及股东资格的变动,对公司组织结构的破坏远远小于司法解散和强制回购,最大程度保持了司法的谦抑性,维护了公司作为一个组织的完整性。
三、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的适用条件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规定,仅在存在股东滥用权利并导致股东损失的情形下,法院才会适用这一制度支持公司进行强制盈余分配。但有关“滥用股东权利”情形如何界定、该制度适用的法律后果等并未有具体的界定。
前述,最高院已在(2016)最高法民终528号“庆阳太一热力公司盈余分配案”中适用了该条规定,该案基本案情为:太一热力公司是一家设立于2006年的有限责任公司,太一工贸公司和居里门业公司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本案一审被告太一热力公司的股东(前者持股比例为60%,后者为40%)。原告主张太一热力公司存在可供分配的利润,但长期不向股东分配,亦未形成任何有关利润分配的决议,后小股东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强制分配公司利润。
最高院主要裁判要旨为,公司在经营中存在可分配的税后利润时,有的股东希望将盈余留作公司经营以期待获取更多收益,有的股东则希望及时分配利润实现投资收益,一般而言,即使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形成盈余分配的决议,对希望分配利润的股东的利益不会发生根本损害,因此,原则上这种冲突的解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是否进行公司盈余分配以及分配多少,应当由股东会作出盈余分配的具体方案。但是,当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者转移公司利润时,则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实体利益,已非公司自治能解决,此时若司法不加以适度干预不能制止权利滥用,亦有违司法正义。
盈余分配义务的给付主体是公司,若公司的应分配资金因被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而不足以现实支付时,不仅直接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到其他股东的利益,利益受损的股东可直接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向滥用股东权利的公司股东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向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
下文将结合相关理论及该案的裁判逻辑对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的的适用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1.强制盈余分配以公司有可供分配利润为前提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66条的规定,公司获取的当年税后利润,不能全部用于分配股利。其需要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后才能进行分配。同时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会有权决定提取一定数额的任意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的数额直接影响股东实际可以获得分配的数额。一方面需要考虑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考虑股东分取适当红利的需要。也就是说,公司的强制盈余分配应以公司有可分配的利润为前提。
事实上,无论是前述最高院公报案例,亦或是相关著作中所提及的国外判例,被告公司的可分配利润数额都较大。值得讨论的是,判断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的时点应以何为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行为发生时,或受压制股东提起诉讼时,或法院作出判决时。我们认为,实践中,股东滥用权利的行为往往呈现隐蔽性、持续性,其行为的开始时间并不易确定,且部分滥用权利行为侵害公司利益所致损失,本也应归入公司可分配的利润总额中。而如以法院作出判决时才确定利润金额,又势必使判项如具体分配金额等存在事实认定的欠缺。因而,出于最大限度保护股东权益和方便裁判的考量,以提起诉讼时确定可分配利润金额较为妥当。
(未完待续……)
注释:
[1]《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梁上上,载于《现代法学》,2015年3月第37卷。
[2]杜万华,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P334,人民法律出版社。
[3]《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梁上上,载于《现代法学》,2015年3月第37卷。
[4]《公司法》第75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的股份收购请求权的具体适用的情形,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1)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的;……”
[5]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价值、要件及司法效果——从《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出发,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巡回观旨”栏目由张小健律师主持。如您对“巡回观旨”栏目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点击文末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