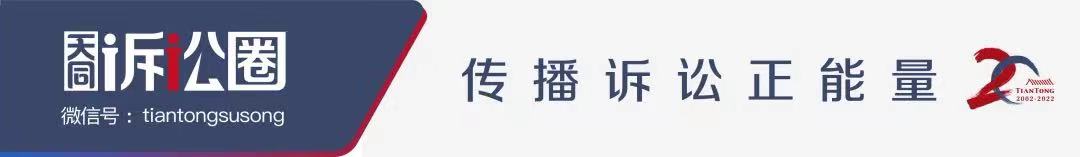
商事 - 担保卷 - 抵押 - 效力 - 流抵契约
1.2
202002/280:11
2018
债务到期前协商处置担保物且对价公允,不属流质
——担保的设立应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前,但如担保物的价值不足以覆盖已知债务,可协商提前清算,以实现担保权利。
标签:| 让与担保 | 流抵契约 | 股权转让 | 以物抵债
案情简介:因项目存在对外债务,原项目方奕公司引入资方兆公司,并与兆公司等方先后签署了四份协议。第一份协议约定,奕公司承诺以其持有的项目公司标的股权作为解决争议及向兆公司融资借款的担保,如未能履行承诺,奕公司可选择付款清偿或以标的股权抵偿。第二份协议约定,奕公司将标的股权以过户的方式抵押给双方合资的第三方公司,但实际所有人及权利人仍是奕公司,用以担保一系列债务。第三、第四份协议约定,部分对外债务已经到期,且明确标的股权已不足以清偿,故奕公司放弃标的股权、由兆公司全权处置,所负债务在一定数额范围内由兆公司等负责偿还,并约定了最终清算后不足或超出部分的处理方式及部分具体债务的处理方式。
法院认为:① 担保权利人并非债权人,且当事人无相关约定,故本案并未设立质权,但在认定双方权利义务时,仍应考量对价是否有失公允、侵害债务人利益。② 四份协议应进行系统考察, 第一份协议中,虽在标的股权之上设立了担保,但其价值、抵偿方式均有待明确;第二份协议明确了标的股权的担保内容、担保方式及满足条件后以市场价值评估为基础的抵偿方式,且明确了股权过户目的并非出让,实质上设立了让与担保且符合公允原则;第三份及第四份协议明确标的股权不足以清偿已知债务,义务人放弃标的股权,各方作为高度理性的商事行为主体约定了具体的标的股权对价及清算规则,属于明确让与担保权利如何实现,并非独立的股权转让约定。③ 仅部分债务到期、并非全部债务到期之前,均可设立让与担保,否则属于债务履行。④ 各方当事人可基于意思自治约定担保物对价,不必然需经过专业机构评估。
实务要点:设立让与担保应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进行,且即使债务履行期尚未届满,如担保物的价值已不足以覆盖已知债务,权利人亦有权行使让与担保权利。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就让与担保标的物价值达成的合意有效,但为防止出现类似于流质、流押之情形,在预见债务数额可变化的情形下,仍应在约定基础上据实结算。
案例索引: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终字第751号“奕公司、侯某某与兆公司、某信息咨询公司、某投资发展公司、第三人某电子科技公司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02/280:11)
核心意见:

兆公司与奕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以公允总价受让项目公司股权,双方合作开发案涉项目。
本案纠纷涉及某科技园升级改造主体的股权转让。兆公司系在项目烂尾的背景下受让项目公司的股权,并且支付了总价(含股权转让款加若干负债投资补偿款),股权转让价格公平合理。

在合作开发阶段,为确保奕公司、原实控人依约解决股权转让之前项目公司既存及或有债务并对项目持续投入,奕公司同意共管项目公司股权作为履约保障,双方签订了《担保协议》,约定股权仍属于奕公司所有,双方需进行清算,不构成流质条款,合法有效。
奕公司负有解除项目公司土地查封、解决债务、偿还兆公司借款(如发生)以及对项目后续投入的合同义务;为确保奕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双方共管奕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实际控制权仍属于奕公司。这一约定具有担保奕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功能,但兆公司并非奕公司的债权人,且股权实际仍在奕公司控制之下,因此该约定不属于典型的让与担保。
《合作协议》及《担保协议》均明确约定如触发抵偿条件,双方均需依据经评估的市场公允价值确认抵偿数额,明确了抵偿情形下的清算责任,不存在未经清算直接发生所有权转移效果、损害债务人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流质条款,符合等价有偿原则,合法有效。

鉴于奕公司、原实控人无力承担合作开发关系中的各项义务,奕公司决定终止合作关系,将项目公司股权以n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兆公司,该n亿是股权转让价款而非让与担保关系项下债权债务的清算,转让价格公平合理。
3.1 《转让协议》签订背景:股权已不足以清偿所约定的债务和保障后续投入
在签订《担保协议》后,因某诉讼导致项目迟迟不能步入正轨,兆公司和奕公司都希望整体转让项目并积极寻找买家,均未能成功。奕公司因受到高利贷的巨大压力,请求兆公司再次受让股权。
另如《转让协议》鉴于部分条款所明确的:“经过对整个项目的市场评估,甲方在项目公司中所享有的权益份额已不足偿还上述债务。”
在此情况下,奕公司、原实控人决定终止合作关系,将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给兆公司,双方由合作开发关系变更为股权转让关系,兆公司成为案涉项目的独立开发主体。
3.2 协议性质上,《转让协议》是奕公司向兆公司转让项目公司股权、兆公司向奕公司支付n亿元转让款的股权转让协议。
《担保协议》约定,奕公司向兆公司“转让其所持项目公司的股权”。据此,双方在《转让协议》项下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兆公司以n亿元为对价,受让奕公司所持项目公司的股权。只是为了防止项目开发受奕公司此前债务的不利影响,因此双方约定n亿元定向用于奕公司清偿五项债务。这一约定,不影响双方仍为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定性。
3.3 协议效力上,奕公司主张《转让协议》是让与担保的延续、因构成流质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3.3.1 奕公司与兆公司间并无债权债务,不存在让与担保法律关系中需要债权人与债务人进行清算的前提条件
如一审判决所认定,《转让协议》所约定定向清偿的五项债务,其债权人都不是兆公司。因此,不存在需要对兆公司与奕公司、原实控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算的问题。奕公司、原实控人主张违反让与担保的强制清算义务,并没有需要清算的前提。
3.3.2 从《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及实际履行可见,奕公司系以股权转让所得n亿元定向清偿五项债务,清偿的后果归属于奕公司,其利益不会因此受损。
n亿是项目公司标的股权的固定转让对价,而非兆公司与奕公司、原实控人之间债权债务结算的结果。奕公司、原实控人的各项债务是否已届清偿期、是否已足额清偿,均需奕公司、原实控人与其债权人另行逐一结算,兆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义务,既不构成债务承接、也并非代为清偿,更未损害任何案外人利益。兆公司、奕公司、原实控人关于“清算责任”与“债务清偿期”的主张,混淆了不同的债权债务关系。
3.3.3 n亿元股权转让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兆公司利用缔约优势地位侵害奕公司、原实控人权益的情况。
本案最核心的争议其实是n亿元的股权转让价格在当时市场条件下是否公平合理:
第一,《转让协议》之前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项目公司当时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m亿元,即标的股权价值为<n亿。且《转让协议》鉴于部分条款已明确“经过对整个项目的市场评估……”。因此奕公司、原实控人称签订《转让协议》前未评估标的股权价值,与事实不符。
第二,《合作协议》约定的y%股权受让价格,是m+亿元(高于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m亿元)。y%股权转让是在案涉标的股权转让的4个月之前,而当时深圳房地产市场持续处于低迷期,因此y%股权转让的价格对于判断案涉股权转让对价是否公允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以此参考,标的股权的价值以n亿的价格转让,公平合理。
第三,奕公司、原实控人早在2015年初即以重大误解、2015年中以胁迫和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转让协议》(后均以撤诉结案),说明奕公司、原实控人明知核心争议在于n亿元的转让价格是否公允,而非“让与担保强制清算义务”。但在奕公司、原实控人2016年中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了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一年除斥期间。
第四,从时间上看,在签订《合作协议》《担保协议》四个月后,各方才签订《转让协议》,不存在债权人利用借款发放时的优势地位,强迫债务人接受不平等的条件,签订不公平协议损害债务人利益的情形。且如《补充协议》在鉴于部分条款所指出的,“履行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确认,更进一步明确了项目公司的股权归属及项目的各项权益的归属”,也可见三份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胁迫”“显失公平”。
3.3.4 即便是在让与担保法律的关系中,在债权债务未届清偿期的情况下,双方协商一致提前结算,也不违反法律规定。
流质条款无效的原因,在于债权人利用发放贷款时的优势地位,强迫债务人接受不平等的条件攫取不当利益,否则不予发放贷款。但如最高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80号【第72号指导案例】、(2016)最高法民申2720号民事裁定所指出的,法律并不禁止在借款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在债务履行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提前结算。因此退而言之,即便兆公司与奕公司在本案中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即便《担保协议》构成让与担保,双方在四个月后再约定抵债价格,即便此时债务履行期限未届满,亦应合法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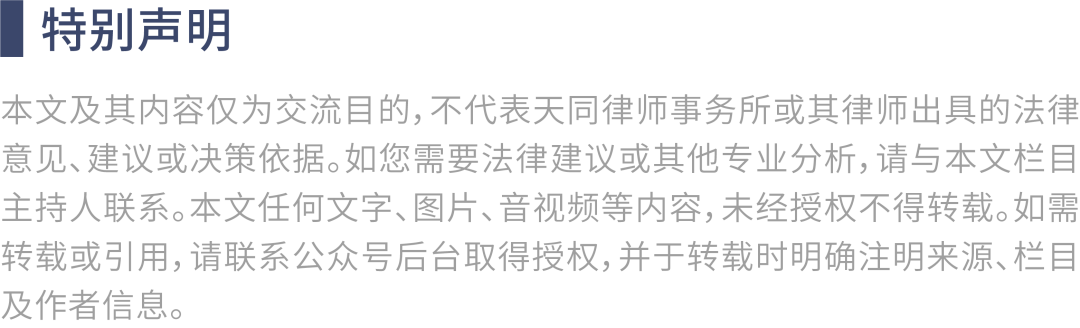
“天同码”栏目由陈昱竹律师主持,秉持天同的“开放、创新”精神,邀请同行共建。栏目主要分享典型案例,进一步关注并分享法治建设、法律科技、知识管理、数据合规等前沿问题。如您有意加入共建、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或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点击文末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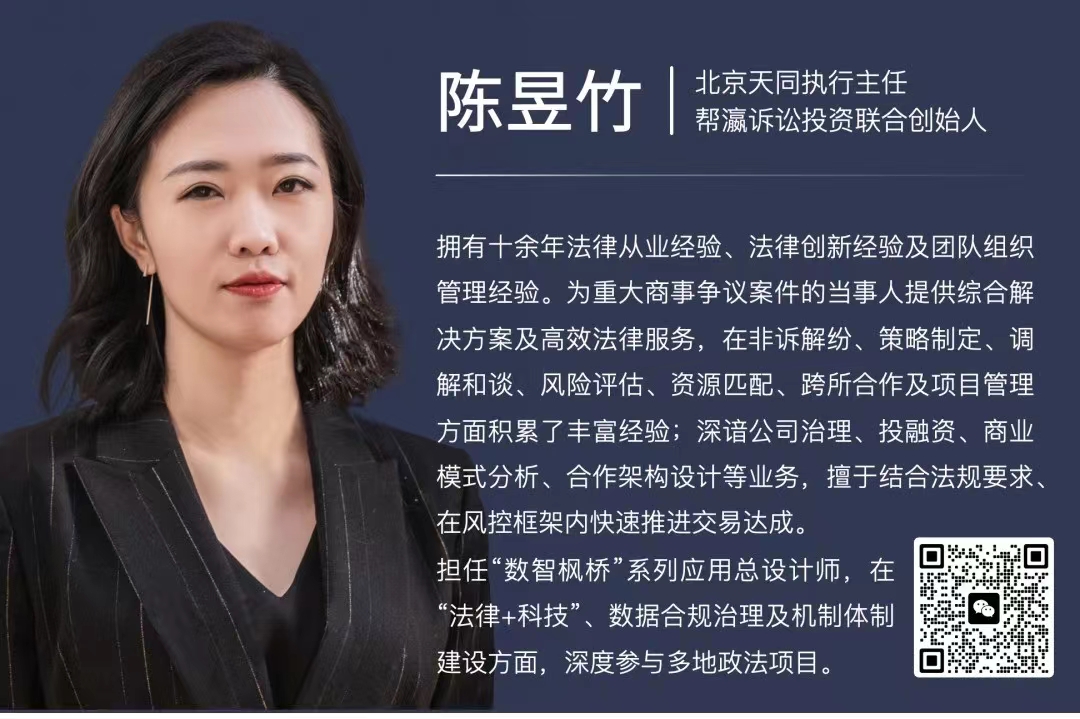

查看往期文章,请点击以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