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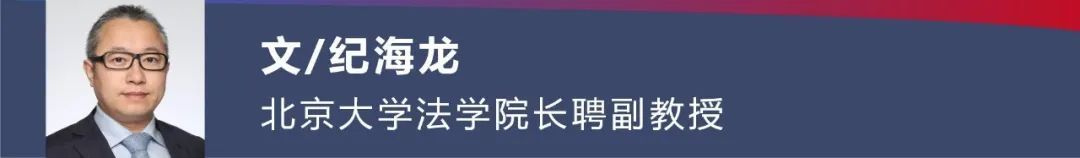
注:本文系基于《〈民法典〉第404条(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评注》(载《清华法学》2023年第4期,第158-175页)一文扩充修订而成。本文发表于朱庆育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条文选注(第4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
摘 要:在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剔除负担地处分抵押物时,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无须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内在根据在于:抵押权人选择抵押而非质押方式,将抵押物置于持续销售该类商品的抵押人之手,造成了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以剔除负担的方式转让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从而不知且不应知抵押权人限制或禁止抵押物转让的买受人,在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中购买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抵押权的追及力被切断。《民法典》第404条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构成该法第406条和第403条的特别规定。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于抵押物为特定存货(主要是成品和商品)且抵押人持续销售此种存货的情形,出售生产设备不能满足本条适用条件,抵押人登记的经营范围对于本条适用意义不大。实质为担保交易的买卖不能满足本条适用条件,而是应适用担保权排序的规则。不正常的销售方式也不会满足本条适用条件,但购买数量本身不足以认定销售方式不正常,抵押人和买受人之间的关联关系也不必然否定本条的适用。本条适用要求支付合理价款,部分价款的支付亦可满足支付价款要求,但以物易物、以物抵债以及抵销原则上无法满足此要求。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要求买受人取得抵押财产的所有权,且不限于以交付方式取得,交付替代的方式亦可。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要求买受人善意,该善意指向的是不知且不应知限制或禁止抵押物转让的约定,但该种约定被登记的,不能仅凭此登记认定买受人恶意。
关键词: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 抵押物转让 动产抵押 善意无负担取得
《民法典》第404条:
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目录
一、历史沿革、规范依据与体系关联【1-12b】
(一)历史沿革【1-3】
1.《物权法》时期:基于浮动抵押的论证【1】
2.《民法典》的转变:与浮动抵押脱钩【2-3】
(二)规范意旨【4-9】
1.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转让抵押物时无需本条之适用【4】
2.抵押权人沉默时由法律推定的同意【5-6】
3.存在限转或禁转约定时买受人的善意取得【7】
4.小结与澄清【8-9】
(三)体系关联与规范性质【10-12】
(四)本条的类推适用【12a-12b】
二、构成要件【13-50】
(一)动产抵押【13-15】
(二)正常经营活动【16-28】
1.出卖人(抵押人)而非买受人的正常经营活动【16】
2.登记的经营范围与正常经营活动【17】
3.抵押物属于出卖人持续销售的同类商品【18-22】
4.不属于不正常的销售方式【23-25】
5.不属于为实现担保目的的买卖【26】
6.关于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的关联关系【27-28】
(三)支付合理价款【29-40】
1.价款【29-33】
2.价款的合理性【34-35】
3.价款已被支付【36-40】
(四)取得抵押财产【41-44】
1.取得抵押财产的所有权【41-42a】
2.取得抵押财产的方式:交付与交付的替代【43-44】
(五)买受人善意【45-50】
1.买受人善意指向的是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转让的限制或禁止【45-47】
2.限转或禁转的登记【48-50】
三、法律后果【51-53】
1.买受人取得的所有权上无抵押权负担【51-52a】
2.抵押权人的保护措施【53】
四、举证责任【5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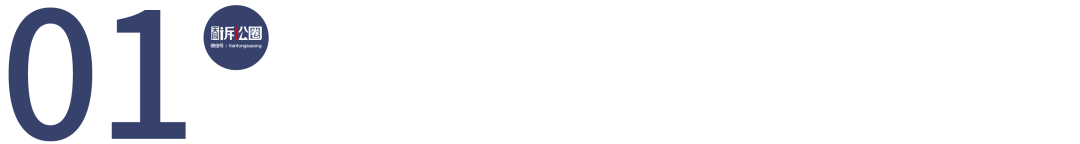
历史沿革、规范依据与体系关联
(一)历史沿革
1.《物权法》时期:基于浮动抵押的论证
【1】原《物权法》第189条第2款规定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只适用于浮动抵押情形。《物权法》立法工作人员对该款的阐述揭示,该款规定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乃是基于当时人们对浮动抵押的理解。彼时人们认为,首先,浮动抵押是以抵押人全部或部分动产做抵押,如不让抵押人处分抵押物,抵押人的经营活动就无法进行,从而浮动抵押人有权自由处分抵押物。[1]其次,浮动抵押具有抵押期间财产不确定,在抵押财产最终确定前处分抵押财产不受物上追及的特点。[2]可见,当时人们是按照英式浮动抵押来理解《物权法》中的浮动抵押。[3]基于英式浮动抵押下抵押人自由处分抵押物的特点,认为买受人取得浮动抵押下的抵押财产不应受抵押权人的追及。形象地说,英式浮动抵押情形在抵押财产结晶前担保的罩子尚未扣在担保标的上,从而抵押人自然可以无负担地处分抵押财产。[4]当时对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理解也受到保护买受人、减轻买受人查询登记负担之思想的影响。也即是,如果在浮动抵押中不保护抵押人的买受人,则买受人为避免购买的货物被追及的风险,就要在交易前查阅登记和征得担保物权人的同意。[5]而此种保护买受人的思想主导了《民法典》对于《物权法》第189条第2款中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修改。
2. 《民法典》的转变:与浮动抵押脱钩
【2】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立法者将《物权法》第189条第2款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从浮动抵押扩大到所有动产抵押领域。按照《民法典》立法工作人员的阐释,对此的理由是一般的动产抵押也可能以存货作为抵押标的,从而如果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限于浮动抵押场合,则任何买受人都要在交易前查询登记,以确定买卖标的上是否存在抵押以及该抵押是动产抵押还是浮动抵押。此不合交易习惯,降低交易效率。立法工作者还以大卖场的商品上被设定一般动产抵押为例,认为如顾客购买的商品会受到抵押权人的追及不尽合理,以此来论证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扩大到一般动产抵押情形的合理性。[6]可见,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从浮动抵押扩大到所有动产抵押,这种改动的立法动因是保护买受人的思想,即减轻买受人查询登记的负担。[7]
【3】本文认为,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浮动抵押脱钩,其实是顺应民法典下的浮动抵押并非英式浮动抵押而是美式浮动抵押的定位。美式浮动抵押是覆盖未来取得财产的动产抵押,其在登记时(而非如英式浮动抵押那样在结晶时)便发生相应的对抗和顺位效力,[8]本就是一种动产抵押。[9]《民法典》下浮动抵押的对抗、顺位等问题,适用与一般动产抵押一样的规则,再加上《民法典》新增第416条购置款担保超级优先规则以破除在先之浮动抵押的“垄断”地位,从而很显然《民法典》下的浮动抵押为美式浮动抵押。形象地说,美式浮动抵押情形,担保的罩子在设立和登记时便已经扣在担保标的上。从而对于抵押物的转让,民法典下的浮动抵押应适用与一般动产抵押相同的规则,也即是浮动抵押人转让抵押物不会当然地导致抵押权追及力被切断(《民法典》第406条第1款后句)。动产抵押(包括浮动抵押)下抵押物转让后抵押权追及力的切断,要么基于抵押权人的同意(边码4),要么基于本条之适用(边码5-7)。就此而言,浮动抵押和一般动产抵押并无区别,确无必要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仅限于浮动抵押的情形。[10]但《民法典》立法工作者以减轻买受人查询登记的负担、保护买受人为由来证成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虽不乏一定合理性,却有失重心。实际上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无义务查询出卖人的登记,并非是证成该规则的原因,而是适用该规则的结果。对于该规则的证成,应基于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地销售抵押物的推定与表象(参见边码5-7)。遗憾的是,《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也延续了立法工作者对本条的理解,同样基于减轻买受人查询登记的负担来设计《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的规定(参见边码9)。
(二)规范意旨
1. 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转让抵押物时无须本条之适用
【4】抵押权作为物权本具有追及力,但如果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动产的所有权,则买受人取得的所有权上将不再负担抵押权。此时并不需要本条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11]也不必满足本条规定的相关要件,例如价款已被支付或正常经营活动等。从而,本条其实是在不存在抵押权人之同意时,对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销售情形法律规定之抵押权追及力切断。是否存在抵押权人的同意,乃是意思表示解释问题。抵押权人的同意可以是明示的,明示的同意可以体现于抵押合同中相关的明示意思表示,或体现于事后的单独同意表示(例如基于与买受人的谈判);抵押权人的授权也可以是默示的,例如基于行业惯例或交易习惯,甚至是基于对抵押人无负担处分抵押物的容忍。[12]
2. 抵押权人沉默时由法律推定的同意
【5】在当事人未基于私法自治设定规则时,法律可能会配置缺省规则。如果抵押权人对于是否授权抵押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所有权未表态,即抵押权人对此保持了沉默,在特定情形法律也推定抵押权人同意抵押权人无负担地出售和转让抵押物。此即是本条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的核心情形。首先,担保权人明知担保人持续销售某类商品,却选择该类商品作为担保物;其次,担保权人选择的是抵押的担保方式,并未选择控制担保财产的质押方式。法律基于此推断抵押权人允许抵押人在其正常经营活动中无负担地出售和转让抵押物。[13]
【6】实际上,法律的此种推定在绝大多数情形亦符合各方当事人的预期。对于抵押权人而言,以出售该类商品为业的抵押人如不能无负担地出售该等商品,则抵押人(通常便是债务人)的销售便会困难,便无法获取现金流,进而抵押人也就无法清偿其针对抵押权人的债务;对于买受人而言,从持续销售某类商品的出卖人手中购买该类商品,买受人可以信赖即便该等商品上存在抵押权,抵押权人也会授权或至少不反对抵押人无负担地出售和转让该等商品;而对于抵押人来说能够无负担地出售和转让抵押物更是其经营乃至存活所需。[14]总之,在抵押权人对于是否同意抵押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沉默时,本条的规范依据在于法律对抵押权人之同意的推定。
3. 存在限转或禁转约定时买受人的善意取得
【7】抵押权人也可能限制或禁止抵押物的转让。限制转让包括转让抵押物应征得抵押权人的同意,也包括对抵押物的转让设置要求,例如要求买受人将价款直接支付给抵押权人或支付至特定账户;限制转让也包括禁止抵押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或者对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设置了要求。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1款,如买受人对于限转或禁转属于恶意即其知道限转或禁转约定的,买受人无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从而此时因买受人不能取得抵押财产而无法适用本条(边码41)。但如买受人善意即不知限转或禁转约定的,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1款,买受人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同时,其可基于本条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动产抵押权人选择担保人持续销售的商品作为担保物且并未采取控制担保物的质押方式,制造了其同意抵押权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的表象,买受人基于对此表象的信赖无负担地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此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善意取得。[15]此种善意取得并非是《民法典》第311条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1款规定的所有权的善意取得。《民法典》第311条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1款保护的是对有权处分的信赖,后果是物权的善意取得;而本条保护的是对有权无负担地处分的信赖,后果是取得的所有权上无负担。[16]
4. 小结与澄清
【8】本条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规范意旨在于:在抵押权人并未明示或默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处分抵押物的情形,动产抵押权人选择抵押人持续销售的商品作为担保物,且并未选择控制担保物的质押方式,法律基于此推定抵押权人允许抵押人在其正常经营活动中无负担地出售和转让抵押物,从而买受人可以无负担地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动产抵押权的追及力被切断。如抵押权人限制或禁止抵押人转让,则善意的买受人基于上述授权表象,也可以无负担地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在抵押人和债务人并非同一人即抵押人为他人提供担保时,本条亦同样适用。此乃因为本条是基于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出售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此推定和表象在抵押人并非债务人时亦同样存在。
【9】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时,认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豁免买受人的查询义务。按此观点,动产抵押采用登记作为公示方法,如任何人在和抵押人进行交易时都需要查询登记,那么会增加查询成本、交易成本,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而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正是豁免潜在买受人的查询义务。[17]从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第5项规定“买受人应当查询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作为排除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的兜底事由。但此种理解值得商榷。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之所以能切断抵押权的追及力,并非是因为要保护买受人对于抵押权不存在的信赖,而是要保护买受人对于(即便存在抵押权)抵押权人会同意抵押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无负担处分抵押物的信赖。买受人知悉标的物上负担抵押权并不妨碍本条的适用。即便买受人(例如依据交易习惯)有查询登记的义务从而应知标的物上负担抵押权,或者买受人虽然没有查询登记的义务却因实际查询了登记而知悉标的物上负担抵押权,均不妨碍本条的适用。换言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是因,豁免买受人查询登记义务是果。《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对于本条的认识,是倒果为因了。从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第5项将存在查询登记义务作为排除本条适用的事由,并不合理(边码50)。[18]
(三)体系关联与规范性质
【10】本条构成《民法典》第406条第1款第3句的特别规范。[19]按照《民法典》第406条第1款第3句,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即该句确认了抵押权(包括动产抵押权与不动产抵押权)的追及力。本条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实质上确认了正常经营中的买受人不受动产抵押权的追及,在动产抵押情形构成《民法典》第406条的特别规范。
【11】本条亦构成《民法典》第403条的特别规范。在动产抵押已登记或虽未登记但买受人恶意的情形,按照第403条的登记对抗规则,买受人取得的所有权上负担抵押权。但此时如本条的要件得以满足则买受人会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就此而言,本条构成《民法典》第403条的特别规范。[20]有观点认为在动产抵押未登记的情形,如买受人善意(即不知或不应知抵押权的存在),则应优先适用《民法典》403条。[21]买受人善意且两条中的“不得对抗”的要件均得到满足时,因无论是适用本条还是《民法典》第403条,法律后果均相同,即买受人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买受人自可依据举证的便利来选择依靠哪条保护自己,[22]没有必要强求买受人一定要诉诸哪一条文。
【12】本条适用的法律后果是买受人取得的标的物所有权上不再负担抵押权,本质上涉及的是抵押人与买受人之间处分行为的法律效果。但本条涉及抵押权人、抵押人和买受人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该三方的合意自可排除本条的适用,从而本条属于任意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但须注意的是,只是买受人同意或抵押人与买受人合意排除本条的适用,虽然此对抵押权人看似有利,但因我国法下在债务免除、真正利第三人合同以及债务加入的场合受益人均有权在合理期限内拒绝其受益,从而此时抵押权人有权在合理期限内拒绝之。
(四)本条的类推适用
【12a】本条只能适用于抵押物被买卖的情形,还是也可能被类推适用至非买卖情形例如租赁,对此存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保障抵押人的正常经营活动,而维持生产经营所需的、所有对抵押财产的处分行为都应该能够自由进行。因此,包括租赁、买卖、设定担保等在内的经营性行为,都应当属于“正常经营活动”。[23]本文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本文否认将该条无限制地类推到租赁或设定担保等情形,但认为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本条规则可被类推适用到租赁与许可情形。[24]
【12b】本条的内在根据在于抵押权人选择抵押人持续销售的商品作为担保物且并未选择控制担保物的担保方式,造成了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将此原理准用到租赁的场合便意味着,如果抵押人是以出租某种动产为业,那么在抵押人的正常出租经营活动中租赁该动产的承租人,也可信赖其会无负担地承租相关标的物,可以对抗在先的抵押权人。《民法典》第405条虽然只是规定了租赁先于抵押时租赁优先,但根据《民法典》第403条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4条第2项之规定可以推知,如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先于租赁的,在先的抵押权优先于租赁。但在抵押人为持续经营出租业务之经营者的情形,类推本条会实现承租人优先于在先登记之动产抵押权人的效果,此时会构成《民法典》第405条、第403条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4条第2项的例外情形。[25]同理,在以知识产权为担保标的的情形,如担保人是以持续许可知识产权为业的,本条亦存在类推的可能。类推的结果便是,在担保人正常经营的许可业务中的被许可人,可以对抗在先登记的知识产权质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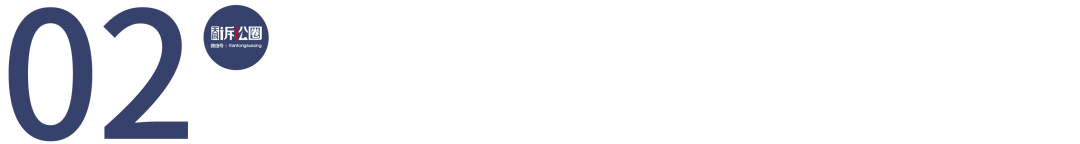
构成要件
(一)动产抵押
【13】本条适用于所有动产抵押的情形。[26]所谓动产,是指不动产(即土地和其上附着物)以外的物。《民法典》第395条第1款第4项和第6项分别规定“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和“交通运输工具”可作为抵押权的标的。对于未与土地分离的庄稼和林木等,民法理论将之理解为土地的附着物从而构成不动产,[27]似无法适用动产抵押的规则去设定担保。但如果是暂时养护嗣后会移走的苗木,应可被视为动产,在其上设定抵押应采取动产抵押的设定和登记方式,对之可以适用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28]如果当事人抵押的是某块土地上待收割或采伐的粮食或木材,此属于在未来动产上设定抵押即浮动抵押,对此现行法下并无障碍。从而抵押人将收割或采伐后的粮食或木材出售的,亦可适用本条规定。[29]机动车虽然属于特殊动产,机动车抵押虽然不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2条第7项)而是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参见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条、第22条)登记,但本条亦可适用于机动车抵押。例如汽车4S店以其销售的车辆为债权人设定抵押的,自4S店购车的买受人可基于本条规定无负担地取得车辆的所有权。[30]反对观点认为,买受人在购买机动车时,因较容易了解机动车上是否存在抵押权,从而没有必要对这类买受人予以特别保护。[31]但由于本条的适用与买受人是否知悉抵押权的存在无关(边码45),反对说不足为信。
【14】在动产担保功能主义的背景下,所有权保留买卖和融资租赁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定为担保物权交易,因此《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2款也将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交易纳入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覆盖范围。所有权保留交易中的保留买主或融资租赁交易中的承租人相当于本条中的动产抵押人,其出售标的物符合本条规定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买受人取得的标的物所有权上无负担,保留卖主或融资租赁出租人在标的物上享有的权利被切断。值得提及的是,由于融资租赁的标的常是设备,较少为存货,从而满足本条之适用条件的融资租赁交易应属例外(边码19)。
【15】本条不能类推适用到动产质押情形。出质人将质物(例如以返还请求权让与的方式)出售并转让给买受人的,即便质物属于出质人持续销售的某类商品且本条的其他条件(例如价款支付、所有权被移转)被满足,买受人也无法以剔除质权的方式取得所有权。这是因为,如担保人选择了控制担保物的担保方式,则本条规范所依据的担保权人同意担保人无负担转让担保物的推定和表象便被打破,从而本条不得准用到质押情形。[32]由于留置权的情形也无法证成该推定和表象,从而本条也不得类推至留置权情形。
(二)正常经营活动
1.出卖人(抵押人)而非买受人的正常经营活动
【16】本条对于何为正常经营活动未加以界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对此进行了解释。该条第1款首先明确《民法典》第404条中规定的“正常经营活动”是指出卖人而非买受人的正常经营活动。这是因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规范依据是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转让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而抵押权人通常只会在抵押物属于出卖人正常销售的商品时才不会反对抵押物被无负担地转让。从而此条中的正常经营活动,指向的是出卖人而非买受人的正常经营活动。[33]
2. 登记的经营范围与正常经营活动
【17】《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2款前句规定:“前款所称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是指出卖人的经营活动属于其营业执照明确记载的经营范围,且出卖人持续销售同类商品。”该规定要求《民法典》第404条中的正常经营活动必须属于出卖人营业执照明确记载的经营范围,对此颇值反思。一方面,市场主体均应进行设立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才能从事合法经营,[34]而在营业执照中均明确列出了该经营者的经营范围,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超越经营范围构成违法行为。但另一方面其违法只是体现在应办理变更登记而未办理变更登记。[35]而且,对于不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变更经营范围非常方便;在“先照后证”的背景下,即便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也可在行政许可前纳入登记的经营范围。从而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经营者并不会超越经营范围经营。而且国务院于2021年发布的通知中甚至明确规定,“企业超经营范围开展非许可类经营活动的,市场监管部门不予处罚。”[36]另外,由于农业生产经营者也可能设定动产抵押(参见《民法典》第396条),农业生产经营者主要是农村承包经营户,[37]而农村承包经营户无须办理登记,也就没有登记的经营范围,从而要求正常经营活动必须属于登记的经营范围,对于农业生产经营者既不必要也不现实。[38]在经营范围总体已经被“虚置”的背景下,强行要求本条中的正常经营活动必须属于出卖人登记的经营范围并无意义。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经营者均不会超越经营范围去持续销售某类商品,但即便极少数情况下某经营者超越经营范围持续销售某类商品,也不应断然认为此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毋宁是,对于正常经营活动的判断,“出卖人持续销售同类商品”这个标准更具有关键意义。
3. 抵押物属于出卖人持续销售的同类商品
【18】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2款前句,属于登记经营范围的出售行为并不当然构成本条意义上的正常经营活动,对此还要求“出卖人持续销售同类商品”。这是因为,如今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范围可能很广泛,但其真正开展持续性经营的范围却比较狭窄。[39]而且,一些辅助型或附属型的商行为也不应被认定为超越了经营范围,但这些不构成本条意义上的正常经营活动。例如印刷公司出售旧印刷机不属于印刷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40]而是属于出售生产设备(《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第2项)。究而言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规范依据在于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销售某商品仅仅落在担保人经营范围之内但担保人没有持续销售该类商品的,并不能造成此种推定或表象。
【19】《民法典》第395条第1款第4项规定“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可作为抵押财产。从会计准则角度看,生产设备属于设备,而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属于存货。构成出卖人的正常活动要求买卖标的属于出卖人持续销售的某类商品,此意味着构成本条下之正常经营的出售不会是生产设备的出售,[41]因为企业的生产设备不会构成企业持续销售的对象(《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第2项)。[42]此是因为,销售生产设备并非企业常态,企业也并非以此为业用以赚取利润,从而担保权人通常没必要允许担保人无负担地出售生产设备,即销售生产设备不会造成无负担出售的推定或表象。[43]如果某制造企业本就是制造某类型的设备并销售之,那么该种设备对于该企业构成存货而非生产设备,该企业销售该设备因符合“持续销售同类商品”,可构成本条下的正常经营活动。[44]
【20】并非所有出售存货(即《民法典》第395条第1款第4项中规定的“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的情形都会构成出卖人的正常经营活动。“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45]可见,只有产成品或商品(即《民法典》第395条第1款第4项中的“产品”)才构成企业日常出售的对象,而半成品、原材料等并非企业日常出售的对象。虽然原材料、半成品也属于存货,制造商销售原材料、半成品却通常不构成本条下的正常经营活动,[46]除非此种销售属于行业的通常或惯习做法。
【21】虽然担保人并没有以持续销售某类商品作为主要营业活动,但如果销售该类商品构成担保人所在相关行业的通常做法时,此亦可构成正常经营活动。[47]例如,某公司的主业虽然是制造并销售成品,但如果在该行业内类似公司可能也会在市场上时不时销售原材料,由于销售原材料符合该行业的通常或习惯做法,[48]销售原材料也构成出卖人的正常经营活动。[49]这同样是因为此情形可以造成担保权人允许担保人无负担出售担保物的推定或表象,即该行业通常会销售原料,担保权人将原料作为担保品但又没有对该原料进行控制(如采取质押方式),会造成担保权人允许担保人无负担出售担保物的推定或表象。
【22】对于某类商品是否构成出卖人持续销售的同类商品,应从理性买受人视角观察之。如从理性买受人角度看出卖人乃是以出售某商品为业,即可构成持续销售同类商品。就此而言,对于“持续”并无明确时间要求。例如从消费者角度看超市出售任何日用品几乎均可构成持续销售同类商品,即便该超市之前从未销售拖把,亦不妨碍超市现在销售拖把构成正常经营活动。进而,对于“同类”亦无法严格界定,因为类型可以无限细分下去。只要从理性买受人的视角看出卖人乃以出卖该种商品为业,即可认定为符合“持续销售同类商品”的要求。
4. 不属于不正常的销售方式
【23】尽管出卖人持续销售某类商品,但销售该类商品的特定销售行为异常,例如销售的方式或规模不正常时,也不构成正常经营活动。如果出卖人在其通常的销售渠道以外进行出售,例如出卖人通常只卖给零售商而此次是向批发商出售,此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50]这是因为,债权人很可能不会同意担保人在其通常的销售方式以外销售商品,从而担保人的此种举动并不会造成担保权人同意其无负担出售的推定或表象。
【24】《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第(2)项规定,“购买商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的买受人不构成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此项规定借鉴于《美国统一商法典》(以下简称“UCC”) § 1-201(b)(9)对“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之定义,按此定义大宗转让(transfer in bulk)情形的出售不构成正常经营活动。UCC第六编[51]规制之大宗出售,指的是非在出卖人的正常经营活动中(not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seller's business)销售其存货价值的一半以上,且买受人知或应知出卖人以后不再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UCC § 6-102(1)(c))。可见,UCC第六编调整的典型情形是某经营者出售大部分货物后转行不干。此时出卖人有清仓后卷款逃债的风险,[52]从而UCC第六编对此情形的买受人施以通知出卖人之债权人的义务。UCC第六编中的大宗转让之所以要求买受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出卖人未来不再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是为了将该编的适用限于会对债权人造成最大风险的销售。[53]买受人违反UCC第六编下通知义务的后果,并非是买受人无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UCC § 6-107(8)),而是买受人应赔偿出卖人之债权人因此造成的损害(UCC § 6-107(1))。可见,UCC第六编处理的问题是(类似于营业转让或公司分立情形)债权人的保护,防范的是某商人赊购货物然后将货物销售后卷款逃债的风险,此种风险是上个世纪初(即1900年左右)美国常见的一种欺诈类型。随着技术(如征信技术)和法律的进步,这种类型的欺诈已较鲜见。从而美国法学会和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已认为对于大宗买卖没有必要进行管制,并鼓励已经采纳UCC第六编的美国各州废止该编。[54]
【25】对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第2项“购买商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在具体适用上任何理解呢?本文认为,对于“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的理解,应回溯规则继受来源(美国法在20世纪初对大宗交易的规制)的最初动机,将此解释为出卖人的出售行为不同寻常,使得买受人合理怀疑出卖人的销售行为会损害其债权人利益。[55]抵押人出售大部分存货且不再从事相关营业,一般都会满足此合理怀疑的要求。但具体出售行为的数量只是衡量因素之一,即便(如美国法下对大宗出售的定义那样)出卖人出售存货中的大部分,出卖人也未必在从事逃债行为,也可能构成正常经营活动。[56]而“购买商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是否会导致买受人合理怀疑出卖人逃债从而不构成出卖人的正常经营活动,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57]一般情形的买受人作为消费者只买一个保温杯,某买家突然买了一百个保温杯,也不应仅因其购买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而否认该买受人为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58]
5. 不属于为实现担保目的的买卖
【26】《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第3项规定,出卖人(即动产抵押人)“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担保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抵押权人依旧可以请求就抵押动产优先受偿,即此时买受人不应被认定为本条中的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在民法典动产和权利担保迈向功能主义的背景下,如果抵押人为了担保目的出售抵押财产给买受人,虽然按照当事人间的交易文件买受人会取得动产所有权,但该等交易应被认定为担保交易。在为实现担保目的而订立买卖合同的情形,如在形式上并未转移抵押财产的所有权,那么本条会因不符合 “取得抵押财产”的要件而不得适用。如买受人在形式上已经取得了抵押财产的所有权,也应认定买受人实质上并未取得所有权,而只是取得了一个担保物权(《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68条)。[59]此时在抵押权人与买受人(新的担保物权人)之间,应适用《民法典》第414条第2款竞存的担保物权排序的规则。为实现担保目的而出售抵押动产,典型的情形如售出回购交易,即抵押人和买受人约定将财产转移至买受人名下,在一定期间后再由抵押人或者其指定的第三人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回购,抵押人或第三人到期不履行回购义务,财产归买受人所有。按照《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68条第3款,此种情形应按照担保交易处理,买受人取得的并非所有权,实质上取得的是担保物权。此时不应适用本条,而应按照竞存担保物权的顺位规则处理。[60]
6. 关于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的关联关系
【27】按照《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第4项,“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的,抵押权人依旧可以请求对抵押财产进行优先受偿,即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不予适用,抵押权的追及力未被切断。按照该司法解释起草人的观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哪些情况下可以豁免买受人的查询义务……如果买受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已被设定担保物权,此时其就不能援引该项规则阻却抵押权的追及效力。”[61]根据此种理解,在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时,因买受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买卖标的上已被设定担保物权,所以此时不应适用本条来切断抵押权的追及力。但如上文所述(边码9),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豁免买受人的查询义务。即便买受人知道买卖标的上负担抵押权,只要买受人构成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抵押权的追及力也会因本条的适用而切断。
【28】因此,只是买受人与出卖人间存在关联关系从而买受人知或应知买卖标的上负担抵押权,并不足以排除本条的适用。不过,如果抵押权人和抵押人之间存在限转或禁转约定,在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时可以认为买受人知悉此等约定,从而会因买受人非善意而排除本条的适用(边码46)。如抵押权人和抵押人之间并不存在此等约定,抵押人向其关联企业出售抵押财产,只要交易公平合理,且不存在其他异常情况的,并不必然损害债权人利益,[62]从而也不能推翻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转让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本条依旧可以适用。但在相关买卖为关联企业之间的买卖时,对于交易是否公平合理以及不存在异常情况,可由买受人负担举证责任,买受人如不能说明具体交易行为的合理性,应视为关联企业之间的买卖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63]
(二)支付合理价款
1. 价款
【29】本条的适用要求买受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价款指买卖合同下买受人支付给出卖人的金钱。在此可提出的问题是,本条中的价款是否必须是金钱,还是买受人提供某种价值(value)亦可。以货易货或以物抵债是否满足价款的要件?就此应基于本条的规范意旨和调整之利益关系进行分析。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的内在根据是对于抵押权人允许抵押人无负担转让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而此种推定和表象最终是因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也符合抵押权人的利益,至少通常不会损害其利益。如果抵押人以持续销售某类商品为业,其营利和现金流都倚赖于出售此种商品,那么其可以无负担地出售此商品对于抵押权人也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抵押人才可以获取现金流进而偿还其欠抵押权人的债务。换言之,抵押权人之所以通常不会反对抵押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出售担保物,是看中抵押物的变价能力,如果抵押物的转让不能换取价值,那抵押权人不太可能会愿意抵押物无负担地转让,因为这等于抵押权人丧失了担保又不能换取新的偿债可能。从而,出售抵押物换取金钱肯定满足本条的价款要求,这也是实践中的常态。
(1)关于互易
【30】抵押权人之所以愿意允许抵押人无负担地处分抵押物,是看重抵押物的变价能力。但如果抵押物变价后所换来者并非金钱(互易),则抵押人很难以其直接清偿抵押权人的债权,其虽然增加了抵押人的责任财产但不能增加其现金流,抵押人还需要再次变价才能换来现金流。相比于卖货换钱,互易似乎对于抵押权人会更加不利。但对此也要在类型化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64]
【31】如果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是针对某类型财产的浮动抵押,且互易换来的货物也属于此类型从而可被浮动抵押所覆盖,那么互易对于抵押权人并无不利,此时抵押权人大概率不会反对抵押人无负担处分抵押物。如果抵押权人在抵押财产的收益(proceeds,即由抵押物所续生之财产)上设定了担保权,例如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约定抵押权人的担保权继续存续于抵押财产所生之任何收益,如应收账款、价款或互易所得等等,且将此约定登记,情况会如何呢?此时,由于互易换取的财产可被潜在交易第三人(例如想购买所易之物的第三人)预测为抵押财产之收益的可能性比较低,也即是在实物形式之收益的场合收益上担保权的登记基本无法起到信息传递作用,从而实物形式之收益也不应顺延收益担保权的顺位效力和对抗效力。[65]在此场合,互易所换得之物上虽然也存在抵押权人的担保权,但因该担保权未公示从而不具有对抗力,其虽然增加了抵押人的责任财产,但却“掏空”了抵押权人的担保权而并未实质增强其债权得到清偿的可能。从而很难认为此时抵押权人会同意抵押人通过互易无负担地处分抵押财产。
【32】综上,对于互易,只有在所易之物会被抵押权人在先设定的浮动抵押所覆盖时,才可以推断抵押权人一般不会反对抵押物被无负担地处分。此时可认定互易满足本条“价款”要件。而对于其他情形的互易,本文认为不应满足本条下的“价款”要素,从而不应适用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66]从而抵押人的交易相对人在面临互易交易时,应查询抵押人登记,如发现标的物上可能存在抵押权,其可以选择采取普通的买卖方式即支付金钱作为价款,或者可以和抵押权人谈判以使其同意抵押人无负担处分抵押物。总之,对于互易这种比较少见的交易,认定其通常不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67]让该交易中的交易相对人承担控制风险的成本,并无不当。
(2)关于以物抵债
【33】如动产抵押人与第三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约定以抵押物抵充抵押人欠第三人的债务,此可否构成本条下的“价款”?首先,如果在被抵之债到期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且债务人此时并未放弃期限利益(也即是按照双方约定此时债并未被消灭,而是待期限届满时才因“以物抵债”而消灭),应认定为此种协议实际上是担保合同。如标的物并未交付给第三人,此时相当于抵押人以该物为第三人设定了一个动产抵押;如标的物交付给了第三人,此时相当于抵押人以该物为第三人设定了一个动产质押。[68]无论如何,此时对于抵押权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应适用担保权排序的规则(《民法典》第414、415条),而非本条规定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其次,如果在被抵之债到期后达成以(抵押)物抵债协议并将该物交付给第三人的,此时抵押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协议虽不构成担保合同,但由于该物所有权移转给第三人是为了消灭既存债务,且并未因此换取新的价值,从而很难认为抵押权人会同意抵押人将抵押物无负担地转让给第三人。即此时的以物抵债无法满足本条中的“价款”要素。[69]综上,以物抵债要么构成担保交易,要么难以满足本条规定之“价款”要素。也即是,以(抵押)物抵债将抵押物移转给第三人的,无法触发本条规定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70]但如果买卖对价的组成是一部分金钱加上一部分抵债,因此种方式带来了部分新价值,且不宜将一个交易从整体上划分效果完全不同的两部分。从而此时也可能会导致本条的适用。此时应重点考察价款是否合理以及买受人是否善意等其他要件是否满足。[71]
2. 价款的合理性
【34】本条规定构成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应支付合理价款。对于价款的合理性,《民法典物权编解释一》”)第18条在解释《民法典》第311条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合理的价格”时,规定“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数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体情况,参考转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此“综合认定”对于本条下价款合理性的认定有参考意义。[72]
【35】但也要注意到《民法典》第311条中“合理的价格”与本条中的“合理价款”有所不同。《民法典》第311条的法律后果是善意取得物权,涉及的是原所有权人丧失所有权和取得人取得所有权。《民法典》第311条中“合理的价格”要件的功能,一是确认(与所有权人相比)无偿受让人较不值得保护,二是价格是否合理也是判断受让人是否善意的重要因素,但其与原所有权人在丧失所有权后针对无权处分人的救济关联较小。[73]从而《民法典》第311条中的“合理的价格”,可以不同于市场价格,甚至“半卖半送”也可以满足此要求。而本条的法律后果是抵押权追及力的切断,涉及的是抵押权人与买受人之间的利益衡量。如果忽略其他担保措施,本条中的“合理价款”,将是抵押权人丧失抵押权后“追及”的最主要对象。抵押权人可能会和抵押人约定,抵押人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出售抵押财产取得价款后,应以其清偿针对抵押权人的债务;抵押权人也可能会在抵押财产的收益(如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取得的应收账款或现金)上设定应收账款质押或账户质押。这些均表明,本条中的合理价款应比《民法典》第311条中“合理的价格”的认定要更加严格。一般而言,本条中的合理价款应以接近市场价格为准。[74]在商业买卖中,“半卖半送”原则上不应认定为满足本条下价款的合理性。[75]当然对此还是要依据交易的情形综合判断。例如当买受人是消费者时,商家正常的打折促销不应认为价款不合理;在电商环境中,关于合理价款的认定也应更弹性。
3. 价款已被支付
【36】本条明文规定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应“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对此,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虽然本条文义明确要求价款应已支付,但此要求是否合理,从而是否应对“已经支付”的要求进行目的性扩张(也即是即便买受人价款未支付亦可构成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其次,即便秉持价款一定要支付的要求,价款是否要完全支付亦或只要支付部分即可?
【37】关于是否要求买受人已经支付价款,学界有不同观点。肯定说认为要求价款已被支付具有合理性。对此的理由,一是认为仅仅订立买卖合同但尚未支付价款或只支付极少价款的买受人,在利益衡量上不值得保护;二是认为价款支付要素可以防范抵押人和他人合谋虚构合同欺诈抵押权人。[76]
【38】否定说则认为要求价款已经支付并不具有合理性。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曾有观点在立法论层面主张不应硬性要求买受人已支付价款。其理由主要有:首先,比较法上无论UCC、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还是《欧洲共同框架参考草案》(以下简称“DCFR”)[77]对于正常经营中的买受人取得担保财产后切断担保权,均不要求买受人的价款已被支付;其次,从体系的视角看,《民法典》第311条在善意取得的场合并不要求“合理的价格”已被支付,对于本条中的合理价款也应一体处理;再次,从对抵押权人的利益影响角度看,虽然价款被支付可增加担保人(很可能同时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但即便价款尚未支付完毕,担保人针对买受人的价款请求权也属于担保人的一般责任财产范围。[78]在《民法典》施行后,学界亦有观点认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不应作为本条的构成要件,而是仅具有列举作用。此观点的理由主要是:并非价款被支付才是对抵押权人最有利的。价款支付后会存在抵押人私自处分款项的风险;而即便价款未支付完毕,抵押权人还可向买受人主张剩余价款请求权以实现其在抵押财产之收益(包括转让该财产取得的应收账款)上的担保权。[79]
【39】本文认为,肯定说的理由有些未必成立,有些有一定道理。首先,就抵押权人和买受人之间的利益衡量而言,正如否定说所指出的,即便价款尚未支付,对于抵押权人也未必不利甚至更加有利,因为价款支付后存在债务人将资金挪作他用而非用于清偿抵押权人之债权的风险,且价款未支付抵押权人也可能会在抵押人针对买受人的应收账款债权上享有担保权。其次,价款支付要件可以防范欺诈这个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道理。例如在抵押权人对抵押物采取执行措施后,抵押人和买受人恶意串通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转移抵押物所有权,并将合同日期倒签至抵押人违约之前或抵押权人对抵押物采取执行措施之前,如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不要求价款支付的要件,则此种操作可能使得动产抵押权人丧失抵押权。此种操作虽然会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被认定为悖俗无效,但恶意串通的证明毕竟比较困难和个案化,具有不确定性。不过另一方面,正如否定说指出的,即便此种操作无法因悖俗(具体表现形式是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被认定为无效,即便此时抵押权人丧失了抵押权,但抵押权人有可能会在抵押人针对第三人的应收账款上享有担保权。从而此种操作对于抵押权人的害处也未必特别大,主要会增加抵押权人执行担保时的“麻烦”。
【40】对于本条下的“已经支付合理价款”,立法论上的根据虽未必扎实,但由于本条已明文规定价款应“已经”被支付,且要求价款已经支付确实会有利于防范抵押人与第三人串通悖俗的风险,从而在解释论上,不妨认可本条的文义表述,即本条的适用要求买受人已经支付价款。[80]但鉴于要求价款支付的最主要意义不在于维持担保人的偿债能力而是在于防范担保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悖俗风险,所以不必要求全部价款被支付,只要买受人可证明相关买卖合同下的部分(甚至极少部分的)价款被支付,即可满足本条下价款被支付的要求。[81]但价款的支付至晚应发生在抵押权人对抵押物采取执行措施前,否则依旧会存在抵押权人采取执行措施后,抵押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倒签合同约定占有改定并支付部分价款,以实现“掏空”抵押权的目的。另需注意的是,与以物抵债不宜认定为价款(边码33)同理,如买受人以价款与抵押人之前欠买受人的债务抵销以此消灭价款债务,也不宜认定为价款已支付。[82]
(四)取得抵押财产
1. 取得抵押财产的所有权
【41】本条的适用要求买受人取得抵押财产。本条中的取得抵押财产应为取得所有权(下称“所有权取得说”)。其原因:一是物权优先于债权,如果买受人还没有取得所有权,其享有的权利就只是债权请求权,不能对抗抵押权人的担保物权;[83]二是由于本条的法律效果本质上是切断抵押权的追及力,在买受人尚未取得所有权时,还谈不上切断抵押权的追及力。[84]
【42】学界有观点借鉴UCC的作法,将本条中的取得抵押财产解释为取得可实现的实际履行请求权(下称“实际履行请求权取得说”)。在此请求权的可实现主要是指标的物的特定化。该说主要借鉴美国UCC下对于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的定义,即“只有占有货物或有权根据第二编[即买卖编——本文作者注]向出卖人收回货物的买受人才可能是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认为只要买受人对被特定化的标的物享有实际履行请求权即可切断抵押权的追及力。对于此作法的实质理由,该观点认为从鼓励担保物流通的角度看,享有实际履行请求权的买受人的期待应获保护。[85]但并未进行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实际履行请求权说并不足取。美国法赋予享有实际履行请求权的买受人以优先于抵押权人的地位,这是因为在美国合同法下实际履行请求权本就是例外情形,而买卖标的是货物而非不动产的场合支持强制实际履行就更属例外了。美国法下在货物买卖认可买受人实际履行请求权的情形,主要是因为该货物对于买受人是独特的,对此买受人不能进行替代性购买会成为强有力的证据。[86]从而,美国法下对于货物享有实际履行请求权的买受人会更加值得保护。而由于我国普遍认可实际履行请求权(《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1句),如赞同实际履行请求权取得说,意味着不存在特别保护买受人之理由的绝大多数货物买卖情形也要倾斜保护买受人,这并无必要。而且,即便采所有权取得说,买受人如想在取得货物直接占有前便获得本条的保护,可以通过与出卖人约定占有改定尽早取得标的物所有权。
【42a】而且,所有权取得说为法律适用提供了清晰简单的标准,而实际履行请求权取得说可能会造成不公平。假设抵押人将抵押物一物二卖,先与甲签订买卖合同,后与乙签订买卖合同。善意的甲除了未取得抵押财产所有权外已满足了本条的其他所有要求,从而如按照实际履行请求权取得说,抵押权人便不得对抗甲,这实质上意味着在甲取得实际履行请求权(且标的物被特定化)之时(时点一),抵押权人的抵押权便已因本条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而被除去。[87]假设后买人乙并不符合本条的规定(如未支付价款或乙为恶意),但如果抵押人选择将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乙(时点二),那么因在时点一标的物上已不负担抵押权,乙在时点二便可以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尽管乙作为买受人并不符合本条的规定从而本不应受到保护。而按照本文认可的所有权取得说,如抵押人选择向甲转移所有权,在甲取得所有权后抵押权人对乙的合同便已陷入给付不能,从而原则上乙无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如抵押人选择向乙转移所有权,乙如不符合本条规定则抵押权的追及力不会被切断,从而乙也无法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所有权。
2. 取得抵押财产的方式:交付与交付的替代
【43】尚可讨论的是,本条下买受人取得抵押财产的所有权是只能通过现实交付的形式,亦或也可通过交付的替代形式(简易交付、返还请求权的让与与占有改定)。[88]有此一问,是因为在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场合,对于占有改定方式是否可支撑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争议极大。有力说对此持否定意见。[89]形式上的理由是占有改定情形受让人并未取得强度足够的占有,[90]实质上的理由是要避免所有权被通过占有改定方式秘密地善意取得,而所有权被秘密地善意取得通常是所有权人无法承受的风险,从而因其不具有可归责性而不应使其丧失所有权。[91]但对交易安全要求极高的场合,例如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动产的,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压制了风险原则。从而在此种场合,无论是占有改定还是返还请求权的让与都应该可以导致善意取得,秘密地善意取得应被允许。[92]
【44】在本条调整之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的场合,恰恰就是抵押权人将抵押物留于持续出售某类商品的抵押人之手,此时一方面应视为抵押权人允许抵押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无负担地出售抵押物,抵押权人本就已承接了抵押物被无负担出售的风险,另一方面保护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之交易安全的需求也极高,从而应认可买受人通过交付的替代方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也可满足本条规定之“取得抵押财产”,[93]即便此会导致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被秘密地切割掉。[94]
(五)买受人善意
1.买受人善意指向的是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转让的限制或禁止
【45】本条文义中并未规定买受人善意的要件。依本条文义,即便买受人在受让动产标的物时明知该物上负担抵押权,也不妨碍买受人无负担地取得动产所有权。其原因是,抵押权人选择抵押人持续销售的商品作为担保物,且并未采取控制担保物的担保方式,此造成了其同意抵押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从而,买受人知悉抵押权存在与否不影响本条的适用。
【46】但恰恰因为本条是基于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转让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所以如果买受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抵押权人反对抵押权无负担转让抵押物的,此种推定和表象便被打破,本条也就不应适用。从而本条文义中虽未要求买受人善意,但买受人善意的要件应被解释进本条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只是在此买受人的善意,并非是指其不知且不应知转让标的物上存在抵押权,而是指其不知且不应知抵押人不具有无负担转让抵押物的权限,从而抵押人出售抵押物侵犯了抵押权人的合同权利。[95]例如抵押权人禁止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或禁止抵押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或对抵押物的转让附加条件而在具体个案中相关条件并未得到满足。具体而言,受让人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下的恶意,需要满足三个层层递进的条件。首先,买受人需要知或应知标的物上存在担保权;其次,买受人须知或应知出卖人与担保权人之间存在“就该动产限制或禁止出售”之约定或其他类似约定;再者,买受人还应知或应知其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行为会侵犯担保权人基于前述担保协议所享有的权利。[96]对于买受人“应知”的标准,应参考《民法典物权编解释一》第14条之规定,以因重大过失不知为标准。
【47】至于在本条文义并未提及买受人善意这个要件的情况下如何引入该要件,学界观点不一。有认为应借鉴UCC § 1-201(b)(9)之规定,将买受人善意要素直接涵括到正常经营活动的概念之中。[97]如买受人为恶意的,其购买行为便不属于“正常经营”的范畴,买受人因此不得因“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受到优先性保护。[98]但本文认为,将“善意”要素解释到“正常经营活动”的概念中,会混淆正常经营活动这个客观要件和善意这个主观要件。就举证责任而言,买受人应负担证明正常经营活动而抵押权人应负担证明买受人为恶意,两者不应被混淆。本条未规定买受人善意这个要件,应被视为构成法律漏洞。此法律漏洞可基于目的性限缩加以填补。即,本条乃是基于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无负担出售和转让抵押物的推定和表象,在此推定和表象被打破之时,应对本条进行目的性限缩,不允许买受人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99]在此,买受人善意的标准是不知且非因重大过失不知。
2.限转或禁转的登记
【48】《民法典》第406条原则上认可抵押物自由转让,但后果是抵押权追及力依旧存在。同时《民法典》第406条第1款中句又规定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所谓另有约定,主要是指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约定限制或禁止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对于此约定的效力,学界曾有观点主张其只具有债法意义上的效力,而并未限制抵押人的处分权,亦即抵押人违反该约定转让抵押物的只会导致其向抵押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会影响其向受让人转让抵押物所有权的权限。[100]但按照《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如果抵押权人有证据证明受让人知道抵押权人和抵押人间禁止或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的约定的,或者该约定被登记的,则受让人无法取得抵押财产的所有权。按照《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限制或禁转约定剥夺了抵押人的处分权,从而抵押人的处分构成无权处分,受让人只能依据善意取得的法理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从而若买受人对此等约定恶意,其无法取得所有权,进而便无须讨论本条是否适用以使得买受人无负担地取得所有权了。但问题在于,若限转或禁转约定被登记,是否可认为买受人应当知道该限转或禁转约定,从而因买受人恶意导致买受人无法取得所有权?回答此问题的关键是,符合本条其他要件的买受人是否有义务查询登记。如其无义务查询登记,那么限转或禁转约定被登记也不等于买受人为恶意,《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2款在此不应适用(目的性限缩),买受人因《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1款取得所有权,进而基于本条之适用其取得的所有权上无抵押权负担。
【49】在消费者买受人的场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肯定无义务查询商家的登记,从而即便限转或禁转约定被登记的,不应推定消费者买受人为恶意,即此时限转或禁转约定不妨碍本条的适用。若买受人非为消费者而是经营者、非营利法人或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该等买受人从持续销售某类商品的出卖人处购买该类商品时,是否有义务查询登记?鉴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内在根据是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中的销售行为存在无负担移转所有权的推定和表象这个授权表象,该表象可以使得买受人相信,即便标的物上存在动产抵押抵押权人也会授权抵押人在其正常经营活动中无负担地出售标的物,从而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并无义务查询出卖人的登记。[101]
【50】结论便是,满足本条要件的买受人无义务查询出卖人名下的登记,从而即便抵押权人和抵押人之间的限转或禁转约定被登记,也不能仅凭借此登记便认定买受人恶意。[102]当然,如果特定个案中存在相关端倪指向限转或禁转约定可能存在的,买受人便有义务查询出卖人的登记;或者如特定行业惯例或交易惯例下作为经营者的买受人一般均查询出卖人的登记的,也应认定买受人有查询登记的义务。此时如果限转或禁转约定被登记的,买受人应被视为恶意,依据《民法典》第406条第1款中句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2款买受人无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进而更谈不上基于本条之规定无负担地取得所有权了。就此而言,《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第5项“买受人应当查询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的不当规定或可解释为:在限转或禁转约定被登记时,如买受人按照行业惯例或交易习惯应当查询登记而未查询的,因买受人恶意而无法适用本条。[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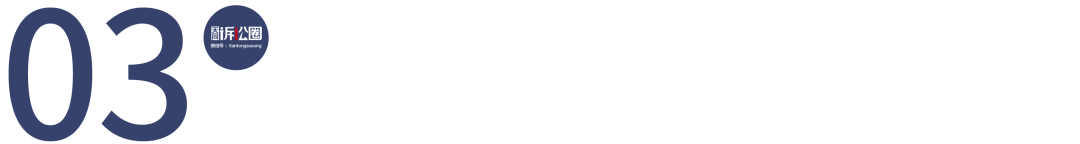
法律后果
(一)买受人取得的所有权上无抵押权负担
【51】本条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买受人”。此规定从句法上看,其实省略了主语,即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人”。抵押权人不得对抗符合本条条件的买受人,具体究竟何指?对此《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规定的是,“请求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无论本条中的“不得对抗”,还是《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6条第1款中的无法“请求就该动产优先受偿”,均可有如下两种理解:一是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的法律后果是动产抵押权依旧存在,只是降格为不具有对抗力的抵押权;二是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的法律后果是动产抵押权消灭,买受人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正确的理解应为第二种,即买受人取得的标的物所有权上不再负担抵押权。[104]从而如买受人将标的物转让给第三人的,即便该第三人不构成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第三人取得的标的物上亦不负担抵押权人的抵押权。
【52】因本条之适用导致抵押权负担被除去的时点是本条要件满足之时。具体而言,出卖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出售标的物给买受人,则在至少一部分价款被支付且买受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之时,标的物上的抵押权被剔除;如买受人先支付价款后取得所有权,则为取得所有权之时;如买受人先取得所有权后支付价款,则为价款被支付之时。
【52a】如抵押人和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则在不认可处分行为无因性的司法实践下,因标的物所有权自始并未转移至买受人,本条的适用要件未被满足,标的物上的抵押权负担也就未被除去。如抵押人和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被撤销,则在不认可处分行为无因性的司法实践下,标的物所有权溯及既往地自始未移转至买受人,此时发生与买卖合同无效时相同的效果,即标的物上的抵押权负担未被除去。如买卖合同被解除或发生了相当于解除的退货,则在解除效果的清算说下,标的物已经转移给买受人,此时如本条其他要件满足,则标的物上的抵押权负担已被除去。在基于解除的法律效果标的物所有权被返还给抵押人后,如抵押权为浮动抵押,则此被返还的标的物当然又被该浮动抵押所覆盖。此时如抵押权并非浮动抵押而是一般的动产抵押,该被返还的标的物是否重新成为抵押权的标的,则颇费思量。鉴于让被返还的标的物重新恢复抵押物地位且享受原抵押权的对抗和顺位效力,可能会更加符合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当初设定抵押权时的潜在合意,本文初步赞同因买卖合同被解除而返还的标的物重新恢复原抵押标的的属性。
(二)抵押权人的保护措施
【53】存货上的担保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很脆弱的担保利益。[105]在存货中的产成品上设定动产抵押,必然面临着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破坏”。抵押人在其正常经营活动中销售作为抵押财产的产品,常会因本条之适用而使得抵押权被消灭。此时,抵押权人只能倚赖因销售抵押财产而取得的收益。抵押权人可基于《民法典》第406条第2款向抵押人主张将转让所得的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提存。[106]对于我国法下动产担保上的担保权是否会覆盖转让担保财产取得的收益,例如应收账款或现金收益,学界存在争议。[107]有观点认为这些收益会自动被动产担保权所覆盖;有观点则认为现行法下无法解释出自动覆盖的效果,毋宁是抵押权人应在收益上设定担保,例如在应收账款上设定应收账款质押,在现金收益上设定账户质押,乃至约定及登记动产抵押覆盖因抵押财产取得的收益。[108]在司法实务对此点争议并未发展出统一态度的背景下,本文建议在存货尤其是产成品上设定动产抵押(包括浮动抵押)的债权人,应自我采取措施保护其利益,例如同时在销售产生的应收账款上设定应收账款质押,在销售获取的现金上设定账户质押或采取其他控制抵押人账户的方式,并尽量采用浮动抵押,以覆盖新流入的存货。[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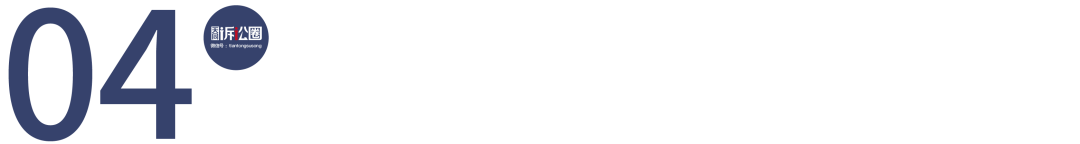
举证责任
【54】在抵押物被出售的情形,动产抵押权人为执行买受人购买的标的物,应负责证明其在标的物上设定了抵押且该抵押在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给买受人前已登记;如在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给买受人前该抵押并未被登记,则动产抵押权人应负责证明买受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标的物上负担抵押权。
【55】买受人为阻却抵押权人的追及,其应负责证明抵押权人已经明示或默示授权抵押人无负担地转让抵押物,或证明买受人是在抵押人的正常经营活动中购买了该标的物,即标的物属于抵押人持续销售的商品、其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进而,抵押权人可通过证明标的物的销售方式不正常,或证明标的物的转让是为了担保目的,或证明买受人恶意(即知道或应当知道存在限转或禁转约定),来推翻本条的适用。在抵押人和买受人为关联企业时,应由买受人负责证明交易的合理性。
注释:
* 本文为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法评注编纂重大问题研究”(批准号:22&ZD205)的阶段性成果;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优化营商环境视角下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现代化研究”(21BFX018)的阶段性成果。
案例检索情况:利用北大法宝数据库的法条联想功能,在《民法典》404条以及《物权法》第189条下选择“引用到条”。在该检索结果的基础上,同时在北大法宝、威科先行、Lexis China律商网三个数据库的案例检索框下,组合运用关键词“《民法典》第四百零四条”(或“《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正常经营活动”“动产抵押”“合理价款”,关键词间采用“且”的逻辑,选择“全文”“精确”“同篇”的检索选项进行检索。在补缺与剔重后,得到适用《民法典》第404条的56篇裁判文书,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略作讨论的裁判文书仅1篇;得到适用《物权法》第189条第2款的192篇裁判文书,实质性讨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裁判文书28篇。从裁判文书看,司法实践对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认识比较混乱,正确适用的情形不多。
[1]《物权法》时期司法实践对于浮动抵押多持此态度,并以此为理由论证《物权法》第189条第2款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终字第4016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3民终1575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二终字第00041号民事裁定书。
[2]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415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3页。对于物权法立法工作者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之阐释的反思,参见龙俊、高曼琳:《动产抵押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十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17-18页。
[3]关于英式浮动抵押下抵押人有权自由处分抵押物,且抵押财产确定前处分抵押物不受物上追及的特点,可参见[英]艾利斯·费伦:《公司金融法律原理》,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7页。
[4]实际上,如果认为浮动抵押只是在结晶时才发生效力,在此之前浮动抵押人可以无负担地自由处分抵押物,那么其实浮动抵押人的任何处分包括出售生产设备或赠予等,本应都是被允许的。也即是按此逻辑,在英式浮动抵押的模式下,其实本不需要《物权法》第189条第2款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
[5]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3页。
[6]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4页。相同观点参见龙俊、高曼琳:《动产抵押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十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39-41页。
[7]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4页。同时此改动也受到比较法的影响,立法者借鉴了美国法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的作法,即无论是一般动产抵押还是浮动抵押,都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
[8]参见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35页;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45页。
[9]但英式浮动抵押和一般的动产抵押完全不同,对于英国法下浮动抵押的定性与讨论,参见[英]艾利斯·费伦:《公司金融法律原理》,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7-373页。
[10]赞同的观点参见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33页;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52页。反对的观点,参见邹海林:《论〈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担保物权”的制度完善——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编物权为分析对象》,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2期,第37页;邹海林:《民法典上的动产抵押权规则体系解释论》,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5期,第35页。
[11]参见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0页;Official Comment 6 to UCC § 9-320; Richard B. Hagedorn, Secured Transactions, fifth edition, Thomson/West, 2007, p. 223.
[12]关于美国法下基于交易过程(course of dealing,相当于一系列交易中的惯例)的默示授权的讨论,参见Lawrence, Henning & Freyermuth, Understanding Secured Transactions, LexisNexis, 2012, pp. 258-259。
[13]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United States, 2010, p. 202.
[14]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95页;纪海龙、张玉涛:《〈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08-109页;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51页;龙俊、高曼琳:《动产抵押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十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40-41页。
[15]参见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2页;纪海龙、张玉涛:《〈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09页。
[16]对于不同表象的信赖是一个谱系:(1)对享有所有权的信赖,例如乙将从甲处借来的书转让给善意的丙,丙善意取得所有权;(2)对享有处分权的信赖,例如乙作为行纪商将甲委托乙修理的机器转让给善意的丙,丙善意取得所有权;(3)对负担不存在的信赖,例如甲在乙之机器上享有未登记之动产抵押权,乙将此机器转让给善意的丙,丙取得的机器上不再负担抵押权;(4)虽然标的物上存在负担,但信赖标的物可被无负担地处分,例如甲在乙生产的产品上设定浮动抵押,乙将产品在正常经营活动中转让给丙,丙取得的产品上不再负担抵押权。以豁免买受人查询义务作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主要目的,涉及的是上述(3),其背后的逻辑是,由于要豁免某些买受人的查询登记义务,从而这些买受人不知或不应知标的物上存在抵押权,所以买受人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而本文认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是涉及上述(4),即无论买受人是否知悉标的物上负担抵押权,买受人均可信赖抵押权人允许抵押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无负担地转让标的物。
[17]参见林文学、杨永清、麻锦亮、吴光荣:《〈关于适用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2021年第4期,第41页;似乎亦以此为理由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论证,参见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32-33页。
[18]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3页;杨代雄主编:《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311页(吴宏乔主笔)。
[19]相同观点参见岳红强、罗泽伟:《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对抗效力——以《民法典》第403条、404 条与406条的体系分工为视角》,载《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7期,第32-33页。
[20]认为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应当优先于登记对抗制度适用的观点,参见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22页;龙俊、高曼琳:《动产抵押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十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21、42页;岳红强、罗泽伟:《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对抗效力——以《民法典》第403条、404 条与406条的体系分工为视角》,载《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7期,第33-34页。
[2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486页。认为若抵押权未登记,则受让人为善意时应优先适用第403条而受让人恶意时第404条接续第403条适用的观点,参见王琦:《论抵押财产转让对抵押权的影响——以〈民法典〉第403,404,406条的协调适用为视角》,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3-6页。
[22]认为在《民法典》第403条和本条的要件均满足时“买受人可择一适用,此时构成法条竞合”的观点,参见麻锦亮:《民法典·担保注释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661页。
[23]参见钟维:《民法典编纂背景下我国浮动抵押制度的释评与完善》,载《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235页;木拉提、李军:《域外法律制度对完善我国浮动抵押制度的启示》,载《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3期,第116页。
[24]参见纪海龙、张玉涛:《〈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1页。
[25]仅以《民法典》第405条、第403条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4条第(二)项为根据,认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不应被类推至租赁情形的观点,参见刘智慧:《〈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134页。
[26]有观点认为,“该条中所使用的“正常经营活动中”这一特定术语,就将该条规范适用领域限定在了动产浮动抵押权“,参见孙宪忠、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4》,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9、154页(董学立执笔)。该观点的逻辑是,“正常经营活动中”指向存货的销售,而存货的抵押属于浮动抵押。但其实,存货的抵押未必一定是浮动抵押,如果存货的抵押不覆盖未来取得的存货,其就不是浮动抵押而是一般动产抵押。此在实践中也不少见。
[27]参见崔建远:《物权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28]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3094号民事判决书。
[29]美国法下,UCC § 9-320 (a)规定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不适用于自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人购买农产品的买受人。但1985年《美国食品安全法》(Food Security Act of 1985)在很大程度上废止了此种做法,规定原则上购买农产品的买受人也可被认定为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除非担保权人或债务人按照该法的通知要求向潜在买受人进行了通知或在(不同于担保融资登记系统的)一个州的中央登记处备案了“有效融资声明(Effective Financial Statement,简称为EFS)”。
[30]认为在机动车抵押场合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规则亦可适用的判决,参见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11522号、11532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终751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云0112民初2820、3241、3475、5365、5366、5367、5368、5369号民事判决书。
[31]参见刘智慧:《〈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140页。
[32]按照UCC § 9-320 (e)之规定,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不得适用于“有担保权人占有的有体动产之上的担保权益”。对此可参见Lopucki and Warren, Secured Credit, A Systems Approach, Fifth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p. 590.
[33]相同观点参见董学立:《论“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法学论坛》2010年第4期,第90页;孙宪忠、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4》,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51页(董学立执笔)
[34]2022年3月1日生效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8条。
[35]2022年3月1日生效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72条。
[36]《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高圣平教授认为,在鼓励营业自由、“万众创业”的背景下,出卖人具有相应的经营资格并不应构成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的“正常经营活动”的要件。参见程啸、高圣平、谢鸿飞:《最高人民法院新担保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55页。
[37]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83页。
[38]参见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8页。
[3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485页。
[40]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United States, 2010, p. 203; Grant Gilmore, Security Interests in Personal Property, Volume II,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1965, p. 694. 相反的观点认为,“非生产设备的抵押人为更新设备而出售二手设备”会构成本条中的正常经营活动;对此参见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8页。
[41]认为本条只会适用于出售存货情形,但并未将此纳入“正常经营活动”的解释,而是认为本条中的“动产”只能是存货的观点,参见张素华、李鸣捷:《〈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释论》,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2页。此种解释方案结论上并无不妥,但实践中会存在抵押人以机器设备和存货等一起设定抵押的情形,从而或许将出售存货纳入“正常经营活动”解释更为妥当。
[42]在物权法下认为出售生产设备也可构成正常经营活动的错误判决,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金商终字第664号民事判决书。
[43]错误地认为出售设备也可满足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判决,参见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6民终1399号民事判决书。
[44]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4页;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2页;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8页;刘竞元:《民法典动产担保的发展及其法律适用》,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60页。
[45]《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财会[2006]3号)第3条。
[46]参见Grant Gilmore, Security Interests in Personal Property, Volume II,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1965, p. 695; Robert H. Skilton,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under Article 9 of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Related Matters)," Wisconsin Law Review 1974, no. 1 (1974), p. 22.
[47]类似观点参见张素华、李鸣捷:《〈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释论》,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5页。
[48]对此可参见UCC § 1-201(b)(9)。
[49]关于美国法下相关案例的介绍,参见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9页。
[50]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United States, 2010, p. 202.
[51]关于UCC § 1-201(b)(9)中的大宗转让是否就是UCC第六编“大宗转让(bulk transfer)”中规定的大宗出售(bulk sale),美国法学界曾有不同观点。之所以会质疑UCC § 1-201(b)(9)对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之定义中的“大宗转让”是否就是UCC第六编规制的“大宗出售”,是因为后者的定义中包含了“非在出卖人的正常经营活动中”这样的表述,从而两者有循环定义之嫌。另有观点认为,UCC § 1-201(b)(9)对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的定义,是承继自UCC之前的《美国统一信托收据法(UTRA)》中对“正常贸易活动中的买受人(Buyer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de)”的定义,该定义排除“大宗受让人(transferee in bulk)”为正常贸易活动中的买受人。UTRA对“大宗受让人”的定义是“抵押人或质押人或实质上整体购买受托人业务的买方”。该观点主张UCC § 1-201(b)(9)中的大宗转让应按照UTRA对“大宗受让人”的定义解释。对上述观点的介绍参见Robert H. Skilton,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under Article 9 of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Related Matters)," Wisconsin Law Review 1974, no. 1 (1974), p. 29. UCC第六编之“大宗出售”和UTRA下“大宗受让人”的定义实质类似,都是指出卖人转让其所有存货的大部分的情形(从而存在逃债风险);但也有不同,例如前者要求买受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出卖人未来不再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而后者则无此要求。
[52]See Bradford Stone, Kristen David Adam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in a Nutshell, seventh edition, Thomson West, 2008, p. 164.
[53]See Official Comment 1 (c) to UCC § 6-102.
[54]参见美国法学会、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美国〈民统一商法典〉及其正式评述(第二卷)》,李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305页。
[55]《物权法》时期曾有案件中,浮动抵押人原高管出资成立了买受人公司,买受人租赁抵押人的场地经营,同时购买了抵押人场地中的所有存货后销售殆尽。此案中法院认为买受人构成正常经营买受人,应属不当。参见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3民终1575号民事判决书
[56]类似观点参见杨代雄主编:《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310页(吴宏乔主笔)。
[57]亦可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1页;张素华、李鸣捷:《〈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释论》,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7页。
[58]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1页。
[59]虽然《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2条第7项只是规定了“其他可以登记的动产和权利担保”,而并未明确规定让与担保可以在此系统中登记,但(非属于机动车、船舶、航空器、债券、基金份额、股权、知识产权的)普通动产和权利的让与担保在实操中可以在该系统中登记。
[60]对此参见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34页;龙俊、高曼琳:《动产抵押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十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47页;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7页。庄加园教授认为之所以此时不构成正常经营活动,有两个原因:一是担保权人并非真正的买受人;二是未向债务人支付对价。本文认为,第一个原因才是真正的原因,而第二个原因未必。提供担保是否会满足支付对价的标准,应分情况而定。如果是为了第三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原则上相当于无对价。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既存债务提供担保,也相当于无对价。如果是为了从他人获得融资而提供担保,并且也获得了融资,那其实是有“对价”(即取得融资)。
[61]林文学、杨永清、麻锦亮、吴光荣:《〈关于适用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司法》2021年第4期,第41页。
[62]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3页;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4页。认为如出卖人与买受人关系过于密切则本条不得适用的观点,参见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34页。但龙俊教授作为例证引用的美国判例Morey Machinery Co., Inc., v. Great Western Industrial Machinery Company, 507 F.2d 987 (5th Cir. 1975)中,法官认为“卖方和买方相互间的商业关系、对Great Western的快速销售以及该销售的条款,不能证明发生于正常经营活动中买方与卖方之间的正常交易(arm’s length transaction)。”从而,其实该判例并非一概认为具有关联关系的买方不会构成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而是认为如果构成正常交易则也可能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
[63]类似观点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3页;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4页;杨代雄主编:《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310页(吴宏乔主笔)。
[64]认为以货易货可否作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下的买卖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又并未分情况分析)的观点,参见刘智慧:《〈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134页。
[65]对此参见纪海龙:《动产担保权益延伸的合意路径》,载《现代法学》2022年第3期,第16页。
[66]不同的观点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98页;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21页;张素华、李鸣捷:《〈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释论》,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6页。在物权法时代,曾有判决认为以物易物也可以满足本条中的价款要素,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二终字第00041号民事判决书。在本案中,1号仓库中的粮食本属于抵押人且为抵押财产,3号仓库的粮食本属于第三人。后因该第三人租赁1号仓库,粮食挪库麻烦,双方便约定1号仓库的粮食和3号仓库的粮食置换,由此1号仓库的粮食转移给了第三人,3号仓库的粮食转移给了抵押人。但本案中的浮动抵押却不涉及3号仓库,从而在置换后3号仓库中因置换而属于抵押人的粮食并非抵押标的。如果认可此情形符合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的要件,则1号仓库中的抵押财产被通过置换转移给第三人后,其上的抵押权消灭,但抵押人没有获取新的资金,抵押权人也没有获取新的担保。
[67]与本文观点不同的是,按照美国UCC § 1-201(b)(9)对该法下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的定义,在UCC下以物易物(“by exchange of other property”)也可以满足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要求。但其实,美国法下,以物易物换得之物也会构成原担保物的收益,并自动顺延原始担保权的对抗和顺位效力,从而此时对于担保权人并无不利。
[68]2019年9月18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第45条的观点是,只有在抵债物交付给债权人(即本文此处正文中的“第三人”)时,实质上才会构成担保(《九民纪要》起草者认为此时构成让与担保);如抵债物未交付给债权人,此时以物抵债协议类似于签订买卖合同作为债务的担保,应参照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处理。对此参见最高人民法学民事审判第二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08页。
[69]在民法典前认为以物抵债也可以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错误判决,参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金商终字第664号民事判决书。
[70]按照美国UCC § 1-201(b)(9)对该法下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的定义,为了全部或部分地满足某金钱债权而取得货物的人(a person that acquires goods …… in total or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a money debt.),亦不构成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对此亦可参见Grant Gilmore, Security Interests in Personal Property, Volume II,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1965, p. 696. 国内学者认为以物抵债无法构成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下的买卖的观点,参见刘智慧:《〈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135页。认同以物抵债可构成本条中“合理价格”的观点,参见张素华、李鸣捷:《〈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释论》,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6页。该认同观点以债务重组中的以物抵债为例,说明有些情形的以物抵债会使债务人财务状况改善、责任财产增加,从而也有利于抵押权人。但其实债务重组情形的以物抵债仅仅是以物抵债的少数适例,以此情形为由论证以物抵债满足本条要件属于以偏概全;且债务重组时作为债权人的抵押权人也可能会参与,如计划被抵之债的债权人意图无负担地取得用以抵债之担保物,也可以与抵押权人谈判征求其同意,如此交易的确对于抵押权人有利,抵押权人也可能会同意之。
[71]参见龙俊、高曼琳:《动产抵押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十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30、46-47页。美国法下的判例参见General Electric Credit Corp. v. RA Heintz Const. Co., 302 F. Supp. 958 (D. Or. 1969)。
[72]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5页;高圣平、叶冬影:《民法典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的解释论》,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84页。
[73]当然,在善意取得制度中,无权处分人可能会对原所有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或负担不当得利返还的义务,无权处分人因无权处分所取得的对价越高,也就越能增加其责任财产,从而当然也更有利于实现原所有权人对其主张的救济措施。在无权处分人向原所有权人返还不当得利的情形,无权处分时对价的高低也可能会影响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的范围(参见[德]汉斯·约瑟夫·威灵:《德国不当得利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65-67页)。但这种有利,只是一种比较弱的意义上的有利。
[74]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98页;刘智慧:《〈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137;郭明瑞、房绍坤、张平华:《担保法》(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75]《物权法》时代,以购买价款过低难以解释从而不合理以及标的物并未实际交付为理由否定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的案例,参见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8民终673号民事判决书。
[76]对此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98页;程啸:《担保物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页。
[77]对此问题,DCFR并不要求价款已经被支付,其理由一是欧洲大多数国家在此均不要求价款已被支付;二是如要求价款已被支付,则只支付部分价款会导致问题非常复杂。对此参见von Bar/Clive (Hrsg), 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DCFR), Volume 6,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 2009, pp. 4880, 4830.
[78]以上几点理由参见纪海龙、张玉涛:《〈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2页。对于最后一个理由的不同意见认为,由于价款请求权的坏账风险以及执行上的麻烦,虽同为责任财产一部分,但相比于价款价款请求权对于抵押权人利益的保护力有不逮;参见张素华、李鸣捷:《〈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释论》,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5页。此意见有一定道理,但也忽略了价款到了债务人手里被挪用的风险(尤其是在其陷入财务危机时)。
[79]对此的分析参见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20页。该分析的前提是动产抵押情形担保权会自动延及至抵押财产的收益(对此参见庄加园:《动产担保物权的默示延伸》,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40-44页);但其实即便不支持动产抵押情形担保权自动延及至抵押财产的收益,而是需要担保权人实现在收益上设定担保权,例如设定应收账款质押或账户质押(对此观点参见纪海龙:《动产担保权益延伸的合意路径》,载《现代法学》2022年第3期,第5-12页),庄加园教授的分析依旧有意义。原因是,鉴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存在,存货上的担保权本就比较脆弱,所以在存货上设定动产抵押的抵押权人,如其足够理性和老道,本就应在抵押财产的收益上设定担保权(例如设定应收账款质押以及账户质押)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80]参见刘智慧:《〈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138页。
[81]相同观点参见徐涤宇、张家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26页;认为需要支付大部分价款才可满足此要求的观点,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98页。
[82]不同的意见参见张素华、李鸣捷:《〈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释论》,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6页。《物权法》时代将此认定为价款已支付的判决,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628号裁定书。
[83]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99页;刘智慧:《〈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140页。
[84]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99页;纪海龙、张玉涛:《〈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2页。
[85]参见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23页;孙宪忠、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4》,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53页(董学立执笔)。
[86]参见[美]E·艾伦·范斯沃斯:《美国合同法(原书第三版)》,葛云松、丁春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1页。
[87]逻辑上当然也可能采取另一种构造,即将本条中的“不得对抗”解释为只是发生抵押人与特定买受人间的相对效力,即在本例中,抵押人不得对抗甲并不意味着抵押(在对世意义上)被除去,只是意味着对于甲该抵押被除去。但这种构造过于复杂,也不足采。
[88]认为取得抵押财产应为取得抵押财产的所有权,但该所有权应通过交付转让给买受人的观点,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5页。
[89]《民法典物权编解释(一)》第17条第2款在解释动产善意取得情形善意的认定时点时,只是对现实交付、简易交付、返还请求权让与这三种情形作出了规定,而对于占有改定未予置喙,或可体现该司法解释的起草者对于占有改定形式无法支撑善意取得的态度。
[90]参见庄加园:《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再审视——基于权利外观学说的建构尝试》,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第1356页。
[91]参见纪海龙:《解构动产公示、公信原则》,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第712页。
[92]参见纪海龙:《解构动产公示、公信原则》,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第713页。
[93]相同观点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99页;刘智慧:《〈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142页;纪海龙、张玉涛:《〈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2页;徐涤宇、张家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26页。
[94]不同的观点参见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22页;高圣平、叶冬影:《民法典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的解释论》,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84页;刘竞元:《民法典动产担保的发展及其法律适用》,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60页;张素华、李鸣捷:《〈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释论》,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6页。美国UCC下虽不存在例如占有改定这样的术语,但美国法院通过“拟制占有(constructive possession)”这一构造实现了占有改定约定也可满足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规则的效果。按照UCC § 1-201(b)(9)对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的定义,“只有占有货物或有权根据第二编向出卖人收回货物的买受人才可能是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美国法院在一系列的判例中将此处的占有解释为也包括“拟制占有”(见本注释中所引的美国判例,又可参见Lopucki, Warren, Lawless, Secured Transactions, A Systems Approach, Ninth Edition, Wolters Kluwer, 2020, p.584;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2页)。按照美国法院对拟制占有的认定,“拟制占有是一个在多种情形下被使用的概念,基于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占有某物的权利或能力足以在没有实际占有的情形产生‘占有’的法律后果”(参见In re Havens Steel Co., 317 BR. 75, 88(Bankr. W. D. Mo. 2004))。“如果所有权人故意将动产(personal property)的实际占有(即直接的实际控制)交给他人,目的是让该他人为了所有权人或对于该财产实施某种行为,则存在所有权人对该动产的拟制占有。”(In re Western Iowa Limestone, Inc., 538 F. 3d 858, 867 (8th Cir. 2008))可见,从功能比较的角度看,美国法下的拟制占有和大陆法系的间接占有基本相同。而且在上述判例中,美国法院都是在认定标的物所有权已转移给买受人后确认了买受人(对于尚被出卖人实际占有之货物)的拟制占有。从而在这几个判例中对拟制占有的认定,实质上相当于在大陆法系下认定买受人基于占有改定而取得了所有权。
[95]此是比较法上的通行做法。对此参见UCC § 1-201(b)(9)、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第34条第4款、DCFR IX. - 6: 102, VIII. - 3:102. 关于DCFR下的买受人的善意要求,参见von Bar/Clive (Hrsg), 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DCFR), Volume 6,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 2009, p. 5605.
[96]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0页;庄加园:《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14页;纪海龙、张玉涛:《〈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3页;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52页;龙俊、高曼琳:《动产抵押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十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43页;孙宪忠、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4》,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153页(董学立执笔)。反对观点参见高圣平、叶冬影:《民法典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的解释论》,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84页;邹海林:《民法典上的动产抵押权规则体系解释论》,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5期,第35页;杨代雄主编:《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311页(吴宏乔主笔)。
[97]参见李莉:《浮动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限制规则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49页。
[98]参见钟维:《民法典编纂背景下我国浮动抵押制度的释评与完善》,《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235页。
[99]参见纪海龙、张玉涛:《〈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13页;刘智慧:《〈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144页;张素华、李鸣捷:《〈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释论》,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7页。
[100]参见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50页。
[101]认为如买受人是商人则负有查询登记之义务的观点,参见麻锦亮:《民法典·担保注释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662页。
[102]虽认为本条的适用不以买受人善意为要件但同时也认为限转或禁转约定被登记不妨碍本条适用的观点,参见高圣平、叶冬影:《民法典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的解释论》,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84页。
[103]类似的观点参见王利明:《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2-103页。
[104]参见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33页。
[105]See Robert H. Skilton,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under Article 9 of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Related Matters)," Wisconsin Law Review 1974, no. 1 (1974), p. 1.
[106]参见纪海龙:《世行营商环境调查背景下的中国动产担保交易法》,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2期,第41页;龙俊、高曼琳:《动产抵押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十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44页。
[107]参见庄加园:《动产担保物权的默示延伸》,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40-44页。
[108]参见纪海龙:《动产担保权益延伸的合意路径》,载《现代法学》2022年第3期,第5-12页。
[109]对此的讨论参见纪海龙:《动产担保权益延伸的合意路径》,载《现代法学》2022年第3期,第17页;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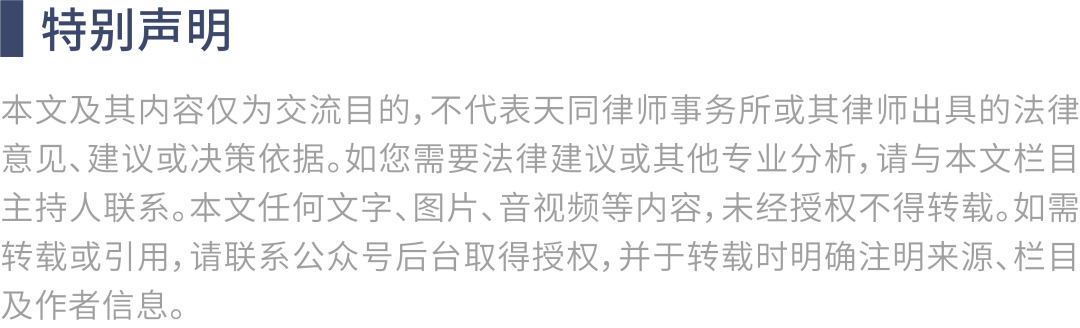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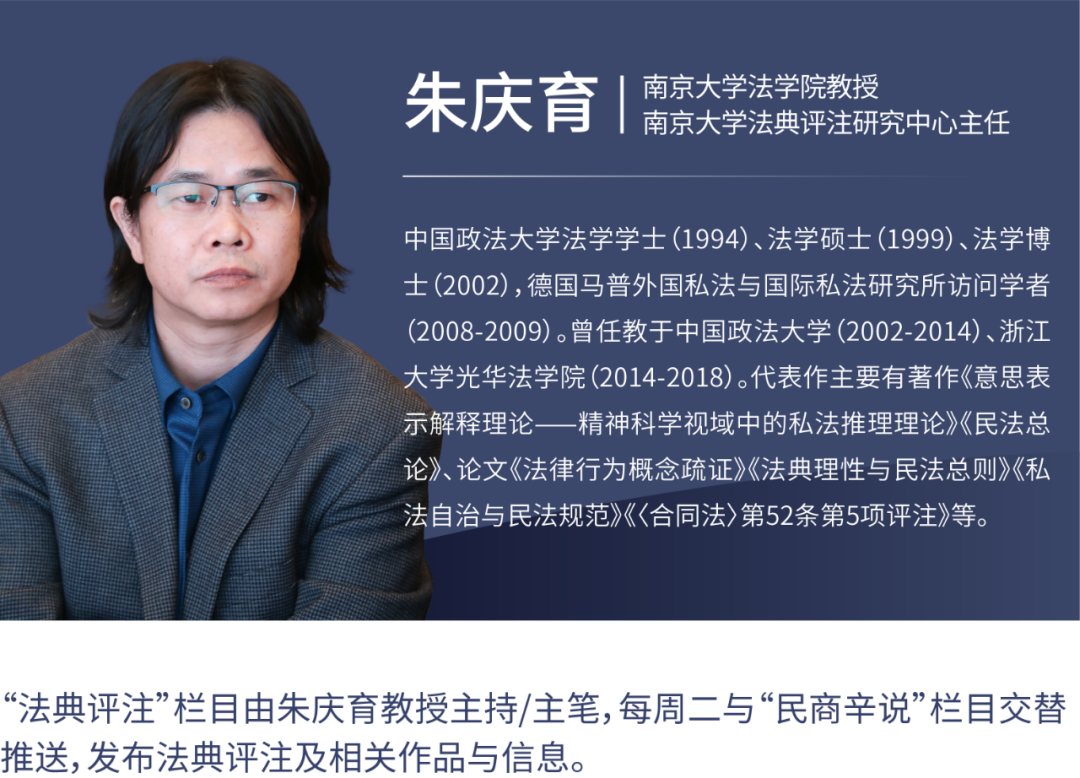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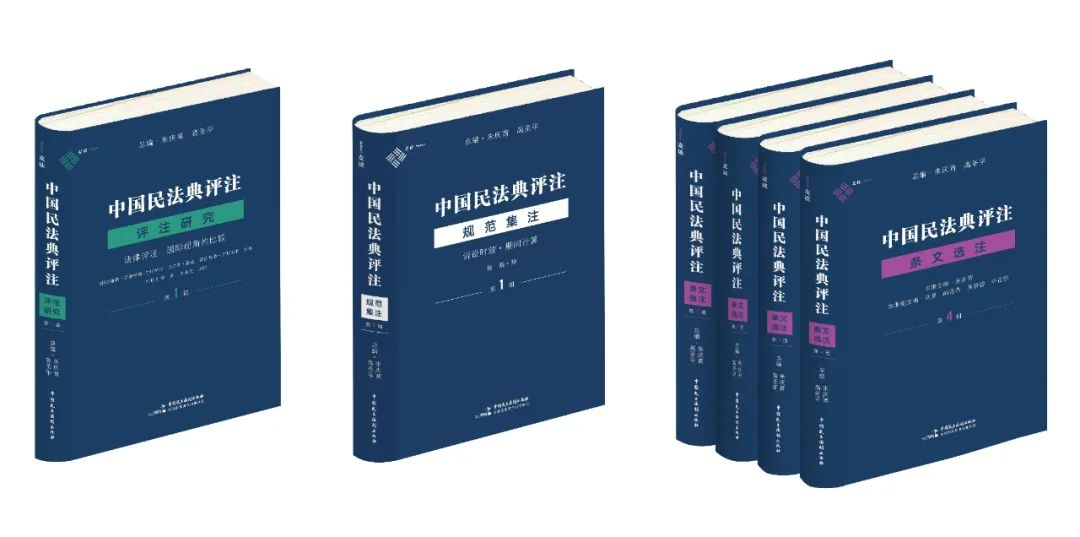
《中国民法典评注》已出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