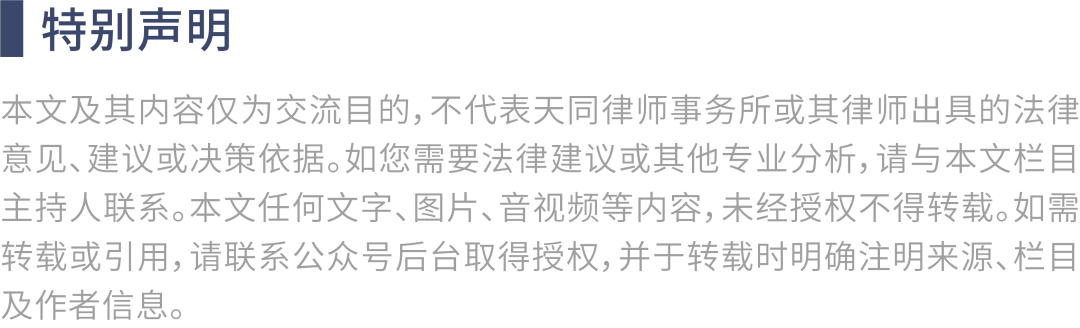文 / 李皓,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晋柠、陈樱娥、李逸梦、柴晨朝、李庚、刘俊宏,天同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
《九民纪要》将股权投资中对赌纠纷的必争之地由合同效力移转至合同履行,在股权回购或业绩补偿因组织法的资本规制而暂时无法实际履行时,投资者能否通过替代履行路径实现权利救济?例如,投资者主张解除投资合同,要求目标公司或相关主体返还投资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此时,若投资合同为股权转让合同,诉讼两造核心争议多为涉案合同能否解除,该类纠纷隶属传统合同法律规制范畴;若投资合同为增资合同,在前述典型争议的基础上,各方往往围绕合同解除后果展开论辩,这涉及公司法律与合同法律的协调并进问题。鉴于解除路径项下,增资合同相关争议基本覆盖股权转让合同相关争议,下文以增资合同为视角展开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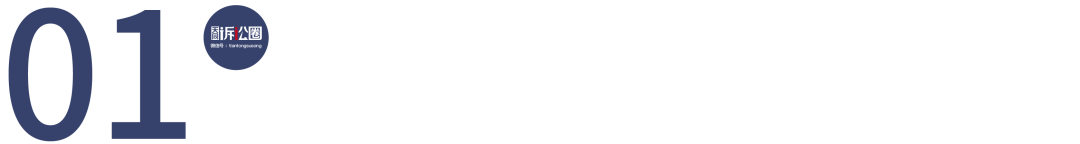
司法裁判趋势
为贴合实践趋势,本系列报告依托《九民纪要》出台后,京浙沪三个地区的股权投资退出纠纷相关裁判文书展开调研。经逐一研阅805篇裁判文书,我们选出261件相关案例。围绕合同能否解除、合同解除后果两个方面,主流裁判规则如下。
(一)合同能否解除
统计样本中,当事人均提出了解除投资合同的主张,支持合同解除案例的共有182件,占比约为70%,总体而言,鉴于投资合同的顺利履行高度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在当事人以司法途径诉请解除之际,案涉交易往往难以为继,基于此,在符合解除条件的的情况下,法院倾向支持解除合同诉请。
1.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时,法院综合衡量违约行为轻重、合同目的能否实现、资本维持原则影响等因素,原则上公司法相关规则不影响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
当事人主张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案例共有167件,得到法院支持的有108件。此类案件的裁判逻辑可概括为:首先,考察原告是否为适格主体,能否行使法定解除权。(2018)京04民初573号一案中,法院认为原告仅为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其未获显名的情况下,囿于股权投资合同的相对性,实际出资人并非适格主体;[1]在(2020)最高法民申1369号等案件中,在原告本身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法院不支持作为违约方的原告行使法定解除权。[2]其次,查明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若被告已经基本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或被告因行使法定抗辩权而拒绝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大多不支持原告解除合同的主张。[3]再次,探究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不少裁判观点提出,即使相关主体尚未完成股权工商登记手续,因原告已实际接管目标公司或原告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投资合同目的能够实现,进而驳回原告解除诉请。[4]最后,衡量资本维持原则对合同解除权的影响。多数法院区分合同解除权本身与合同解除法律后果,认为资本维持原则仅作用于后者,限制此类投资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即使目标公司尚未履行减资程序,原告亦可解除投资合同。只有1件案例以解除增资合同将导致公司减资后果为由否定原告诉讼[5]。此外,个别案例认为当事人行使约定解除权超过合理期间,相关合同解除权消灭。[6]
2.当事人行使约定解除权时,法院重点考察合同约定、解除情形,在违约行为轻微的情况下,法院倾向以司法介入方式限制解除权行使
当事人主张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案例共有88件,得到法院支持的有68件。法院不支持此类解除主张的原因包括:第一,投资合同并未约定合同解除权,当事人未能完成关于约定解除权合意的举证证明责任。[7]第二,虽然投资合同明确约定合同解除权,但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符合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8]第三,虽然约定解除权已成就,但因对方违约行为轻微或已补正,法院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深度、合同目标实现情况等,限制约定解除权的行使。[9]第四,个别案例中,法院亦认为当事人行使约定解除权超过合理期间,相关合同解除权消灭。[10]
3.在当事人对投资合同解除达成合意时,法院往往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
当事人主张合意解除并得到支持的案例共有6件。此类案例中,虽然双方就合同解除的违约原因及责任承担的主张不同,但不影响双方就解除合同这一事项本身达成一致,在此情况下,法院往往支持解除合同。[11]
(二)合同解除后果
以投资者与目标公司之间的紧密程度为区分标准,增资合同的履行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阶段一,签订合同;阶段二,实际行使股东权利;阶段三,签发出资证明或记载于股东名册;阶段四,完成工商登记。根据增资合同的不同履行阶段,法院对此类合同的解除后果处理不一。法院观点存在分歧,究其本质是对股权变动模式的不同认识。
1.阶段一裁判规则较为明确,合同签订后,投资者取得股东身份之前主张解除合同的,多数法院支持返还增资款项
司法实践中不乏各方当事人签订增资合同后,因投资者未能如期支付投资款项或因目标公司无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原因,一方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案例。[12]此时,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尚未变更,投资者亦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主流裁判观点认为投资者尚未取得股东身份,自然无涉组织法关于股权退出的规定,径行适用合同法律规定,判令目标公司返还增资款项。
2.阶段二、三、四的裁判规则存在一定分歧,各地法院对于投资者何时取得股东身份认识不一,在确认投资者取得股东身份后解除合同的,若目标公司尚未履行减资程序,多数法院不支持返还增资款项
阶段二、三、四的裁判规则取决于投资者何时取得股东身份这个前提问题,即股权变动模式。因我国现行法尚未明确股权变动模式,各地法院对此存有分歧,进而导致此类增资合同解除后果的处理亦不相同。
阶段二、三项下,一种观点认为投资者此时已经取得股东身份,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返还增资款项。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投资者股东身份虽然尚未得到工商登记确认,但在其已实际参与目标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记载于股东名册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投资者已经取得股东资格。依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股东一经出资入股,依法不得抽逃其出资,仅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减资。在目标公司尚未履行减资程序的情况下,投资者无法要求返还增资款项。[13]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时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尚未产生对外公示效力,可以直接要求目标公司返还增资款项。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以及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并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在投资者增资款项尚未办理工商登记时,目标公司债权人尚无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投资者解除合同后请求返还投资款,并不涉及因抽逃出资或不按法定程序减资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问题。[14]
阶段四项下,即目标公司业已完成工商登记,统计样本中全部裁判观点均认为,在目标公司没有履行减资程序的情况下,投资者不能要求返还增资款项。[15]其中,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1265号判决最具代表性,该案入选了全国法院系统2020年度优秀案例,法院认为增资合同虽解除,但未解除投资者的股东身份,此时增资合同解除的后果,实际上是处理投资者作为原增资股东的退出问题,投资者要求将其出资直接返还以“恢复原状”,实质上等同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任意抽回出资,将造成公司资产的不当减少,显然有违公司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原则,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债权人利益保护。
3.投资者关于目标公司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主张亦需受到资本维持原则规制
合同解除后,当事人除要求“恢复原状”外,还可以同时主张“赔偿损失”。例如,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1265号一案中,原告诉请解除增资合同,并要求各被告赔偿增资款本金等额损失。此时涉及的问题是目标公司赔偿损失是否受资本维持原则规制?投资者是否存在损失,如何确定投资者的损失?对此,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作法,多数法院认为赔偿损失系合同履行之替代责任,在目标公司因资本维持原则而陷入一时履行不能时,赔偿损失势必加剧亏损程度,实质等同合同履行,鉴此,投资者关于赔偿损失的诉请仍需接受资本维持原则的检验。此外,持此类裁判观点的法院进一步认为,增资合同解除后,投资者仍持有股东身份,无法证明其增资款项发生损失,即使目标公司资不抵债或陷入破产导致股权价值严重贬损,股权投资本是高风险高收益市场行为,该股权价值贬损损失也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16]少数法院认为,在目标公司无法回购股权的情况下,其基于未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支付违约金,并不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亦不必然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鉴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规范目的以及目标公司对于其一时给付不能具有可归责性,目标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17]
注释:
[1] 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573号案。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369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5232号案等。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491号、(2019)最高法民终1983号、(2019)最高法民申5743号案等。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5128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1民终7212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3民终2993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4民终507号案等。
[5]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终3281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民终4503号案等。
[6]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1民终10627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申869号、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4186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终15320号案等。
[8]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0)京01民终1840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15271号案等。
[9][9] 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6民终4607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3民申60号案等。
[10]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初231号案。
[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5310号、(2020)最高法民终501号、(2021)最高法民申296号、(2021)最高法民申1178号、(2021)最高法民申3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2民终7210号案。
[1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1178号、(2019)最高法民终1993号案等。
[13]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1073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申568号案等。
[1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1738号案。
[15]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1265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5622号、(2020)最高法民终223号案等。
[16]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1265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终549号案等。
[17]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495号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