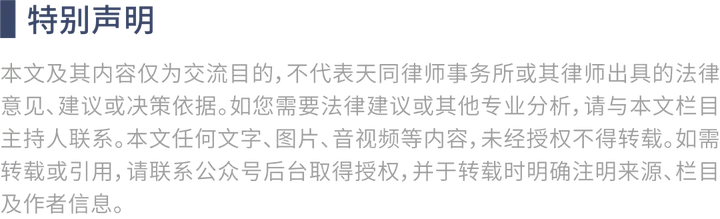文/朱华芳 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佑宁、郭萌、庄壮、叶一丁、陈芯宇、林晓欣 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继此前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概述》(点击阅读)、《2022年度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大数据分析》(点击阅读),《2022年度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主题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制度实践观察(上)》(点击阅读)后,本文作为主题一下篇,将重点讨论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特定争议可仲裁性的相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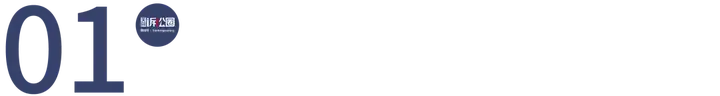
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院”)拟进一步明确仲裁协议在特定情形下的效力扩张问题,但部分问题仍存争议
(一)指导性案例认为,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仲裁协议约束
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是否应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仲裁协议约束,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点击阅读:《2021年度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主题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制度实践观察(下)》)。2022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198号认定:“实际施工人并非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的当事人,亦未与发包人、承包人订立有效仲裁协议,不应受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仲裁协议约束。”该案审查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依据,是仲裁合法性、正当性的基础,其集中体现了仲裁自愿原则和协议仲裁制度。”[1]
关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仲裁协议能否扩张适用于实际施工人的争议,实践中存在不同案型。一种案型系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提起诉讼,发包人以其与承包人存在仲裁协议为由主张案涉争议应提交仲裁机构。此种情形下法院否认仲裁协议扩张适用至实际施工人的主要理由包括:其一,实际施工人并非发包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故发包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实际施工人[最高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5747号];其二,在实际施工人无从知晓发包合同项下的仲裁协议时,否认仲裁协议扩张适用于实际施工人更契合保护弱者的政策考量。如新疆高院(2022)新民再187号裁定认为:“如认定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仲裁协议的约束,将……导致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享有的权利被实际阻断,与相关司法解释对实际施工人权利特殊保护的目的相悖。”
另一种案型系实际施工人主动依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但发包人主张其与承包人的仲裁协议不应适用于实际施工人。指导性案例198号即属于此种情形,该案中实际施工人主动对发包人申请仲裁,发包人先是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管辖异议未被支持,随后又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法院最终以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为由裁定撤销仲裁裁决。
不过,指导性案例198号能否完全平息既有争议,可能还有待观察。第一,有观点认为,如发包人明知实际施工人的存在,则不宜适用该案例规则。典型情形即资质挂靠,如发包人明知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企业名义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此时施工合同的实际主体系发包人和实际施工人,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均应受施工合同项下仲裁条款约束。[2]
第二,在实际施工人主动申请仲裁时,能否一概认为发包合同项下仲裁条款不应适用于实际施工人,理论上亦存在不同观点。首先,对主动申请仲裁的实际施工人而言,在司法实践中,主动依仲裁协议申请仲裁可被视为仲裁申请人对仲裁协议的默示认可。实际施工人依发包人与承包人仲裁协议主动申请仲裁,存在被认定为其同意受相应仲裁协议约束的空间。其次,对此时的仲裁被申请人发包人而言,有观点认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仲裁,表明其同意将该合同项下争议交由仲裁机构管辖,坚持仲裁不会减损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亦不超出发包人签订发包合同时对争议解决方式的正常预期。如发包人主张发包合同项下的仲裁协议系基于其与承包人之间的特殊信赖关系订立,应举证证明其订立仲裁协议时的主观状态。[3]
(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拟明确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时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问题
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是否应受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仲裁协议约束,以往司法实践存在较大争议(点击阅读:《2020年度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主题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制度实践观察》;《债务人与次债务人订立仲裁条款,债权人能否提起代位权诉讼?》)。从2022年度及近期司法实践来看,各地方法院对该问题仍未达成共识。一些法院认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受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仲裁协议约束[北京朝阳法院(2022)京0105民初23176号、上海静安法院(2022)沪0106民初6210号之一、山东胶州法院(2023)鲁0281民初895号之一],一些法院则持相反观点[山东济宁中院(2023)鲁08民辖终27号、天津三中院(2022)津03民辖终424号、广西桂林中院(2022)桂03民终3331号、辽宁营口中院(2022)辽08民辖终125号]。
对于上述问题,最高法院2022年11月4 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8条提出两种方案。方案一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的相对人以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约定了仲裁协议或者管辖协议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对该异议不予支持。但是,相对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对债务人申请仲裁,或者向管辖协议约定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主张代位权诉讼中止审理的,人民法院对该主张应予支持。”方案二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或者其相对人以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约定了仲裁协议或者管辖协议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同往年报告分析,我们倾向于赞同方案一。即原则上应认为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不受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仲裁协议约束,但若债务人及/或次债务人依其之间的仲裁协议就次债务本身申请仲裁,债务人及/或次债务人可申请中止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不过,若在任何条件下均允许债务人、次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期间另行申请仲裁,可能导致债务人、次债务人恶意利用仲裁协议拖延代位权诉讼。对此可考虑通过限制债务人及次债务人申请仲裁的时间节点、明确次债务仲裁案件不影响债权人对次债务人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等方式进一步保护债权人。[4]方案一对次债务人另行申请仲裁的时间作出限制,我们认为值得赞同。但关于次债务人另行申请仲裁的具体时间,理论上有观点认为,基于防止次债务人恶意拖延代位权诉讼等原因,次债务人应在代位权案首次开庭前或举证期限届满前另行申请仲裁。[5]
(三)关于仲裁协议对债权受让人的效力,司法实践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9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条的适用关系存在不同理解
《仲裁法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9条,债权受让人依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排除债权让与人与债务人的仲裁协议约束。但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条,债权受让人变更标的债权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需经债务人同意。
对于上述两条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关系,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仲裁法司法解释》效力位阶相同,且《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条规定的“管辖协议”广义上可包括仲裁协议,应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条已变更《仲裁法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故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条[北京高院(2020)京民申5310号、辽宁高院(2021)辽民申3390号、北京二中院(2019)京02民终12812号、山东青岛中院(2022)鲁02民辖终309号、浙江杭州中院(2021)浙01民终1411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条规定的“管辖协议”不包括仲裁协议,此时判断仲裁协议对债权受让人的效力仍应适用《仲裁法司法解释》第9条。我们倾向于认为,《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3条应优先适用。具体而言:
第一,“管辖协议”在文义上可包括仲裁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均有对仲裁制度的规定,不能认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所有规定均不能适用于仲裁制度。理论上虽有“主管”与“管辖”概念之分,但《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严格区分两概念,且“管辖”这一概念亦在仲裁程序中使用。在最高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335号、上海一中院(2017)沪01民辖终713号等案例中,法院均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条认定仲裁协议效力。
第二,基于债的同一性,债权受让人不应比让与人处于更优地位,且应避免因债权转让使债务人处境更为不利。[6]《民法典》第548条[7]规定的债务人可对让与人主张的抗辩,应同时包括程序性及实体性抗辩,其中程序性抗辩包括通过诉讼还是仲裁解决纠纷。仲裁协议与管辖协议本质上均系当事人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合同,认为二者应适用不同的变更规则,缺乏充分依据。
第三,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而言,债权转让无需债务人同意(即便存在禁止转让债权的约定,该等约定的对外效力亦受到较大限制),债务人在债权转让中对风险的控制能力较弱,但债权受让人却可预先调查并进行风险预防。基于债务人和受让人的风险控制能力比较,应倾斜保护债务人——未经债务人同意,债权让与人与受让人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及受让人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单方意思,不能影响到债务人利益。[8]此外,实践中《仲裁法司法解释》第9条易被债权让与人滥用于规避原合同的仲裁协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9条不利于保护债务人的正当权益。比较法上亦有观点认为,允许受让人可随意摆脱仲裁协议约束,将使得任何不想通过仲裁行使救济权利的当事人简单将债权转让即可实现其目的,仅以单方权利决定仲裁协议强制约束力的观点缺乏理论依据。[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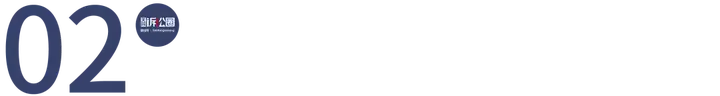
我国对一些争议的可仲裁性持逐渐放开态度,但对部分争议的可仲裁性,理论及司法实践仍存在争议
(一)通过仲裁解决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我国已开始有益尝试
中国证监会、司法部2021年10月15日发布的《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下称“《证券仲裁试点意见》”)提出,“支持、推动证券期货业务活跃的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开展试点,在依法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内部设立证券期货仲裁院(中心),适用专门的仲裁规则,专门处理我国资本市场产生的证券期货纠纷”。意见第四条明确,包括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在内的证券期货纠纷,可以适用仲裁方式解决。2021年7月发布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亦提出:“人民法院、证券监管部门,加强与调解、仲裁、公证、行政复议等程序衔接,不断完善纠纷化解联动衔接机制。”整体来看,我国对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及其他证券期货纠纷的仲裁持谨慎放开态度。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本质上属于侵权纠纷,在司法实践中,肯定与仲裁协议约定的实体合同有关的侵权纠纷具有可仲裁性已渐成主流,但部分法院曾以虚假陈述纠纷属于侵权纠纷为由,认定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辖终210号]。从2022年及近期司法实践来看,认为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应适用当事人之间的有效仲裁协议,有望成为主流观点[最高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391号,北京高院(2022)京民终74号、(2022)京民终415号,山东高院(2022)鲁民终872号,北京金融法院(2021)京74民初394号,辽宁沈阳(2022)辽01民初2128号]。在实践中,当事人的仲裁合意可能体现在三类文件中:一是当事人在发行阶段签署的文件,包括股票发行中的《股票招股说明书》《认购协议书》及债券发行中的《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二是公司章程;三是资本市场自律组织会员章程,如根据《证券仲裁试点意见》第六条,证券期货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期货行业协会等资本市场自律组织的会员可在章程中规定针对会员之间证券期货业务纠纷的仲裁条款。[10]
不过,在虚假陈述纠纷中如何判断当事人是否存在仲裁合意、当事人仲裁协议的效力范围,裁判思路有待进一步统一。如在浙江高院(2020)浙民辖终33号、(2019)浙民辖终160号案中,法院认为案涉《募集说明书》虽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其仅明确对发行人及投资者有法律约束力,不能约束债券承销商。而在北京金融法院(2021)京74民初524号案中,法院认为债券承销商、评级机构关于虚假陈述责任承担的声明也构成《募集说明书》的一部分,债券承销商、评级机构应受《募集说明书》仲裁条款约束。
(二)从近期司法实践动向来看,最高法院对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似持否定意见
我们曾在2020年报告中讨论过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最高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46~47号裁定、(2019)最高法民申6242号裁定曾对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作出不同认定,前者认为纵向垄断协议纠纷不属于法定可仲裁范围,而后者认为原告关于确认被告实施并请求其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诉请,属于案涉仲裁协议约定的 “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的范畴(点击阅读:2020年度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主题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制度实践观察)。
从近期司法实践动向来看,最高法院对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似持否定意见。2022年11月18日最高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第3条规定,“原告依据反垄断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以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已有仲裁协议为由提出异议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受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但是,人民法院受理后经审查发现不属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可以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在2022年2月审结的(2021)最高法知民终924号案中,最高法院提出,反垄断法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质,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当事人之间的仲裁条款不能当然排除法院对反垄断纠纷的管辖权。最高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276号裁定亦持相似观点。
典型案例
某科技公司与某智能装备公司、某自动化控制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最高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276号]
原告某科技公司起诉请求确认某智能装备公司、某自动化控制公司实施了排除、限制竞争的纵向垄断行为,且原告与某智能装备公司、某自动化控制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某智能装备公司、某自动化控制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原告诉请及理由均针对当事人签订的《经销协议》《和解协议》项下权利义务关系,体现了合同的相对性,未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仍应适用《经销协议》《和解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最高法院二审认为:因合同签订、履行引发的确认垄断行为或同时请求损害赔偿之诉与因一般合同关系引发的合同之诉或侵权之诉的竞合不同。在一般合同关系中,即便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该侵权行通常亦系合同约定的履行行为,原则上不会超出合同范围。但在因合同签订、履行引发的垄断纠纷中,受害人与垄断行为人订立的合同仅系垄断行为人实施垄断行为的载体或工具,合同中涉及垄断的部分才是侵权行为的本源和侵害发生的根源,对垄断行为的认定与处理超出了受害人与垄断行为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能成为排除法院管辖垄断协议纠纷的当然依据,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我们倾向于认为,《反垄断法》虽具有一定公法属性,但部分反垄断纠纷可能主要涉及私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财产权益,此时不宜仅以《反垄断法》本身的公法属性一概排除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11]此外,从兼顾公共政策标准与支持仲裁的角度考虑,即便认为涉及反垄断纠纷的仲裁裁决可能有损公共利益,仍可通过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解决。如通过事后审查可阻却仲裁裁决执行,则一般不宜事先排除仲裁的进行。[12]在比较法上,更多国家和地区亦开始认可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13]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并未平息关于行政协议认定标准及其可仲裁性的争议,有理论观点认为行政协议项下争议并非完全不具有可仲裁性
在2019年、2020年观察报告中,我们讨论了行政协议的认定及其可仲裁性问题(点击阅读:《2020年度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主题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制度实践观察》;点击阅读:《2019年度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主题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制度实践观察》)。2019年11月的 发布《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二条对“行政协议”作出界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协议约定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条款无效”。但该司法解释发布后,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行政协议之概念及可仲裁性的分歧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对“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不完全统一。最高法院及部分地方法院曾提出:“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最大的区别在于,行政机关以公权力行使者的身份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仍然是一种行政权行使方式……行政协议包括四个要素,一是主体要素,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二是目的要素,必须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目标;三是内容要素,协议内容必须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意思要素,即协议双方当事人必须协议一致。”[14]但即便存在前述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协议的认定仍可能出现不同把握尺度。如部分法院认为PPP协议属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并非行政协议[浙江绍兴中院(2020)浙06民特4号],但部分法院认定PPP协议“具备民事合同的特点,也体现了行政协议的特征,不宜仲裁解决”[上海一中院(2020)沪01民特265号之一]。有实务人士认为,并非所有PPP协议均属于行政协议,应根据PPP协议的具体内容、当事人争议事项及仲裁请求具体判断。具体而言,应主要审查合同当事人是否处于平等地位、合同设立的权利义务是否属于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争议事项及仲裁请求是否针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15]
第二,对行政协议项下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有不同认识。事实上,行政协议的产生背景即决定其天然具有民行交织的特点。《行政协议案件规定》之所以未实现定纷止争,不排除是因为理论与司法实践对行政协议本身的可仲裁性仍有不同见解,为尽量支持仲裁,但又囿于《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的规定,只能对“行政协议”本身作限缩解释。在理论讨论层面,近年来不断有观点提出应修订《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相关规定,重新审视仲裁协议可仲裁性。如有观点认为,《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界定的行政协议类型并不妥当,某些领域的行政协议可被认定为民事合同并具有可仲裁性。[16]还有观点认为,过分强调行政协议的行政性而忽略其民事性,进而将行政协议纠纷完全排除在仲裁范围外,不利于行政协议纠纷的及时高效解决。[17]
我们亦倾向于认为,《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六条一刀切地否认行政协议项下争议具有可仲裁性,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如前述,行政协议天然兼具行政性和民事性,一份行政协议中可能同时存在一般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和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条款,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可能同时扮演不同角色。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指出,在PPP项目中,合同双方应“平等协商”,政府同时是“社会资本的‘合作者’和PPP项目的‘监管者’”。将行政协议与民事协议的明确区分作为判断争议可仲裁性的前置程序,缺乏清晰的操作标准。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称“《仲裁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的不能仲裁的争议系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理论上认为行政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的主要原因是,行政权行使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其合法性只能由国家自身通过法定机关和程序推翻。行政争议的审查重点系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仲裁无法达成该目标。[18]但是,考虑到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及权利义务条款的复杂性,行政协议项下争议并不完全等同于前述《仲裁法》规定的“行政争议”。实践中已有部分法院注意到行政协议项下争议可能具有的不同属性。如最高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40号裁定认为,不能仅凭一方主体的特定身份认定争议法律关系的实际性质,而需结合争议的具体内容及所针对行为的性质具体判断案涉争议是否与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相关。安徽六安中院(2019)皖15民特3号裁定持相似观点。部分实务人士亦提出,无需将识别合同整体性质作为判断PPP合同法律适用的必经程序,应直接从具体争议性质的角度认定特定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19]
最后,从立法趋势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下称“《仲裁法修订草案》”)规定的可仲裁纠纷范围有所扩张,第2条删去现行《仲裁法》关于可仲裁纠纷发生在 “平等主体”之间的要求,有望为行政协议项下争议通过仲裁解决进一步提供法律依据。国务院2017年7月21日发布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第40条亦规定“因合作项目协议履行发生的争议,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比较法经验来看,在不违反公法强制性原则的前提下,为防止行政主体滥用优势地位、尊重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在行政协议领域支持选择仲裁机制是最新立法趋势。[20]
关于行政协议项下争议适用仲裁的具体范围,可能需结合不同合同的具体内容进行认定。有观点认为,一般而言纯粹平等协商条款可直接仲裁,纯粹行政职权条款则排除仲裁,行政优益权条款应由当事人具体分析——如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与行政机关职权冲突,当事人可约定就行政优益权条款适用仲裁。[21]但亦有观点认为,如某行政协议项下纠纷交织着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且在技术上无法分割处理,则不宜通过仲裁解决。[22]
(四)认可部分公司内部争议具有可仲裁性有望成为趋势
1. 更多观点开始认为,部分公司内部争议具有可仲裁性
公司内部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近年讨论愈盛。[23]《仲裁法修订草案》第二十五条拟规定股东/有限合伙人派生诉讼中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对与公司有关纠纷之可仲裁性争议作出正面回应。[24]部分实务人士认为,将部分公司内部争议提交仲裁,有利于专业高效地解决纠纷,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25]从各国仲裁实践发展来看,承认部分公司内部争议的可仲裁性是大势所趋。[26]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开始认可公司章程中仲裁条款的效力[北京四中院(2022)京04民初507号、江苏南京中院(2020)苏01民终2723号、四川成都中院(2019)川01民终15274号、山东济南中院(2017)鲁01民初1913号、重庆五中院(2017)渝05民终2262号]。不过亦有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故公司决议效力之诉、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公司清算之诉均属于法院专属管辖范围,不具有可仲裁性[北京四中院(2022)京04民特945号]。
我们倾向于认为,一概否认公司内部争议的可仲裁性缺乏充分依据。一方面,公司内部争议不属于《仲裁法》第三条规定的不能仲裁的争议;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第27条仅系相应纠纷由法院主管时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则,并不当然排除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相应纠纷的权利。公司内部争议虽会对外部债权人产生影响,但可尝试通过完善仲裁第三人制度、仲裁机构设置特殊仲裁规则等方式解决前述问题。如仲裁机构可考虑对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设置特殊仲裁规则,保障利益相关方的程序参与权及对仲裁案件程序进展的知情权,还可通过合并仲裁将同一决议所涉争议在同一案件中处理,避免出现相互抵触的裁决结果。[27]
不过,在原则上认可公司内部争议本身具有可仲裁性的基础上,股东间仲裁协议的效力范围可能还需进一步讨论。例如,若公司章程仅有股东签署,章程中的仲裁条款能否约束公司本身,可能存在争议。
2. 司法实践主流观点认为,公司解散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
整体来看,司法实践对公司解散纠纷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多持否定意见。最高法院在《关于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09)CIETACBJ裁决(0355)号裁决案的请示的复函》([2011]民四他字第13号)、(2013)浙商外终字第91号裁定、(2015)民提字第89号裁定、(2016)最高法民再202号裁定中的观点一以贯之,均认为仲裁不能处理公司本身的解散清算问题。大部分地方法院亦持相似观点[上海高院(2021)沪民辖终11号、河北高院(2020)豫民辖终115号、陕西宝鸡中院(2013)宝市中法民三初字1号]。不过,相关裁判文书多未详细论述具体理由,而是直接以“现行法律并未赋予仲裁机构解散公司的裁决权”为由,认定即便公司章程中存在仲裁条款,该等仲裁条款亦不能适用于公司解散纠纷。
理论上否定公司解散纠纷具有可仲裁性的主要理由是仲裁程序的基本特点与公司解散涉及第三方利益、公共政策的特点无法匹配。具体而言:第一,公司解散可能影响多方利益,但仲裁保密性将导致第三方无法了解仲裁进程及结果,利益可能受损。第二,仲裁合意是仲裁制度的基石,通过仲裁处理公司解散纠纷可能导致职工、消费者等其他利害关系人无法参与仲裁程序并表达诉求。[28]部分法院曾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公司解散涉及主体众多,具有一定公共性,须通过法定程序才能进行,并非当事人可任意处分的事项[陕西宝鸡中院(2013)宝市中法民三初字1号]。
但近年来有理论观点认为,仲裁机构有权作出解散公司的裁决;公司解散纠纷并非《仲裁法》规定的不可仲裁的纠纷,请求解散公司不等同于启动公司清算程序,第三人利益保护可在仲裁裁决执行、公司清算程序中处理。[29]
注释:
[1] 湖南岳阳中院(2018)湘06民特1号。
[2] 参见《浅谈最高法院第198号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载“民商法指南”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fHqj8TZbZkBreyBMaWDMqg,2023年6月1日最后访问。
[3] 参见陈忠谦:《合同相对性突破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辩证关系研究——兼谈其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适用》,载《仲裁研究》2019年底1期,第1-9页。
[4] 参见《债务人与次债务人订立仲裁条款, 债权人能否提起代位权诉讼?》,载“天同诉讼圈”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G9ZmM6uelAv70w9KD3Zq3A,2023年5月15日最后访问。
[5] 参见郁琳:《代位权诉讼司法管辖与仲裁管辖冲突的解决》,载《商事审判指导》2013年第4辑(总第3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46~54页。
[6] 参见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53 页。
[7] 《民法典》第548条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8] 参见朱虎:《债权转让中对债务人的延续性保护》,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146-162页。
[9] Gary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outh Hollan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4, p. 1469.转引自姚宇:《仲裁协议随债权转让的价值平衡方法——对债务人保护的再审视》,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载2022年第3期,第282-293页。
[10] 参见何海锋等:《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可仲裁性问题的实务研究》,载“天同诉讼圈”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nriDpxzhQIEbkWdVBUEYlA?search_click_id=366968173286076339-1684280616708-9564887044,2023年5月17日最后访问。
[11] 参见《2020年度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主题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制度实践观察》,载“天同诉讼圈”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qG4QouxRLMhGvjrLjpfQdQ,2023年5月17日最后访问。
[12] 参见曹志勋:《论可仲裁性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美国反垄断仲裁经验的考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56-65页。
[13] 参见张艾清:《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研究——兼论欧美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6-153页;曹志勋:《论可仲裁性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美国反垄断仲裁经验的考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56-65页;邓志松:《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实务研究:欧盟与英国》,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0年第4期,第148-160页。
[1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新闻发布会》,载最高法院官方网站,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7571.html;《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国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2019-2021)》,载“北京四中院”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vCXe6O5r86k5kyAWx3R81A,2023年6月1日最后访问。
[15] 周显峰:《PPP协议与行政协议的关系及可仲裁性》,载“商法CBLJ”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7soNWBRXkEnqlS2KjduP3Q,2023年5月16日最后访问。
[16] 参见谢鸿飞、高壮:《行政协议的类型重塑及其可仲裁性》,载“商法CBLJ”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vE1HOb1koxYQnOJRCnj72Q,2023年5月16日最后访问。
[17] 参见于鹏:《行政协议纠纷适用仲裁研究》,载《清华法学》2022年第5期,第55-71页。
[18] 参见余凌云:《行政协议能否仲裁?》,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84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19] 参见《论PPP合同的可仲裁性》,载“通商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6fuq4FwpPFtto7TWR8-1Fg,2023年5月16日最后访问。
[20] 参见徐琳:《论法国行政合同纠纷的可仲裁性》,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99-108页;于鹏:《行政协议纠纷适用仲裁研究》,载《清华法学》2022年第5期,第55-71页;姜波、叶树理:《行政协议争议仲裁问题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9-120页。
[21] 参见于鹏:《行政协议纠纷适用仲裁研究》,载《清华法学》2022年第5期,第55-71页。
[22] 参见余凌云:《行政协议能否仲裁?》,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84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23] 目前比较系统的讨论可参见张子学:《公司法纠纷可仲裁性初步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47-62页、第206-207页;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姚宏敏 “几类公司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讲座综述,载“东方律师”网,https://www.lawyers.org.cn/info/921544e2f83a49888d5c57fb8241d6cf;李谧:《公司内部争议的可仲裁性》,载“商法CBLJ”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ou8LWci8w3IPfQyEnyZ8g,2023年5月16日最后访问。
[24] 参见《2021年度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主题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制度实践观察(上)》,载“天同诉讼圈”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w_FsgjHfDFxjjYV82X0jtA,2023年5月16日最后访问。
[25] 参见李谧:《公司内部争议的可仲裁性》,载“商法CBLJ”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ou8LWci8w3IPfQyEnyZ8g,2023年5月16日最后访问。
[26] 参见张子学:《公司法纠纷可仲裁性初步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47-62页、第206-207页。
[27] 参见《2021年度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实践观察报告——主题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制度实践观察(上)》,载“天同诉讼圈”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w_FsgjHfDFxjjYV82X0jtA,2023年5月16日最后访问。
[28] 参见王利香:《公司解散纠纷的可仲裁性研究——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解散纠纷为中心》,载《北京仲裁》2019年第4期,第94-116页。
[29] 参见王利香:《公司解散纠纷的可仲裁性研究——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解散纠纷为中心》,载《北京仲裁》2019年第4期,第94-116页;张子学:《股东压制与公司强制解散争议中的可仲裁性问题》,载《商法界论集》2019年第1期,第69-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