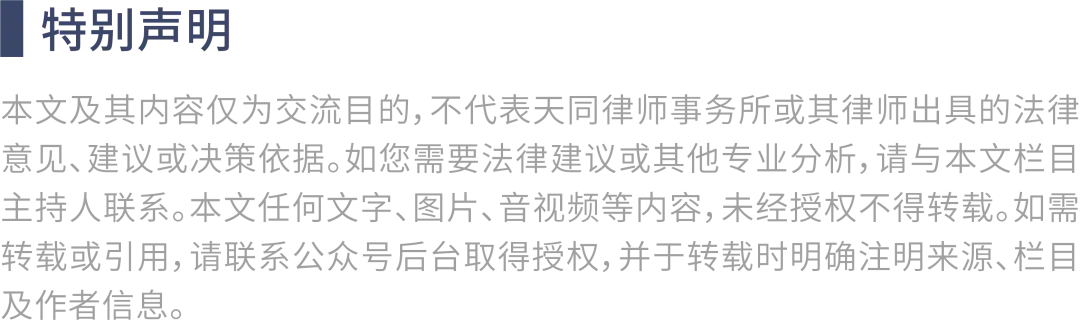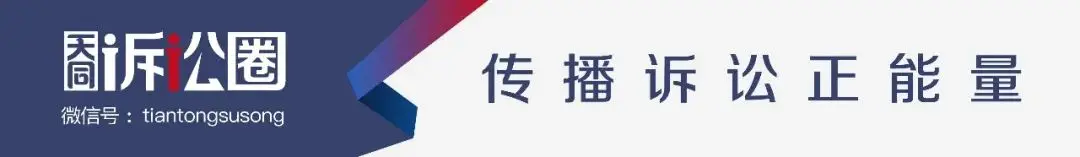
文 / WongPartnership LLP[1]: 合伙人Koh Swee Yen, Senior Counsel[2]; 合伙人Joel Quek[3]; 高级律师Charles Tian[4]
翻译:高泽欣 天同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
在最近发生的“新加坡亚化集团和西北化工公司诉中国政府案”[1](“AsiaPhos 诉中国案”)中,仲裁庭就中国与新加坡于1985年11月21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新双边投资协定》”)项下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裁决。仲裁庭多数意见认为,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不包括申请人的间接征收诉请,也不能因为《中新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条款而扩大被申请人同意仲裁的适用范围。但是,少数意见(Dissenting Opinion)对此持有不同观点。最终,仲裁庭基于多数意见,以超出管辖范围为由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
点评
AsiaPhos诉中国一案是投资仲裁领域关于仲裁同意范围最新的一起案例,本案涉及对《中新双边投资协定》中争议解决条款的解读。针对《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3条第3款中的“关于由征收、国有化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其他措施发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应对该条款进行限缩性解释,只有在确定征收(或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已经发生,投资者与征收国就应得的补偿金额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投资者才能根据条约诉诸仲裁。然而,投资者通常主张对该条款作扩张性解释,即仲裁庭有权先判断是否存在征收(或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然后再处理应支付的补偿数额问题。
在 AsiaPhos诉中国一案中,仲裁庭根据1969年5月23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维也纳公约》”)第31条规定的条约解释原则,对《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3条第3款的字面含义以及条款的背景进行了广泛探讨。值得关注的是,仲裁庭的多数意见与既往判例中倾向于扩张解释该条款的意见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仲裁条款包含“岔路口条款(fork-in-the-road provision)”[2]的情况下]。经仔细研究仲裁庭(包括反对意见在内)在裁决中的说理意见,我们发现,仲裁庭就《维也纳公约》第31条的解释存在着一些细微而关键的差异,这个差异使得本案最终采取了限缩解释,而反对意见以及过往其他一些裁决, 例如世能投资有限公司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案[3]( “世能诉老挝案”,关于《中国-老挝双边投资协定》的新加坡上诉法院案件),香港居民谢业深诉秘鲁共和国案[4]( “谢业深诉秘鲁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关于《中国-秘鲁双边投资协定》的仲裁案件)等案件则采取了扩张解释。因此,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投资者角度,在选择关于潜在投资索赔的法律策略时,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些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AsiaPhos诉中国一案中,多数意见裁决给了申请人两个选择:向仲裁地法院挑战仲裁裁决效力,或(在诉讼时效期内)向中国法院提起关于违反《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的诉讼。
本文将分析AsiaPhos诉中国一案的仲裁裁决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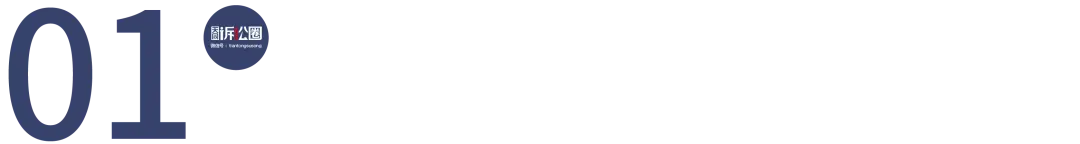
背景
本案申请人为新加坡亚化集团有限公司(AsiaPhos)和西北化工公司(Norwest Chemicals Pte Ltd)(两者合称“申请人”),二者均是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公司。被申请人是中国政府。申请人通过其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持有两座磷酸盐矿山的采矿和勘探许可证,并使用从上述两座矿山开采的磷酸盐矿生产黄磷。此外,AsiaPhos还通过持股一家中国公司间接持有一处重晶石矿的勘探许可证和勘探权。这三座矿山和工厂位于中国四川省绵竹市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
2016年和2017年,被申请人在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设立了一家大熊猫国家公园,制定并通过了一项禁止在该地区采矿的新政策。据申请人称,这一新政策导致三座矿山在2017年被强制关停,其采矿权也因而不复存在。基于此,申请人对中国政府提起了投资仲裁,主张被申请人违反了《中新双边投资协定》,具体而言:(a)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资采取了非法的、其效果相当于征收的措施,违反了《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6条;(b)被申请人未给予申请人的投资以公正和平等的待遇,违反了《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3条第2款(c)被申请人未给予申请人的投资和收益以充分的保护及安全的投资环境,违反了《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4条和第3条第2款;及(d)被申请人在申请人探矿和采矿许可有效期内禁止申请人勘探和采矿,关停矿区,违背了其对申请人投资所作出的承诺,违反了《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5条和第4条。
申请人主张,根据《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3条第3款,仲裁庭对征收措施问题(即前述(a)项主张)享有管辖权,而《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4条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该条款目的是确保一国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的保障效果上等同于向其他国家外国投资者所提供的保障)也适用于解决投资争议的条款,故仲裁庭对申请人上述所有请求均具有管辖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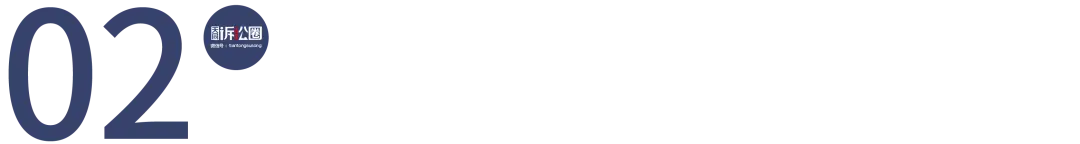
仲裁庭裁决
由于本案争议涉及对《中新双边投资协定》多个条款的理解,为便于参考,本文将相关规定罗列如下:
第4条最惠国条款
除第5条、第6条和第11条外,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根据第2条规定允许在其领土内的投资或收益所给予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第三国国民和公司的投资或收益的待遇。
第6条征收
一、缔约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措施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其它措施,除非这种措施是为法律所准许的目的、是在非歧视性基础上、是根据其法律并伴有补偿,该补偿应能有效的实现,并不得无故的迟延。该补偿应受缔约一方法律的制约,应是在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其他措施前一刻的价值。补偿应可以自由兑换和转移。
二、征收、国有化的措施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其它措施的合法性,应受影响的国民或公司的要求,可由采取措施的缔约一方的有关法院以其法律规定的形式进行审查。
...
第13条投资争议
一、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争议应尽量由当事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果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当事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第6条关于由征收、国有化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其他措施发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有关的国民或公司在诉诸本条第1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可将争议提交由双方设立的国际仲裁庭。
如果有关的国民或公司诉诸了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程序,则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一)《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3条第3款项下被申请人同意仲裁的范围
如前所述,仲裁庭依据《维也纳公约》第31条[5](经第32[6]条补充)对《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3条第3款进行了解释,该解释路径本身并无争议。
首先,仲裁庭评估了《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3条第3款的通常含义。针对该条款中的“关于(involving)”一词,申请人认为,根据“关于”一词在多个词典中的释义,可以将其定义为“包括”、“要求”或“包含”、“作为必要部分”,如果《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的缔约方意图缩小仲裁同意的范围,他们本可以使用诸如“限于(limited to)”、“由于(over)”或“有关于(concerning)”这样的表述。对此,多数意见认为“关于”一词在本案中的含义是中立且非决定性的,没有接受申请人所提出的 “关于”一词具有包容性含义的观点。
也就是说,多数意见同意“世能诉老挝案” 和“中国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政府案”(“黑龙江国际等诉蒙古案”[7],涉及《中蒙双边投资协定》)、的裁决意见,即,“关于”一词既可作广义解释,也可作狭义解释,重点是对“补偿款额(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一词的理解。如果要将“关于”解释成具有包容性的含义,即只要赔偿问题是争议内容的一部分,就允许仲裁,那么就没必要再加入 “款额(the amount of)”一词加以限制。
然而,少数意见对这一解释方式提出批评。持异议意见的仲裁员的理由是,多数意见没有分析“关于”一词的词义,仅仅是照搬了“黑龙江国际等诉蒙古案”的裁决意见。另外,多数仲裁员在关注“数额”的词义的同时,拒绝确定“关于”的词义,这是一种循环推理——如果“关于”这个词本来就是包容性的,那么“关于征收赔偿金数额的纠纷”这个句子里包含了“数额”的问题就是无关紧要的。少数意见进一步指出,多数意见未回应其他将“关于”一词解释为“仅限于”而非“包括”的裁决意见(参见“世能诉老挝案”裁决书)。
第二,多数意见进一步分析了《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3条第3款下仲裁同意的范围,重点关注了《中新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两个特定内容,即第6条关于征收的实质性条款,以及第13条第3款第二句的岔路口条款。多数意见认为,根据《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6条第2款,缔约方默认关于征收措施合法性问题的审查程序和关于争议措施所产生的补偿额的后续审查程序是相分离的。结合对第6条第2款的该等理解,多数意见认为第13条第3款中仲裁同意的范围仅指关于补偿款额的程序。
第三,多数意见未采纳申请人的主张,即《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6条第2款和第13条第3款中使用的“可由”一词(与强制性的“应当”不同)意味着投资者在审查征收措施的发生及/或合法性时可以选择国际仲裁而非国内法院。“可由”一词仅意味着投资者可以选择不将该等争议提交任何机关处理。在少数意见看来,多数意见的解释并未真正给投资者提供选择;唯一能使第6条第2款有效的解释是,投资者能够选择是将征收合法性的争议提交国内法院还是提交其他争议解决机关(即第13条第3款项下的国际仲裁庭)加以解决。
关于“岔路口”条款,申请人指出,如果接受被申请人对第13条第3款的解释,诉诸中国国内法院要求就征收的合法性作出裁定的行为将触发“岔路口”条款的适用,从而阻止申请人就补偿金额的任何后续争议诉诸国际仲裁,那么仲裁条款将被架空。但是,多数意见不接受这一主张。首先,考虑岔路口条款在第13条第3款中的位置,该款的第一句规定了第13条第2款这一一般条款的例外,也就是“补偿款额的争议”。因此,紧随其后的岔路口条款仅适用于第13条第3款第一句所指的情况。据此,仲裁庭认为(根据中国法律),就补偿款额问题,投资者可以另行于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所以,只要投资者在国内法院仅就征收措施本身提起争议,而不要求国内法院裁决补偿额问题,就不会触发岔路口条款。
多数意见进而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情景,如果国家向投资者支付了一定数额的补偿款,而投资者请求国内法院裁决征收因补偿款额不足而不具合法性,该裁决也不会触发岔路口条款。作为确定征收合法性的一部分,国内法院将依请求确定是否足额支付补偿款额;然而,这与确定非法征收应支付的具体赔偿数额是不同的,即使国内法院已经做出关于未足额支付补偿款额的事实认定,仲裁庭仍可根据《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3条第3款做出相关认定。对此,少数意见提出质疑。由于《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6条第2款提及“征收措施的合法性”,对这一争议做出裁决之前必须确定政府是否已支付了符合第6条要求的补偿款额。因此,少数意见认为,多数意见错误地想将征收事实与补偿款额问题分开处理,并企图通过提出一种假设情景来为这个站不住脚的论点辩解,但这种假设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引发更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能诉老挝案”和“谢业深诉秘鲁案”在内的多个涉及岔路口条款的案件中,少数意见是获得支持的。特别是在 “世能诉老挝案”中,新加坡上诉法院论述道:“首先,如果案件的唯一争议是赔偿款额问题,那么将何种问题提交给国内法院是不明确的。而如果国家将赔偿款额问题提交给了国内法院,随后又将相同问题提交仲裁,仲裁该如何处理也是不清楚的”;此外,“东道国只需否认其采取了征收行为,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仲裁”,因为这将“迫使投资者诉诸国内法院,禁止投资者在仲裁中主张权利”,并“将得出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即投资者实际上永远不可能提起仲裁”。
然而,并非所有涉及岔路口条款的案件都持相同观点,中国黑龙江仲裁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只有当争议确实限于宣布征收的补偿款额,且对征收的发生没有争议时,仲裁才能适用”,且“与产生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的措施相比,正式宣布征收的情况更为罕见……仲裁庭认为如果一项仲裁条款涵盖了一整个争议类别,就可以不失公允地判断该条款缺乏实际效力”。
多数意见认为,其已经仔细考虑了当事人所援引的裁决,例如 “世能诉老挝案”和“谢业深诉秘鲁案”的裁决。然而,这些裁决涉及的是岔路口条款的范围或者是与《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6条第2款相类似规定的范围,但并不同时涉及这两个问题。尤其是 “世能诉老挝案”案和“谢业深诉秘鲁案”案的条约并没有类似于《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6条第2款这样的规定。此外,这些裁决是一种循环推理,它们依赖于岔路口条款来确定仲裁条款的范围,而岔路口条款的范围又必然与仲裁条款的范围相同。
多数意见之所以没有重点讨论岔路口条款,似乎是因为在将第13条第3款与岔路口条款结合解释之前,仲裁庭先根据该条款所含词语的通常含义、第13条仲裁条款的结构以及第6条的上下文,对第13条第3款作出了解释。相比之下,对于“世能诉老挝案”的新加坡上诉法院和“谢业深诉秘鲁案”的仲裁庭而言,岔路口条款及其效力似乎意义更重大,因为对岔路口条款的审查是对相关仲裁条款整体解释过程的一部分。
多数意见在处理岔路口条款时,考虑了投资者在中国法院依据中国法提出赔偿款额问题是否合适,这也有待商榷。可能引发的问题是,《中新双边投资协定》项下的征收问题是否应由国际法而非国内法确定。此外,在确定这一问题时可诉诸东道国的国内法,这意味着条约中的岔路口条款的效力可能因东道国的身份而改变,而东道国的身份又可能影响仲裁同意的范围。
尽管最终结论相反,多数仲裁员和反对意见都认为没有必要根据《维也纳公约》第32条援用《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的目的、宗旨以及缔约背景(例如政治制度和中国法律的状况),因为根据《维也纳公约》第31条的解释原则就已经足以能对《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第13条第3款作出解释。
(二)被申请人主张通过最惠国条款来扩大仲裁同意范围
多数意见赞同“普拉马财团有限公司诉保加利亚案”[8],“欧美投资银行诉斯洛伐克共和国案”[9]和,和“Vladimir Berschader 等诉俄罗斯联邦案”[10]等投资仲裁案件中的裁决观点,即,通过最惠国条款对仲裁条款进行扩张的前提是双方一开始就明确无歧义地表明最惠国待遇条款具有这种效果。
因此,多数意见认为,《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的仲裁同意范围并未因第4条最惠国条款而扩大。从字面含义看,第4条的措辞并未明确扩张仲裁条款的同意范围。多数意见驳回了申请人靠“待遇”一词来证明《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的当事人有意将最惠国待遇条款应用于仲裁条款的同意范围,这主要是因为《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的第13条第3款中的仲裁同意范围是各方经过仔细协商后达成的。
少数意见赞同多数意见的看法,即,第13条第3款(该条款中的仲裁范围是经过各方仔细协商的)为解释最惠国待遇条款提供了相关背景,但认为多数意见没有对最惠国条款的通常含义,尤其是“待遇”一词加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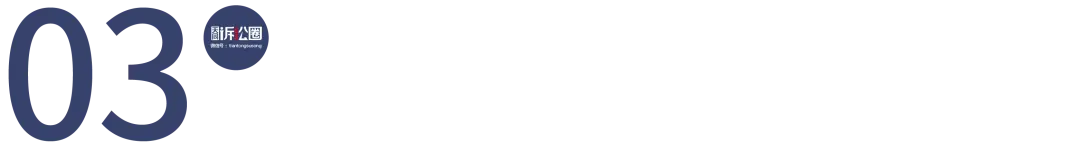
总结
AsiaPhos 诉中国案是将《中新双边投资协定》中仲裁同意的范围局限于仅涉及补偿款额,且仲裁条款含有岔路口条款的裁决之一。类似于《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的仲裁条款出现在与中国相关的约41个“第一代”双边投资条约中[11]。因此,这一新的司法判例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外国投资产生重大影响。鉴于此类条约中仲裁同意的范围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还应谨慎地考虑向国内法院或国际仲裁提出诉请的可行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1] 总部设于新加坡的WongPartnership LLP是新加坡的市场领军者和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WongPartnership LLP拥有60名成员的仲裁团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参与了亚洲地区一些最重要的仲裁案件,以及几乎所有被提交至新加坡法院的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仲裁纠纷,并记录了新加坡律师事务所在ICSID仲裁中的首次胜诉。
[2] Koh Swee Yen, Senior Counsel 是WongPartnership LLP国际仲裁业务部的负责人以及商业和企业纠纷部的合伙人。在新加坡,Senior Counsel(资深大律师)的头衔通常授予给具有顶尖出庭辩护能力,良好职业操守及专业能力的律师。
[3] Joel Quek是WongPartnership LLP商业和企业纠纷部的合伙人。
[4] Charles Tian是WongPartnership LLP国际仲裁业务部的高级律师以及注册外国律师。
注释:
[1] AsiaPhos Limited and Norwest Chemicals Pte Limite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 ADM/21/1
[2] “岔路口”条款(fork-in-the-road provision):一种常见于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条款。该条款要求投资者在提起争端时在国内法院诉讼和国际仲裁之间做出选择。一旦投资者选择了其中一种途径,他们将无法再转向另一种途径寻求救济。换句话说,投资者在选择一条道路后,将无法返回选择另一条道路。因此得名“岔路口”条款。这种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解决同一争端时出现重复诉讼。
[3] Sanum Investments Ltd v Government of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2016]5 SLR 536 (Sanum (CA)),WongPartnership LLP成功代表投资者Sanum Investments Ltd在新加坡上诉法院胜诉。
[4] Tza Yap Shum v The Republic of Peru, ICSID Case No. ARB/07/6 (Tza)
[5] 《维也纳公约》第31条 解释之通则
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
二、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
(a) 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
(b) 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
三、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a) 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
(b) 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
(c) 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四、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
[6] 《维也纳公约》第32条 解释之补充资料
为证实由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依第三十一条作解释而:
(a) 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
(b) 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
[7] China Heilongjiang Int’l Econ. & Technical Coop. Corp. and others v Mongolia, PCA Case No. 2010-20, Award, 30 June 2017 (China Heilongjiang)
[8] Plama Consortium Limited v Republic of Bulgaria, ICSID Case No. ARB/03/24,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8 February 2005
[9] European American Investment Bank AG (Austria) v The Slovak Republic, PCA Case No.2010-17, Award on Jurisdiction,22 October 2012
[10] Vladimir Berschader and Moï se Berschader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CC Case No.080/2004, Award,21 April 2006
[11] 参见 Li Yuwen& Cheng Bian, China’s Stance on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Reform Options,载《荷兰国际法评论》67,503-551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