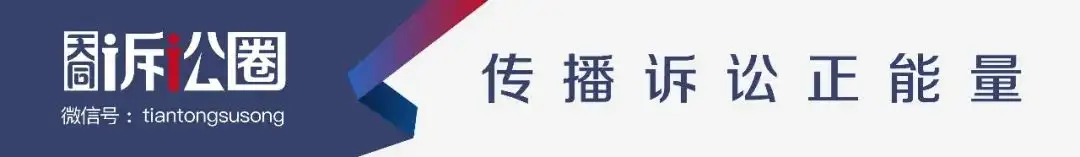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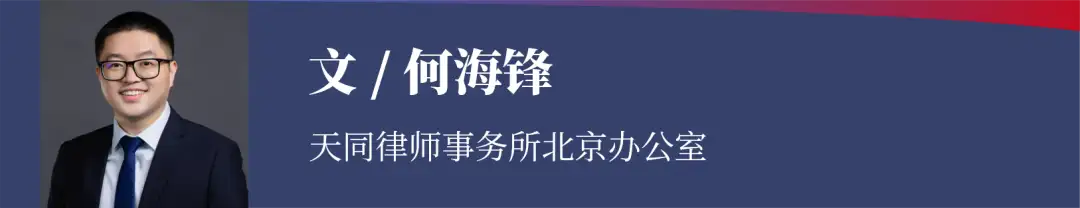
关于专栏
2022年6月,我的新书《证券法通识》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主要面向广大投资者和企业家,也面向企业法务和律师,定位于“让证券法成为通识”。在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把证券法写成通识太难了,结果也不尽如人意。而且,对于证券法这样一个总是跟随市场变化而调整的法律来说,书出来就已经过时了——今天的注册制,早已经不同于2020年的注册制;今天的证券交易所,也早已不是2020年那个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今年年初修订的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让证券诉讼的整个格局都为之一变。因此,几乎在新书出版的同时,我就启动了这本书的修订工作。而具体的修订方式,我就打算以“证券法通识”专栏的方式进行——按照《证券法通识》所确定的逻辑框架,结合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案例和影响证券市场的大事件来重述证券法通识,化整为零,细水长流弥补这一版书的不足。我也希望通过这个专栏跟更多的读者交流探讨。以书会友,不亦乐乎。
我的邮箱:hehaifeng@tiantonglaw.com
微信号是heislawy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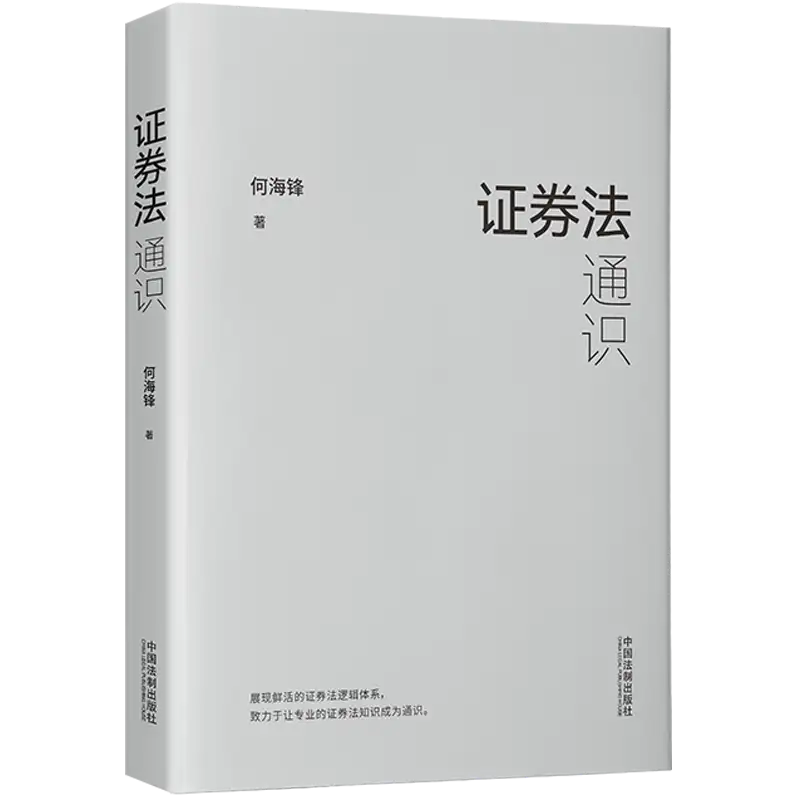
这是“证券法通识”专栏的第15篇文章。证券公开发行并上市后,就进入到了证券交易市场。证券法从两大方面对证券交易进行规范,一是从正面建立证券市场的基本交易规则;二是从反面明确证券市场禁止交易的行为。
证券公开发行并上市后,就进入到了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市场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有买的就有卖的,有亏的就有赚的。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是证券市场最基本的道理,也是投资者必须接受的逻辑,但前提一定是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市场上违反“三公”原则的交易,对投资者来说无异于掠夺。被“割韭菜”是投资者最悲凉的自嘲。那么,到底谁在“割韭菜”?证券交易又要遵循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件人民法院依法惩处证券、期货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涉及证券交易的有5件。在这些案例中,我们能看到在证券市场每天起起伏伏的价格变化后面“手举镰刀的人们”。
1. 唐某博等操纵证券市场案——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
2012年5月至2013年1月,唐某博伙同唐某子、唐某琦,利用实际控制的账户组,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撤单或大额申报、撤单,影响股票交易价格与交易量,并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其间,先后利用控制账户组大额撤回申报买入“华资实业”“京投银泰”股票,撤回买入量分别占各股票当日总申报买入量的50%以上,撤回申报额为0.9亿余元至3.5亿余元;撤回申报卖出“银基发展”股票,撤回卖出量占该股票当日总申报卖出量的50%以上,撤回申报额1.1亿余元,并通过实施与虚假申报相反的交易行为,违法所得共计2581.21万余元。
2. 周某伟内幕交易案——证券交易所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周某伟,原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副总监。
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周某伟利用其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总监助理的职务便利,使用自己的工作账号和密码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系统》,浏览并获取上市公司提交审核的有关业绩增长、分红、重大合同等利好信息后,用办公室外网电脑,登录其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并买入相关股票15只,买入总金额共计852万余元,卖出总金额871万余元,非法获利17万余元。
3. 顾某安内幕交易案——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从事内幕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北京某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聪网)的法定代表人郭某与上海某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联)董事长朱某红就上海某联收购北京某行锐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行锐景)有关“中关村在线”网站优质资产进行商议并达成初步意向,后又进行了多次磋商。2016年2月25日,上海某联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同年4月27日,上海某联发布公告,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知某锐景100%股权。郭某作为上述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于2015年底至2016年1月初,将“上海某联拟收购慧聪网优质资产”等内幕信息泄露给顾某安。2016年1月至2月,顾某安通过潘某梅证券账户买入上海某联股票18余万股,成交金额766万余元,股票卖出后非法获利126万余元。
4. 陈某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情节特别严重。
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江苏某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源电器)进行重组事宜。2014年4月1日某源电器股票停牌,同年9月10日东源电器公告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薛某年(时任某通智汇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系某源电器重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2013年11月中旬至2014年3月31日,陈某啸多次联络、接触薛某年,并使用本人证券账户共买入某源电器股票1022万余股,成交金额6919万余元。2014年9月19日和24日,陈某啸将某源电器股票全部抛售,非法获利1.03亿余元。在前述某源电器重组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陈某啸还将该信息泄露给同事明某、石某,明某买入某源电器股票2900股,在股票停牌之前卖出,亏损2983.26元;某勇买入某源电器247100股,成交金额167万余元,在股票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276万余元。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安徽某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东股份)进行重组事宜。薛某年为某东股份重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2014年9月20日,陈某啸在合肥徐同泰酒店宴请薛荣年等人时,获知某东股份和浙江某家家居合作的内幕信息,并于2014年9月22日、25日、26日买入某东股份239万余股,成交金额2673万余元。2014年9月29日,某东股份股票停牌。2015年2月6日某东股份复牌,陈某啸于复牌当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某东股份股票全部卖出,亏损4万余元。在某东股份重组的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陈某啸将该信息泄露给明某、石某,明某买入某东股份8万余股,成交金额99万余元,在股票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208万余元;石某买入某东股份11万股,成交金额121万余元,在股票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214万余元。
5. 齐某、乔某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齐某,原系某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兼证券投资业务总部总经理。乔某平(齐某的丈夫),原系某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瞿溪路证券营业部督导。2009年2月至2015年4月,某蕾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方证券)利用其负责某方证券自营的11001和11002资金账户管理和股票投资决策的职务便利,掌握了上述账户股票投资决策、股票名称、交易时点、交易价格、交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伙同乔某平利用控制的证券账户,先于、同期于或稍晚于齐某管理的某方证券上述自营资金账户买卖“永新股份”“三爱富”“金地集团”等相同股票197只,成交金额累计达6.35亿余元,非法获利累计1657万余元。从上面5个案例可以看出,在证券市场上“割韭菜”的,可能是其他的投资者,也可能是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可能是发行人和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和离得近的其他人,几乎是“人人得而割之”。而“割韭菜”的方式更是变化多端、潜踪匿影,作为零和博弈的另一方,投资者对于被收割基本是无感的。然而,“割韭菜”的存在,损害的不光是投资者的利益,更会伤害市场本身的公信力。因此,证券法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证券交易市场本质上是一个资本要素市场。现代经济的要素市场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技术等市场。对于任何市场而言,流动性和活跃度都是第一位的,成交量都是首要的评价指标。对于证券市场而言,流动性更加重要,因为证券最大的吸引力和独特性就在于,除了可以通过公开发行的“一级市场”,面向不特定或多数的投资者进行公开发行,大规模募集资金外,公开发行的证券还可以在公开交易的“二级市场”上再次进行自主、有序、高效的流通买卖。证券法不仅要管好一级市场,把好公司选出来,把股票成功发行出去,还要管好二级市场的秩序,让股票高质量地流动起来,防止投资者被“割韭菜”。
证券法从两大方面对二级市场的证券交易进行规范,一是从正面建立证券市场的基本交易规则,规定证券交易的场所、交易方式、交易形式、收费方式等;二是从反面明确证券市场禁止交易的行为。对于交易规则,证券法更多提的是原则性的要求,划出的是证券交易的“底线”,具体规则授权证券监管机构和交易所进行规定。明确禁止的交易行为及法律责任是证券法的重点,证券法从交易对象、交易时间、交易方式等角度划出了证券交易的“红线”,规定了16种禁止的交易行为。对于触及红线的行为,证券法都规定了明确而严厉的法律责任。
这16种禁止的交易行为,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特殊主体的禁止交易行为,只有特殊的主体才能从事这些行为,类似刑法上的“身份犯”,因此可以称为“身份行为”。对于身份行为,禁止的理由是主体身份的特殊性。这些主体因为职务、对发行人的控制力等原因,占据天然的或后天的、一时的或持续的信息优势,允许他们交易,或者在特定时段,或者以特定方式交易,将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证券市场的不公平公正。
这些主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金融市场上的专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这些专门机构包括证券交易场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等;第二类是上市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或者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的股东等;第三类是国资企业等特殊主体。另一类是一般的禁止交易行为,与具体的身份无关,任何人都可以从事这些行为,类似刑法上的“非身份犯”,因此也可以称为“非身份行为”。当然,刑法上还有“不真正身份犯”的概念,即将特殊身份仅作为刑罚加重或者减轻事由的犯罪。[1]证券法上也规定了一个“不真正身份行为”——内幕交易行为。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从事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

可以说,证券法所规定的底线与红线,就是投资者的“平安符”。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在证券交易环节的证券法规范,除非有特殊限制,原则上既适用于股票、公司债券、存托凭证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也适用于上市交易的政府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二是完整的证券交易还包括以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为目的的证券交易,即上市公司的收购,证券法对上市公司收购的基本规则和禁止的行为进行了专章规定。
注释:
[1]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