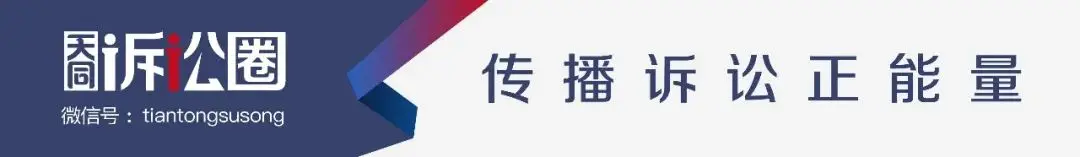

“自述”
“新班子改组刚刚完成,原来的那个方案现在肯定是落地不了了,得继续追加投资,否则项目可能要叫停。”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项目我就亏大发了,前期投进去那些资金都是借的,现在这个用资成本您也知道,这样相当于让我倾家荡产,《补充协议》这个字我签不了。”
“李总,你考虑考虑吧,项目能干下去,将来转手大家都解套不说,还能净赚一部分,如果不继续,已经投进去的可能都打了水漂了。”
“那这个决定我也做不了,得让股东们讨论。资金太大了,当初可是大家一块想办法融的资。”
“公司是你说了算吧,章子也在你那里,资金的问题后面大家再想办法,李总这点魄力都没有?”
“这……那让我想想。”
2003年8月那几份协议、原审笔录以及客户描述所呈现的内容逐步映像在脑海,我在稿纸上将这些零碎的事实连同各方交易的状况逐一画出来,存在矛盾和仍有疑问的地方打上一个大大的“?”,接着,又一头扎进垒如叹息之墙般的案卷里。在天同,四年来我所做的就是代入案件材料和各方陈述所构建的“过去”,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先尽可能还原基础事实,再从中寻找可供救济的法律路径。逐条逐字的解剖条款之外,更需要理解每一个行业的惯例,每一项交易的逻辑,甚至每一个主体的不同身份立场,以便判断那些繁复字眼、往来文件背后的形成原因。
我把这个过程形象地称呼为“潜水”,一口气扎进去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寻找没有被客户或其他同仁发掘的通途、小径。刚开始可能偶尔呛水,随着经验的积累,慢慢也可以游弋其中,甚至沉迷于细枝末节字里行间,串联起一个陌生主体数十年间的真实经历。所以,真正吸引我的,是不断回溯纷争的事实,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不同主体长达十余年乃至数十年的不同经历,落在数千页的协议、函件上,我们用数百个小时的深度阅读,去努力重塑那些不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再去抽丝剥茧对比证据事实、法律要件,从中找到可能的路径一到或有的路径十。有个科技宅的老哥总给我安利VR科技,我其实很想告诉他,哥们,你知道我们每天干的都是人脑VR的黑科技吗?这种听起来就很Cyberpunk的事情,难道不比打卡上下班、交流摸鱼心得更让年轻人热血沸腾吗?
“伙伴”
当我在说出上面那一段话的时候,姣姐正在暴风吸入三合一油泼面,她翻了我一个大大的白眼。
“来来来,我的大律师,收收您那点沸腾的开水,先说说,书记员这周不给阅卷,咱咋办。人家结案季忙得飞起,你这个时候要跑去要用手机一页页扫描,一共二十六本,相当于他得陪咱干耗一整天,你看要不你去给他来套口腔体操,看看能不能让他也沸腾一个。”“这个嘛……”我开玩笑道,“以您的美貌与智慧肯定早就有主意了,需要小管做点什么您就吩咐。”——不出意外喜提一个更大的白眼。这个棕红色长发,和我同一天面试、同一天入职、相互搭档超过1275天的女博士兼好兄弟。在德令哈的砂石漫漫里,在橘子洲的阴雨霏霏下,在塔尔寺的梵音袅袅中,她可以在涉他合同和幼儿退烧的话题之间无缝横跳,以至于当我在跟别人讨论比例因果关系的域外立法例和去某个山洼洼里跟老乡拉家常的情境中,都会感慨一句“要是姣姐在就好了”。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前后,差不多八九个月我俩接触案件和新签案件都稳坐分所老幺,那时候看着别的小伙伴抱着新案子的材料就像领到奖金一样,我俩心里百般滋味难成一言。在天同,每一个案件都弥足珍贵,想要获得更多的倚重,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为表着实可怜,我俩甚至轮番在合伙人处哭惨,但冷静下来反思,必是自己在作业上有所欠缺,才导致合伙人不能放心把案子交给我俩。于是在相互鼓励之外,我俩开始逐份翻看过去案件的材料,思考其中更抽象的法律问题,同时查阅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献材料,动笔撰稿,形成一篇又一篇的小文,虽然大多都只是作为我俩自己的学习笔记,并没有投稿刊发,但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在史律大力支持下,我撰写完成研究构想,顺利申请到民商法方向的在职博士。熬过“十月案荒”后,终于领到梦寐以求的案件时,有天我俩坐在办公室外的长廊,看着斜阳西暇一襟晚照,颇有种历尽劫难闯出黎明的味道。伙伴。是来到天同后最为珍贵的,无论我和姣姐,还是最早筑基期就加入的威威、亮亮、芳姐,或者从帝都红圈回归的健哥、天一等等,在溯流而上、会当击水的进路,所有人都在相互托付、互为支柱。
入夏的时节,西安办公室经历了设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员调整。傍晚伏案倏尔抬头,晚霞铺满几张空落落的桌面,仿佛还能看到那些熟悉的身影,几年时光陪伴,让所有人更像是一个班级、一支队伍,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烙着天同西安办公室的印记。

“豪门”
蒋律告别仪式的时候,立刻动身赶去了现场,那一整天我俩都是懵懵的,脑海一直闪回19年我俩在四合院里请教案子,蒋律招呼我们赶紧去吃饭的样子。姣姐扒着碗热气腾腾的饭说,寰寰你看,这么大的城市里,有一处可以落脚的院子和一个到点喊你吃饭的“家长”,真的很幸福。对我们这群分所时期才加入的小伙伴而言,蒋律在我们心中更多的是仰望和追随。蒋律之于天同,可能如弗爵爷之于老特拉福德,禅师之于芝加哥王朝,他开宗创派式的壮举,缔造了律师行业大竞技场里的一支豪门,也点燃了无数怀揣梦想年轻人心中的火焰。
也许身在一线城市的法学生们体验并不切身,在红圈、魔圈扎堆的北上广深,从名校毕业后可能就握有一张入场券,但对于像西安这样诸多还在拼尽全力迎头赶上的城市,客观上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各地确实都有一流的诉讼团队、一流的金牌律师,但对于法学院的不少学生而言,都或多或少地对口口相传的“红圈”、大腕怀揣情节。天同设立分所给了大家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很多在外求学、回家工作的学生。如果要问这里有什么不同于别处,我想最大的一点是:这儿可以大胆地谈梦想,也让你相信那不只是黄粱一梦,所要做的只是努力再努力地踮起脚尖伸手去抓。当然,作为别人眼中的幸运儿,我们背负着的愿景与压力有多重,可能也只有自己清楚其中滋味。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这是西安办公室阅览室里挂着的一幅墨宝,每次抬头都会心里一紧,像一道符咒一样时刻提示着我们,在这个低容错率甚至零容错率的地方,任何一点小小的差池都可能失去一次代理、一件案子,甚至一位客户。以前我并不清楚,总觉得这些合伙人吹毛求疵,大搞职场PUA,直到慢慢地开始接触客户、独立思考代理,才明白这样的要求是在天同模式下的必然选择。当然,这也倒逼着每一个人在专业领域上更进一步。
我有时会回学校跟自己的导师吹牛,说虽然不是全日制,但是在天同看的文献绝对不比在校的师兄师姐们少,末了还不忘加一句“天同的学习氛围可不比咱民商法研究所差”。
这句话可没有夸张演绎的水分。
——史律经常周末带着孩子到办公室一起学习,晓成主任总关心“最近怎么没人晚上留下来读书了”,大家桌上的民指商指配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以及几乎人手一本的《合同法总论(第四版)》和《民法总论》,让人恍惚间好像在高校研究所,而不是在一家律所,不过想想也是,大家案件汇报PPT的最后一页一直写着那句“我们对做一家平淡无奇的律师事务所毫无兴趣”。
“故事的下一章”
关于天同故事的撰稿,当晓成主任找到我的时候,不能说是意料之中,只能说是一脸错愕。我必然不是西安办公室里最优秀的那几位,也不是从毛坯房时代就入驻的开荒成员,甚至在我刚入职21天的时候,合伙人就直接断言我干不过仨月。思来想去,也许在合伙人眼里我是个不错的侧写师傅,以文字代替颜料,绘一幅眼中的我们和我们扎根的一方天地。
2019年南湖飘着大雪的时候,我在诉讼圈刊发《一味知冬,一案识天同》,那时候我刚刚执业一年。本部老天同的大咖们这样评价我们这群分所的小年轻—— “眼里有光,身上有股劲儿”。转眼之间,又过去三个夏天,在来到天同的第四年头里,无论是四合院里的金玉满堂,还是曲江池畔的杨柳依依,都镌刻为自己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我不敢确保自己可以一直呆在这里不被淘汰,也曾经不自觉地去想如果有天不得不离开时,到底应该如何面对,可惜一直没有想出什么答案。因此,从2020年后,我一直在桌角立着一块倒计时牌,看着卡片一页页翻过,数字一次次减小,自己越来越清楚也许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挥霍,那种少年不惧岁月长的肆意愈发遥远。
也许每个人生活的每段路上都会有不同的际遇,结识不同的伙伴,没准八十岁的时候回望,这可能只是漫漫人生中的一个章节,但为什么这段故事会如此悠长久不释怀,也许,是我们没有再一段青春里的四年、八年和二十年。
“对于咱们,路还有很长,态度上必须是谦逊的,不过思想还是得支棱起来,雄心壮志是得有的,起码得奔一个ALB吧。”对着今年刚刚校招入职的95后们,我装腔作势地吹嘘一番。
天同,20岁正是鲜衣怒马的年纪,能做的和想做的都是无穷无尽。敢想、敢拼,没有什么是一定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恰恰给现在的我们留以最大的遐想空间与开拓氛围。
现在每天醒来,我都会盯着镜子,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被锉去那股锐意。四年里,我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只要眼里还有光,身上还有劲儿,只要还有带着勇气憧憬,敢于谈梦的年轻人,天同的故事,就会一直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