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本文所要叙述的,并非天同作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常规追求,而是一名“别有用心”的合作者与旁观者眼中的另类追求。
(二)
正郁兄在新近发表的大作“中国法典评注中的律师——为何、由何与如何”中说:“天同加入法典评注,或有歆羡,或有怀疑,或论无私,或论无谓。常有问及,律师为何参与法典评注?”我想,各种态度中,怀疑或无谓论者应属多数。实际上,天同捐资设立法典评注基金的这三年来,我也一直在心里问:天同为什么参与法典评注?总是隐隐有种把天同拖下水的歉疚感。
让我略感宽慰的是,这不是天同第一次“不务正业”。除以“专注于复杂重大商事争议解决”享誉业内外,天同另外一项备受关注的工作是天同码。当年蒋勇律师慧眼独具,将陈枝辉律师延揽旗下,俾使专心制作天同码,以为“天同知识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七年,陈律师几乎以一人之力,终以四千余万字、含两万余条裁判规则的“天同十八部”竟其全功。

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何对大规模的系统性案例编纂如此执着,并将其提升至“知识管理体系”的高度?一家律师事务所,又为何要致力于建立“知识管理体系”?蒋律师的解释是,“它对天同律师有价值,就必然对所有法律职业者有价值。也只有所有法律职业者都共享同样的知识基础与思维方法,才能共同更好地在法治实践中发挥作用。”换言之,此事非仅关乎一家律所,而是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
职业共同体无疑有着相似的职业,但如果仅限于此,恐怕只是“职业共同”而已。职业相似不会因此自然形成共同体,这尤其体现在法律职业领域。职业共同而为一体,如蒋律师所言,关键在于知识基础和思维方法。
从天同制作天同码的旨趣中,可以清楚看到此“不务正业”背后的追求,亦可理解为何天同愿以法典评注为己任。
(三)
不太记得是2018年底还是2019年初,正郁兄邀我拜访天同。在那个著名四合院的西厢房,我们一边喝茶抽烟,一边漫无边际闲聊。聊的内容大多已经忘记,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正郁兄谈到天同研究院。在我的理解中,正郁兄想要设立的研究院,类似于传说中专事武学研究的少林达摩院。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古柏森森的庭院里老僧入定的画面,竟然心生驰往之意。二是聊到法律职业共同体,聊及法律学者与司法实务之间的隔阂与偏见,正郁兄言辞中透露的忧虑之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研究院须从长计议,合作无妨先行。得知我有意推进法典评注的工作后,正郁兄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即表示高度认同,其中又尤为看重评注对于推动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意义。2019年6月17日,天同捐资的南京大学法典评注基金正式成立。基金主要资助评注工作坊、评注讲座与评注年会三项活动及评注作品出版。

2019年7月20日,在天同无讼厅,法典评注工作坊第一期正式开坊,主题为漫谈式的“法典评注是什么”。此后,每期工作坊用一天时间讨论两篇评注作品。工作坊邀请二十人左右与会评议,其中一至二人主评,采闭门会议形式,以便评议人用最挑剔的眼光作最严苛的学术批评。这种工作模式,姚明斌教授称之为“会诊”。经过“会诊”的作品,手术矫治事属寻常,整体再造亦非罕见。由此带来的收益是,作品质量得到基本保障,工作坊纯粹率直的学术讨论氛围亦得以建立并成常态。
2020年初,新冠病疫突起。启动不足半年的法典评注活动旋即遭遇不可预知的持续障碍。幸赖所有参与者的鼎力支持,工作坊得以相对从容地见招拆招,视疫情变化在宁京沪三地相机切换地点。三年来,工作坊以游击战的策略举办十八期,评注作品基本实现“应坊尽坊”。
工作坊旨在内部交流,评注讲座则是开放性学术演讲。首期讲座举办于2019年9月7日,正在大陆学术交流的台湾大学吴从周教授应邀主讲。从周教授讲座当晚,能容纳数百人的南大法学院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这对于每届仅招收一百余名本科生的南大法学院而言,实属罕见。顺便一提,原本约请从周兄翌年再赴南大,为南大学子开设法学方法与案例研习课程,岂料世事无常,一别三年,再聚之日遥遥无期。每念及此,心中不免惆怅。同样因为受阻于疫情,讲座仅见缝插针式举办八期,未能实现每年四期的计划,殊为遗憾。
工作年会意在聚拢全部作者集中交流评注撰写中的一般问题。2019年11月23日,以“法典评注:比较观察与本土经验”为主题的第一届年会顺利举办,会上首发新书《合同法评注选》。本届年会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德国弗莱堡大学卜元石教授和日本静冈大学朱晔教授欣然受邀,不远万里专程回国参会,并允诺担任评注编委,为评注的中国化提供比较法经验。
因为疫情,2020年会遗憾停办。
2021年会主题为“评注方法论”。筹备过程一切顺利,但临近会期遭遇疫情反复,几乎再次被迫取消。所幸,在全体作者和特邀嘉宾的热情支持下,经过商议,年会形式于最后时刻改为宁京两地分设线下会场、多地线上参会。北京会场设于天同四合院,并在此首发新书《中国民法典评注·条文选注》第一、二册;南京方面,天同南京分所同仁不辞劳烦,几乎全员亲临南大法学院会场,为疫情寒潮笼罩的会场带来和煦暖阳。颇具戏剧性的是,南京会场离会次日,下榻酒店附近即发现病例,与会人员完美错开病毒全身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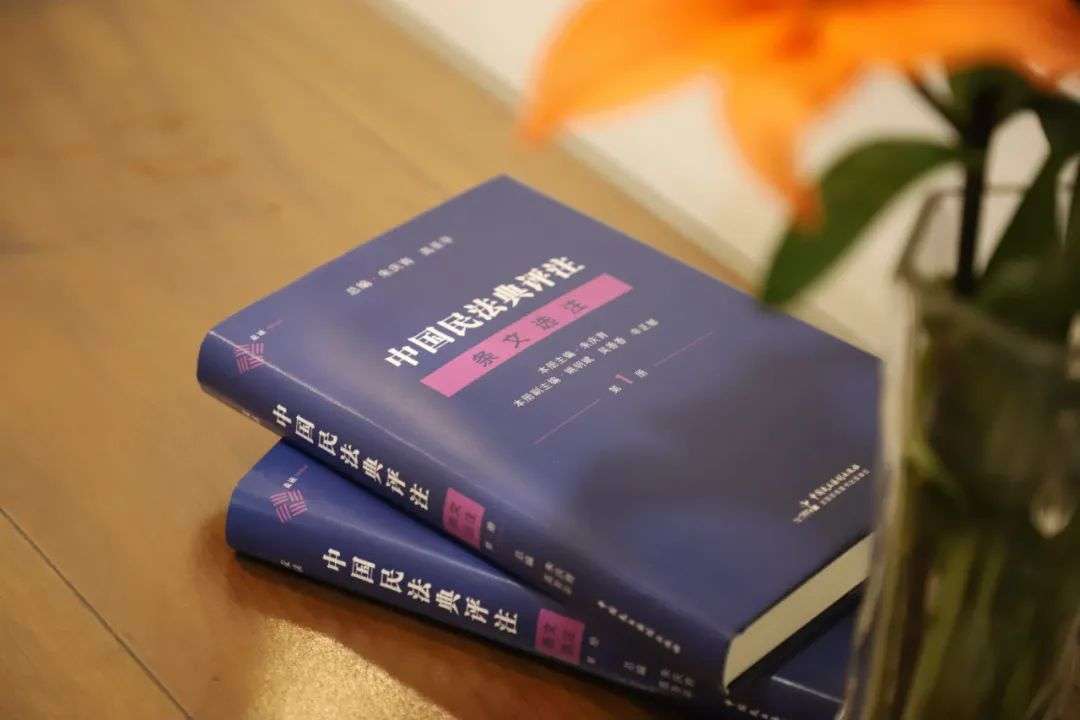
基金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提供资金,虽然资金支持已经足够重要——缺乏资金,评注各项活动均无法开展,评注撰写与组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亦未可知。正郁兄曾数次表示,天同之参与法典评注,并非简单的旁观者式资助,而是全面的实质合作。此非虚言。
十八期工作坊中,共有六期的线下举办地点为天同北京四合院或上海迴峰楼。此六期,大部分是在疫情期间,天同克服重重困难为工作坊的线下开展而创造的机会。比提供场所更重要的,是贡献时间和智力。天同同仁参加每一期评注讲座与每一次工作年会,更在百忙中参与强度极高的每期工作坊。参与评议的天同同仁准备之充分,发言之积极,常常迫使主持人行使权力控制时间,以便确保工作坊不至于过分延时。而所有参与方式中,最能体现实质合作的,无过于正郁兄之领衔天同同仁认领其中一个写作单元,成为法典评注作者团队的一员。目前,游冕律师已率先完成第一篇初稿,质量可圈可点。
(四)
上海迴峰楼的一次工作坊上,在西式典雅略带怀旧的会议室里,暖黄色灯光恰到好处地倾泻而下,映照出与会者激烈争辩的鲜活身影,温暖而充满生机。我调侃正郁兄:“天同越来越像研究机构了。”天同当然无意转型为研究机构,现实的学术研究在司法实务眼中形象亦未必有多正面,因此,这句话实在谈不上是恭维。
钟瑞庆教授发表于今年《法学家》第3期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在“违约所造成的损失”问题上,学者见解与法官裁判可谓各行其是,即使不是“相互看不起”,至少是“相互不理睬”。违约损害赔偿如此,其他问题不太可能更乐观。如果学术和实务总是生活在平行世界,共同体从何谈起?
不相往来的现状,学术与实务双方均难辞其咎。走向合作的第一步也许是各自反躬自省。在此意义上,正郁兄对天同律师的内训名言——“脱离实践的理论只是可笑,脱离理论的实践才是可怕的”——可以理解为,天同在迈出第一步的同时,亦以谦卑姿态伸出橄榄枝。也许,寄托在橄榄枝上的期待才是天同最大的追求。
2022年6月17日
南京大学法典评注基金设立三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