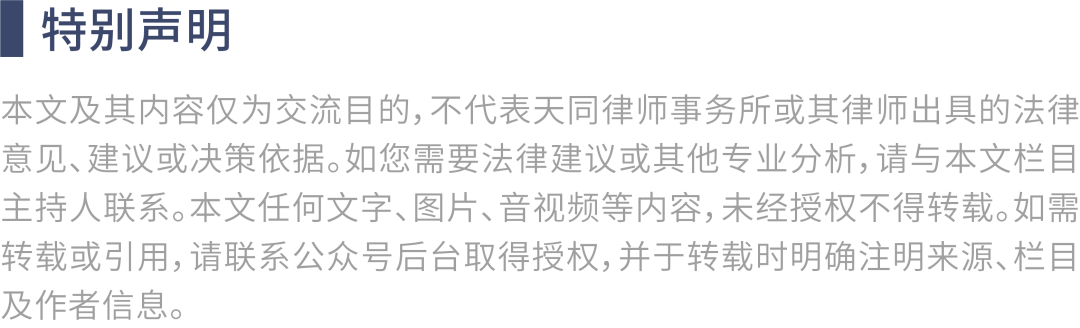注:本文发表于《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载第92–1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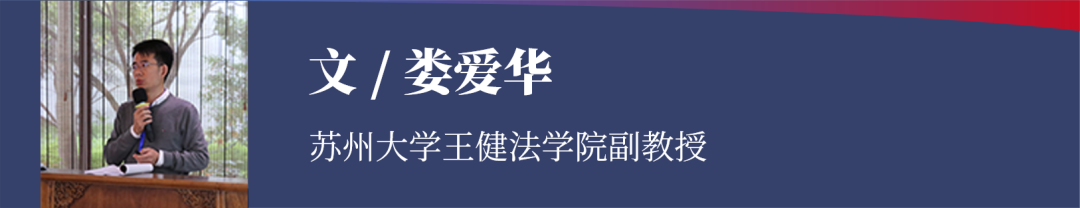
内容提要:忽视了当事人的抵销预期,无法妥善解决保证金的破产抵销问题。保证金权益具有不确定性,权益数额不确定,权益是否发生也不确定,保证金给出人可以基于其抵销预期主张破产抵销,抵销效果在待抵销权益确定后发生。保证金与所担保债务具有发生上的牵连性,作为债务人的保证金给出人的抵销预期不受债权让与影响,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规定的“同一合同”应基于抵销预期予以解释。为保障债务人抵销预期的同一合同内抵销,与传统大陆法系中司法抵销范畴下的同一合同内抵销不同。我国无需在破产法中区分独立抵销和同一合同内抵销。在以封金、专户方式设立保证金担保或者保证金收受人有设立保证金专户的法定义务时,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对保证金协议外的第三人有约束力,保证金给出人的权利为取回权或共益债权,保证金给出人的抵销预期对第三人有约束力,无需考虑破产抵销的偏颇清偿问题。解决保证金破产抵销问题的过程,也是发现抵销预期之价值的过程。
关键词:抵销预期;保证金;破产;同一合同;偏颇清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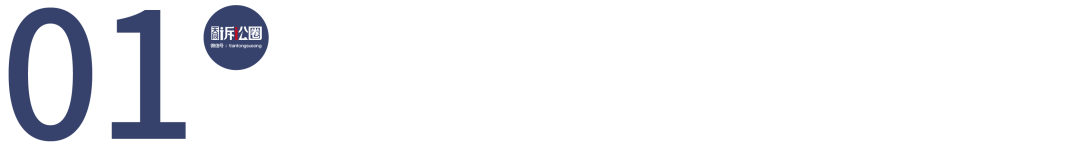
问题的提出
保证金是债务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而交由债权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金钱。[1]给出保证金的债务人在债权人进入破产程序前后可能对债权人负有多个债务,首先是保证金担保的债务,其次是瑕疵履行该债务产生的责任之债,最后是债务人负担的其他债务。保证金给出人基于保证金权益抵销上述债务时,构成保证金的破产抵销。保证金给出人能否以其保证金权益抵销债务,是给出人免受保证金收受人破产风险的关键。保证金给出人主张抵销时,实务界与理论界歧见频现。
首先,涉及不确定债权的抵销问题。保证金用以担保特定债务,保证金给出人只对冲抵特定债务后的保证金余额有权益。在保证金收受人破产时,该余额往往是不确定的。在保证金权益经抵扣后余额为零的情形,不存在保证金给出人对保证金的权益,不符合抵销“互负债务”的要件。在主合同或保证金协议未失去约束力的情形,保证金给出人不能主张保证金返还,也不符合“互负债务”的要件。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主张抵销不以债权确定发生或债权数额确定为前提,[2]也有学者认为在保证金账户担保的情形,保证金数额无需确定即可实现担保功能。[3]但是,为何个别抵销能够突破“互负债务”的要件,仍缺乏深入的论证。即便个别抵销不以债权确定发生或债权数额确定为前提,此等抵销也有别于债权额确定的抵销,如何抵销也成为问题。
其次,涉及主动债权后到期时的抵销问题。保证金给出人对保证金的权益,一般须在抵扣所担保债权后才能确定,往往晚于所担保债权到期。民法典第568条规定的抵销以主动债权到期为要件,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规定了债权让与时主动债权后到期且未到期的抵销,其要件为“债务人的债权与转让的债权是基于同一合同发生”。有学者认为,所谓“同一合同”,指两项债权在产生和存续上均有牵连性。[4]在民法典颁行前,有法院认为,保证金可以与“同一合同”中的其他债权抵销,[5]不能与非“同一合同”中的其他债权抵销,[6]但最高院认为抵销并不以待抵销债权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为必要。[7]有学者力主在破产法中区分“独立抵销”与“同一合同(交易)内抵销”,[8]并有学者主张应将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中的“同一合同”扩张解释为“同一交易”。[9]保证金与所担保债务的关联是否构成“同一合同”,“同一合同”何以证成主动债权后到期时抵销的正当性,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最后,涉及抵销时的偏颇清偿问题。保证金虽由收受人控制以担保特定债权,但“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有法院认为,保证金给出人基于对保证金的物权可以直接抵销,[10]抵销无需考虑偏颇清偿问题。也有法院认为,保证金给出人在给出保证金的一刻,便因“占有即所有”丧失物权、取得债权,[11]抵销需要考虑偏颇清偿问题。与之相关,在保证金收受人不当处置保证金的场合,有法院认为保证金给出人享有取回权,[12]无需考虑偏颇清偿问题,但也有法院认为给出人仅享有普通债权,[13]必须考察抵销是否构成偏颇清偿。
基于不确定的债权能否主张抵销?债权让与时,债务人基于后到期的债权主张抵销的正当性何在?破产抵销须考虑偏颇清偿问题的规则是否存在例外?保证金破产抵销引出的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了当事人的“抵销预期”,也就是当事人以相互负欠的权益进行冲抵的预期。不论债权是否确定,不论债权的到期先后,也不论待抵销权益是能够排除偏颇清偿的物权还是不能排除偏颇清偿的债权,权利人事实上都有着抵销的预期。在保证金破产抵销问题的既有讨论中,保证金给出人的抵销预期若隐若现、飘忽不定。解决保证金破产抵销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发现抵销预期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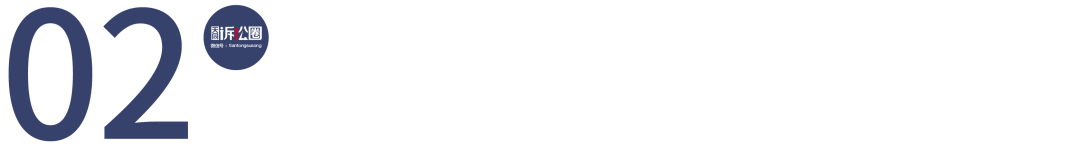
债权不确定时的抵销预期
依保证金所担保的主合同的履行情况,保证金的返还必属以下三种情形之一:其一,主合同完全履行,保证金应当返还;其二,作为债务人的保证金给出人违约,应当依保证金协议抵扣债务和其他费用后,返还余额;其三,收受保证金的债权人违约,债务人可在解除主合同或解除保证金协议后,主张返还保证金。
不论上述三种情形中的哪一种,保证金权益均具有不确定性,体现为是否发生的不确定与返还数额的不确定:在抵扣后保证金余额为零的情形,不存在保证金返还之债;只要主合同或保证金协议未失去约束力,保证金给出人就不能主张保证金返还,也不存在保证金返还之债;在依保证金协议发生抵扣债务或费用的情形,保证金余额是不确定的。
(一)数额不确定不构成主张抵销的障碍
在比较法上,有立法例认为法定抵销中的待抵销债权必须确定。如旧的法国民法典第1291条第1款要求待抵销债权必须确定。[14]新的法国民法典第1347-1条也要求待抵销债权确定。[15]意大利民法典第1243条第1款也要求待抵销债权确定。[16]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法域,债权额不确定时就一定不能抵销。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立法中,在法定抵销之侧,尚有司法抵销,破产法上的抵销也包括司法抵销。[17]司法抵销专门针对债权额不确定的抵销。新的法国民法典第1348条及意大利民法典第1243条第2款,专门规定了确定(certaine)发生但数额尚不确定(liquide)的债权的抵销。
民法中规定司法抵销,是以实体法规范解决程序法问题。法定抵销以债权额确定为前提,无需法官再行裁量,属依法抵销。司法抵销针对债权额不确定的情形,需要法官自由裁量。司法抵销时,若待抵销债权额易于确定,则应抵销。[18]新的法国民法典第1348-1条规定,如果待抵销债务间有关联关系,法官不得以债务额不确定或不可主张(exigible)为由否定抵销。[19]待抵销债务间有关联关系,表明对抵销抗辩或反诉的审查并不会增加审判内容、降低诉讼效率,因而是“易于确定”的。即便待抵销债务间没有关联关系,只要易于确定,不影响诉讼效率,也可以进行司法抵销。未规定司法抵销的立法例,则在程序法部分解决对应问题。例如,在不要求待抵销债权额确定的德国,也不区分法定抵销和司法抵销,若待抵销债权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法院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分别审理主动债权和被动债权,若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则应合并审理。[20]是否合并审理,其规范依据为诉讼法,而非实体法。
大陆法系要求待抵销债权额确定,始于优士丁尼改革抵销制度。[21]在优士丁尼之前,待抵销的债权额可以是不确定的,甚至会发生作为之债(facere)与给付之债(dare)间的折价抵销。[22]优士丁尼之所以要求待抵销债权额确定或易于确定,是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在债权额确定或易于确定时,抵销就能更有效率地展开。对于不符合诉讼效率要求的,债权人另案主张其权益在理论上不会影响其权益实现。
我国民法典在编纂时,也有学者考虑到主动债权额不确定的情形,认为基于同一合同关系产生的损害赔偿,即使数额尚不确定,仍然能够以最低赔偿数额为限进行抵销。[23]这一观点并未体现在民法典中,民法典第568条规定的抵销不以债权额确定为要件,也没有像新法国民法典第1348-1条那样提及关联关系或同一合同。既然民法典第568条不以债权额确定为法定抵销的要件,就没有必要区分法定抵销与司法抵销,也没有必要进一步在司法抵销中区分出基于同一合同(交易)的抵销。待抵销债权间的关联性,以及关联性引发的诉讼效率判定问题,完全可以依照既有的诉讼法条文解决。[24]
综上所述,在待抵销债权额不确定时,不论待抵销债权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法官不能以数额不确定为由否定主动破产债权人的抵销主张。一方面,依我国实体法的抵销规则,并不要求待抵销权益的数额确定;另一方面,在破产的语境下,诉讼法上基于效率考量否认数额不确定时的抵销主张也缺乏正当性。民法语境下,债权人即便无法诉诸更为高效的抵销制度,也能够另案主张自己的权益,民法可以对其抵销预期视而不见。但在破产法语境下,债权人一旦无法主张抵销,就丧失了保护其权益的最后机会,破产法必须尊重其抵销预期。
(二)发生不确定不构成主张抵销的障碍
“相互负债”是最基本的民法抵销要件,不论是否区分法定抵销和司法抵销。不存在相互负债,则没有抵销。相互负债,意味着债的发生具有确定性。履行期尚未届满的债权符合相互负债的要求,但附始期的债权就不符合,前一情形中债权已经发生了,后一情形中债权还未发生。附解除条件的债权符合相互负债的要求,但附停止条件的债权就不符合,前一情形中债权发生了,后一情形中债权并未发生。[25]
但在破产法语境下,债权人一旦无法主张抵销,就等于丧失了全额保护其权益的机会。在这一背景下,即便债权属于是否发生尚不确定的债权,也应允许基于该债权主张抵销。诚如学者所言,当破产债权人在程序启动时至少有希望抵销时,不应该阻止该抵销。[26]基于发生尚不确定的债权可以主张破产抵销,符合比较法上的通例,[27]符合我国破产法学界的普遍认识。[28]
在法技术层面,德国法通过“备位抵销声明”制度解决主动债权可能不存在的问题,在主动债权是否发生仍不确定时依然可以主张抵销,[29]构成互负债务的一种例外情形。意大利法则认为有两种债权额确定,一种是实体上的债权额确定,另一种是程序上的债权额确定。在有债的发生根据时,债权具有实体上的债权额的确定性。但若该债权被异议,被主张债权不存在或债权额有问题时,则不满足程序上的债权额确定。当实体上的债权额确定性被满足后,债权人就可以主张抵销。待程序上的债权额确定性也被满足后,才能发生抵销效果。[30]不论德国法上的“备位抵销声明”还是意大利法上对债权额确定的特殊解释,均旨在解决发生尚不确定的债权抵销问题。我国法虽没有这两种制度,但基于发生尚不确定的债权主张抵销,在实践中也不存在障碍。如有法院认为,“仅以佳宝集团等六公司尚未履行保证责任为由,否认佳宝集团等六公司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可行使法定抵销权,有违破产管理人对企业财产的处理原则”。[31]因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尚未履行,保证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尚未发生。此时允许主张抵销,就是基于发生尚不确定的债权主张抵销。质言之,破产法区别于民法,即便债权人的债权属于发生尚不确定的债权,也应准许债权人依其抵销预期主张抵销。
(三)抵销通知的意义在于启动抵销程序
抵销通知的意义在于启动抵销程序,通过程序达致债权额确定的结果。[32]债权额确定后,才发生面向未来的抵销的清偿效果,抵销无溯及力(ex nunc)。[33]我国民法学界虽然对抵销是否有溯及力存有不同观点,[34]但对于债权额不确定的抵销,抵销只可能是无溯及力的。只有对债权额确定的抵销,才有必要争论抵销有无溯及力。
由于保证金权益的不确定性,可以主张抵销并不意味着抵销效果的发生。诚如我妻荣指出的,债权额必须为确定的,是当然(法定)抵销所要求的,对债权的存在有争议或其金额不明确不构成抵销的障碍。[35]换言之,债权额确定与抵销效果是否发生有关,与是否可以抵销无关。即便基于债权数额或是否发生尚不确定的债权,也可以主张抵销。只是在债权额确定前,不发生抵销的清偿效果而已。有法院认为,只要债权人申报了债权,就意味着没有抵销,[36]这一见解有误。在债权发生尚不确定时,主张抵销并不意味着发生抵销效果,没有发生抵销效果,意味着债权依然存在,债权存在自然就可以申报债权。
对于发生尚不确定的债权,须在债权确定后才能发生抵销效果。日本法上有将待抵销份额提存进而留待抵销的做法。[37]依德国破产法第95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基于附停止条件的债权可以主张抵销,但在抵销障碍被排除后才发生抵销效果。[38]在停止条件成就后,债权确定发生,相互负债的条件成就,抵销障碍被排除。我国有观点认为,德国破产法的上述规定是“直接沿用民法上的抵销条件,破产抵销权能够行使的前提即在于其完全符合民法上抵销条件,未就其从破产法层面予以扩张”,[39]此言恐有不确之处。德国破产法第95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肯定了在不符合民法抵销要件时的抵销可能,构成破产法上的特殊规定。抵销的发生与抵销效果的发生是相互区别的两个问题,抵销发生并不意味着抵销效果的发生,德国法的规定指明了抵销效果发生的障碍消失,此等障碍消失的规则与民法抵销有共性,但不意味着此等抵销就是民法抵销。不符合“互负债务”的要件时可以主张抵销,已经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抵销。
抵销程序启动后会影响破产程序的进程。抵销权人未主张抵销的,不启动抵销程序。若待抵销债权已被清偿,因债权消灭而不再满足抵销的构成要件。在破产程序中,随程序的进行,破产财团的财产会渐次减少,且破产程序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即便真实权利人嗣后参与破产程序,也只能从其参与时起参与分配。如果抵销权人主张了抵销,即便未发生抵销效果,也会影响破产程序的进程。例如,在重整前主张抵销的,抵销不受重整程序的影响,但在重整启动后主张抵销的,因参与了重整程序,重整程序就对抵销有约束力。[40]有法院认为,保证金债权一定要经过债权申报,经申报后被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才可以抵销。[41]还有法院认为,未经法院裁定确认的保证金债权,只要经过破产管理人审查确认,即可抵销。[42]我国破产法上的债权申报程序,起于债权人的申报,终于法院的债权“裁定”。既然是“裁定”,就不存在任何实体法上的认定,“裁定”并不影响实体权利。保证金给出人主张抵销的基础是其基于保证金权益的主动债权,该债权并不会受到“申报”程序的任何影响。无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会议、法院对申报债权持何种态度,最终结果也仅仅是“裁定”而非“判决”。既然申报不影响实体权利,就不应以申报与否判定能否主张抵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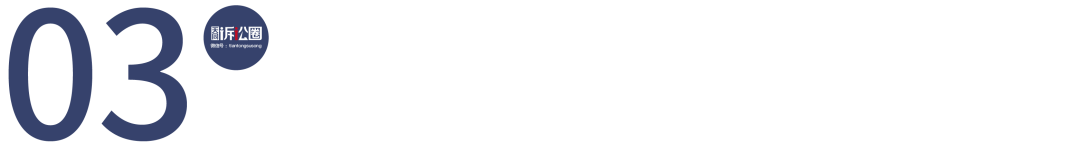
主动债权后到期时的抵销预期
对保证金给出人而言,之所以交付保证金给收受人,是为了担保特定债务。保证金与所担保债务之间有着紧密关联,这一紧密关联构成了保证金的本质属性。不具备这种关联性的,即便名为保证金,实际上也不构成保证金,如所谓工程质量保证金。[43]保证金与所担保债务之间的关联,证成了保证金给出人的抵销预期。该抵销预期在保证金给出人与收受人的两人关系中隐而不显,但在债权让与的情形,成为债务人得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免受出让人破产风险的关键。该抵销预期不仅决定了能否主张抵销,也决定了得以抵销的范围。
(一)同一合同、关联性与债务人的抵销预期
在债权让与的三方关系中,收受保证金的债权人将保证金担保的债权转让给新债权人后,原债权人破产无法返还保证金,保证金给出人能否基于保证金权益主张抵销,成为确保其利益的关键。[44]但“互负债务”是抵销的基本要件,此时债务人对原债权人有保证金权益,对新债权人负有债务,形式上并不满足抵销“互负债务”的要求。
我国原合同法第83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依立法者解释,债务人在接到转让通知后可以向新债权人发出通知主张抵销。[45]在收到转让通知后,债务人与原债权人的清偿关系已经消灭,债务人与新债权人的清偿关系确立,此时允许债务人主张抵销,突破了抵销“相互负债”的构成要件。民法典第549条第1项照搬了原合同法第83条,“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意味着债务人本可依照民法典第568条的规定等待主动债权到期后向出让人主张抵销。
不同于第549条第1项,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要解决的是“债务人的债权晚于转让债权到期”时的抵销问题,也就是依民法典第568条本不能向出让人主张抵销的情形。依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的新规,如果“债务人的债权与转让的债权是基于同一合同产生”,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既不考虑主动债权与转让债权的到期先后,也不考虑让与通知的时间,依“基于同一合同产生”即可主张抵销。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所设案型的两项债权则在产生和存续上均有牵连性”。[46]拙文以为,“基于同一合同产生”,应解释为待抵销债权具有发生上的牵连性即可。只要具备发生上的牵连性,就具备合理的抵销预期,无需再具备履行上的牵连性或存续上的牵连性。如果待抵销债权间还具备履行上的牵连性或存续上的牵连性,则在履行抗辩权或合同解除方面有意义。下文以保证金的抵销为例说明此点。
在债务人给付保证金时,已经有了“我之所以愿意将保证金交给你,是因为已经对你有负债”,“你若不能返还我的保证金,我就不对你为债务清偿”之类的意思。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则有“我之所以愿意你负欠债务,是因为你缴纳了保证金”,“你若不能缴纳保证金,则我不愿意你负欠债务”之类的意思。当事人意思,正如有学者形象指明的那样,同于“如果我对你负债100 元,我也会放心地贷款100 元给你”。[47]诚如我妻荣指出的,“债务人对其债权人取得同种债权时,两债权相互担保和信赖关系都应得到保护,抵销正是为此目的的制度”。[48]基于保证金权益,保证金给出人可以抵销保证金所担保的债务,也决定了保证金权益的抵销是单向度的抵销:收受保证金的债权人可以直接主张依保证金协议清算,其效力等同于债权人主张的抵销,但形式上并非抵销。[49]
在债务人与债权出让人的两人关系中,只要待抵销债权具有发生上的牵连关系,即便债务人的债权晚于出让人的债权到期,债务人在缔结合同时也有合理的抵销预期。债务人可以迟延履行其债务,直至自己的债权到期从而发生抵销。此时虽然债务人需要承担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但并不能因债务人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就否认其合理的抵销预期。因出让人转让债权的行为,受让人取得债权,债务人与出让人之间而不再满足“相互负债”的要件,从而有损债务人原本的抵销预期。既然债权转让以不损害债务人法律利益为原则,那么债务人的抵销预期就应予保护。
基于“同一合同”的待抵销债权,无需具备履行上的牵连性和存续上的牵连性。以租金保证金为例,债务人之所以愿意给出保证金,是因为保证金担保着债务的履行。如果没有所担保的债务,债务人不愿意给出保证金。同样,如果不是因为债务人给出保证金,出租人也不愿意设定对承租人授信的租金之债。对于出租人而言,他会考虑在承租人不付租金时执行保证金以满足租金债务。对于承租人而言,他也会考虑在出租人无法返还保证金时,通过不履行租金债务来抵销应获满足的保证金权益。此等发生上的牵连性足以证成抵销预期。与此相应,保证金债权与租金债权并无履行上的牵连性和存续上的牵连性。在出租人不履行保证金债务时,承租人仍要履行租金债务,在出租人无法返还保证金时,承租人也不能免去缴付租金的义务,因为承租人在占有和使用租赁物,不存在履行抗辩和合同解除的问题;反之亦然,承租人不缴纳租金或不能缴纳租金时,出租人可以执行保证金协议,扣除部分租金,但不能整体地不履行保证金返还义务,也不能解除返还保证金的义务,不存在履行抗辩和合同解除的问题。
在双务合同中,缔约双方互负的主给付义务具有牵连关系。牵连性体现在:积极意义上,你给付我才给付(发生上的牵连性);消极意义上,你不给付则我不给付(履行上的牵连性),你给付不能则我可以不给付(存续上的牵连性)。双务合同的牵连性是完整的牵连性,具有发生、履行、存续三个层面的牵连性,波及双务合同的履行抗辩权及法定解除制度。[50]保证金债权与租金债权仅具有发生上的牵连关系。
在民事留置制度中,[51]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与债权人返还标的物的义务之间有联系,在债务人不履行清偿义务时,债权人得以不返还标的物,两者的关联属于履行上的牵连性,但不具备发生上和存续上的牵连性:债务人之所以负担清偿义务往往是因为债权人提供了服务,而不是为了让债权人返还标的物,不存在发生上的牵连性;债务人不能履行清偿义务,也不意味着债权人返还标的义务的消灭,不存在存续上的牵连性。
如果说仅在同时具备发生上的牵连性、履行上的牵连性、存续上的牵连性三者时,才能说具备牵连性(synallagma),那么保证金权益与租金债权之间仅有的发生上的牵连性就不应被称为牵连性。留置制度中,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与债权人返还标的物义务之间仅仅具有履行上的牵连性,这种牵连性被界定为“关联(connectere)”而非“牵连”。[52]保证金权益与其担保债务仅具有发生上的牵连性,也应被界定为“关联”而非“牵连”。
关联性不仅体现在同一合同中,在涉及多个合同的同一交易中,也存在关联性。若主动债权晚于被动债权到期,但主动债权人在待抵销两债权中的后发生债权发生时,有以晚到期的主动债权抵销先到期的被动债权的意思,亦即主动债权与被动债权具有发生上的牵连性时,主动债权人也有着合理的抵销预期。无论后发生的债权是主动债权还是被动债权,只要在后发生债权发生时,对于主动债权人和被动债权人而言,后发生债权在发生上与先发生债权具有关联性,存有通过两债权互相抵销以实现清偿的预期,就存在合理的抵销预期。这也是将同一合同内抵销扩张至同一交易内抵销的正当性之所在。
如果保证金权益与待抵销债权并无发生上的牵连性,也就没有合理的抵销预期。如在“徐广萍与朱尧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朱尧峰曾在2016年6月15日为向民泰银行贷款交给严晓燕20万元保证金,2019年8月因朱尧峰还清贷款保证金应予返还,2017年1月23日严晓燕对朱尧峰的借贷债权发生,债权出让人严晓燕在2019年1月22日将其对债务人朱尧峰的到期债权转让给徐广萍,并在2019年5月送达了转让通知。法院最终未肯定朱尧峰针对徐广萍的抵销请求,而是依照待抵销债权的到期先后进行了判决,未判准抵销。[53]本案中,严晓燕的债权先到期,无法依照民法典第549条第1项进行抵销,在2017年1月23日严晓燕对朱尧峰的借贷债权发生时,朱尧峰和严晓燕之间也不存在以可能发生的保证金权益抵销借贷债权的预期,两债权并不具备发生上的牵连性,亦即不具备关联性,无法依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进行抵销。
依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的新规,先前依照原合同法第83条判决不能抵销的一些案件,恐怕是可以判准抵销的。如在肇庆市东方广场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王如洪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的判决理由为:“李瑞霞此项债权的到期时间晚于蔡燕屏债权的到期时间,其抵销的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应支持。”[54]李瑞霞赖以主张的借款债权,发生在2013年10月22日,早于被转让债权的发生时间(2013年12月3日),在被转让债权发生时,李瑞霞已有对出让人的确定发生的未到期债权,即便后发生的债权先于李瑞霞的债权近9个月到期,李瑞霞通过迟延清偿被动债权直至主动债权到期进行抵销也属于合理的抵销预期。迟延履行其债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不能据此否认当事人合理的抵销预期。
依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的新规,先前依照原合同法第83条判决不能抵销的一些案件,其判决理由有待商榷。如在山东佳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明海项目转让合同纠纷案中, 法院的判决理由为:“虽然双方补充协议约定的佳辰公司对鸿苑公司的新增土地出让金债权及契税债权是确定要发生的债权,但该两笔债权的到期日均晚于鸿苑公司向信安公司转让债权的时间,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佳辰公司就其对鸿苑公司的该两笔债权无权向信安公司主张抵销,更无权向王明海主张抵销。”[55]本案中,被转让债权与佳辰公司的债权均系房地产开发系列交易中产生的债权,形式上符合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所规定的“同一合同”的要件。本案中,2005年3月29日,鸿苑公司与佳辰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协议》,鸿苑公司据此取得对佳辰公司的3500万元债权,2005年10月9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据此协议佳辰公司在2010年3月23日、2010年4月8日、2010年4月9日履行了鸿苑公司本应履行的两笔债务后取得对鸿苑公司的债权,法院认定这两笔债权分别于2010年4月8日和2013年5月19日到期,2008年8月鸿苑公司转让了对佳辰公司的债权并通知了佳辰公司。本案中佳辰公司不能向债权受让人主张抵销的理由,不应是法院判决理由认定的佳辰公司两笔债权的到期日晚于鸿苑公司的债权,而是佳辰公司在履行鸿苑公司本应履行的义务而取得对鸿苑公司的债权时,不存在对鸿苑公司的抵销预期,因为鸿苑公司的债权已经转移给了第三人且通知了佳辰公司,也不存在佳辰公司据此履行有对第三人的抵销预期,因为佳辰公司并不能因其履行行为取得对第三人的债权。既然不存在合理的抵销预期,也就不能据此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二)我国破产法无需规定“同一合同内抵销”
在比较法上,有两种同一合同内抵销。第一种是在两人关系的抵销中,区分法定抵销与司法抵销,在司法抵销的语境下,对同一合同内的抵销予以特殊对待,考量因素为诉讼效率。第二种是在债权让与的三人关系中,认可债务人基于同一合同关系对受让人的特别抵销权,考量因素为债务人的抵销预期。
第一种类型的同一合同内抵销,在大陆法系有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在古典罗马法中,没有抽象统一的抵销制度,只有若干具体个别的抵销实践,包括诚信诉讼、钱庄主之诉、拍卖财产买受人之诉中的抵销。[56]在诚信诉讼中,法官对“基于同一关系”(ex eadam causa)的待抵销债权,可自行判准抵销。[57]诚信诉讼中抵销能否发生取决于法官意志,优士丁尼改革后的抵销则依法发生。[58]所谓依法发生,是指抵销依照法律的意志进行,而不再取决于法官的意志。[59]诚信诉讼中,待抵销债权是否“基于同一关系”,是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避免重复审查,但审查权必须交由法官行使,有悖优士丁尼创设“法定抵销”排除法官裁量权的初衷。依优士丁尼法,只要满足下述三条件,就应当判准抵销,包括“待抵销债权额的确定或易于确定”“主动债权的可主张”“互负债务的同种类”。[60]至此,“基于同一关系”的概念逐渐淡出抵销制度。从立法上看,“基于同一关系”的概念重新出现在抵销制度中,应始于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1243条对实践经验的汲取,[61]在新的法国民法典第1348-1条则有完整的呈现。[62]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了司法抵销制度,以专门解决待抵销债权额不确定时的抵销问题,但未特别规定待抵销债权间的关联关系(基于同一合同)对司法抵销的影响。新法国民法典第1348-1条同样规定司法抵销制度,并特别规定了有关联关系(基于同一合同)债权的司法抵销。意大利和法国的抵销法,是在优士丁尼改革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两国抵销制度仍以“待抵销债权额确定或易于确定”作为法定抵销的构成要件,因而有必要确立针对债权额不确定的司法抵销制度。在司法抵销中,若待抵销债权“基于同一合同”发生,其债权额虽不确定,但对待抵销债权的审查不会影响诉讼效率,因而将隶属于法官有裁量权的“司法抵销”,规定为法官实质上无裁量权的“法定抵销”。如新法国民法典第1348-1条规定:“如果待抵销债务间有关联关系,法官不得以债务额不确定或不可主张为由否定抵销。”与法国和意大利的抵销制度不同,我国民法典第568条并不以“债权额确定”为抵销的构成要件。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我国的抵销制度与德国保持了一致,德国的抵销制度更接近优士丁尼改革前的古典罗马法,不要求待抵销债权的数额确定,仍将抵销的裁量权交给了法官,由法官依诉讼法考量诉讼效率问题,待抵销是否基于同一合同属于诉讼法上考量诉讼效率的因素。[63]既然不要求债权额确定,自然也没有必要在抵销制度中另辟针对债权额不确定的司法抵销,也就没有必要在司法抵销下进一步规定“同一合同内抵销”,我国民法典未规定此种意义上的同一合同内抵销。近年来欧洲学界的主流观点也认为,既不应将债权额确定作为抵销的构成要件,也不应将与之相关的待抵销债权的关联性作特殊规定。[64]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民事诉讼法上的“同一合同内”的抵销存在误读,表现为以待抵销债权是否“基于同一法律关系”[?1] 作为判准抵销的前提。在湖北贤德面粉有限公司与中央储备粮襄阳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由于该损失与被告应支付的协作保管费和应退履约保证金均系在同一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互负义务,而非因履行不同合同产生,且是在人民法院受理贤德公司破产申请之前既已确定,也无其他不能抵销的法定情形,故前述原、被告双方互负义务可以相互抵销。”[65]显而易见,法院认为抵销的发生以待抵销债权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又如在亳州市广齐置业有限公司诉张立伟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安徽高院认为:“该损失系因涉案工程的施工,导致相邻民事权益遭受损失,属于损害赔偿纠纷,与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在实际施工人张立伟、严纪修未参与前案诉讼的情况下,将非因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予以部分冲抵,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不符。”[66]在此案中,法院认为只有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才可以在在一个诉讼中处理抵销问题。
待抵销债权是否“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构成法官判断诉讼效率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大陆法系,抵销的主张要么构成抗辩,要么构成特殊的反诉。[67]法官须考虑抵销的抗辩或反诉是否在本案中审理,若待抵销债权“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发生,在一个诉讼中解决而非另案诉讼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在意大利法和法国法中,在债权额不确定的司法抵销中,同一合同内的抵销问题由实体法规范,待抵销债权基于“同一合同”发生的,法官应判准抵销,但这绝不意味着不属于同一合同内的抵销就一定不予支持。在德国法中,同一合同内的抵销问题由程序法规范,待抵销债权基于“同一合同”发生的,属于程序法上应判准抵销的考量因素,但也不意味着非基于同一合同的两债权不得抵销。我国法与德国法接近,也是在程序法中解决待抵销债权基于“同一合同”发生时的抵销问题。法官在具体裁判时,“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构成在一案中审理抵销诉请的重要理由,但也不意味着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的抵销就一定不能主张。在亳州市广齐置业有限公司诉张立伟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的再审判决中,最高院认为:“原判决认为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予抵销,显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合同法前述规定的可抵销债务并未要求其必须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实践中,大量可抵销债权往往均是产生于不同的法律关系。”[68]毫无疑问,最高院的立场符合抵销实体法规定,尽管背离实体法规定要求待抵销债权必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做法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多数做法。[69]
第二种类型的同一合同内抵销,涉及债权让与时债务人利益的保护。日本民法第469条第2款第2项规定,“债权基于合同所生,且其合同为受让人已取得之债权之发生原因”,债务人可以主张抵销,即便该债务人的该债权于债权让与后取得。[70]新法国民法典第1348-1条第3款规定,对于关联债务的抵销,“第三人基于某一债务获得了权利,并不影响债务人主张抵销”。[71]这两条均肯定了债务人基于“同一合同”向受让人主张抵销,不受债务人债权发生时间的影响。此种以“同一合同”为依据保护债权让与时债务人抵销权益的做法也影响了我国立法,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明确规定了同一合同内的抵销。为保护债务人抵销权益的“同一合同内抵销”与考虑诉讼效率的“同一合同内抵销”并无关联,日本民法并未规定司法抵销,也未规定司法抵销项下的同一合同内抵销,但规定了债权让与时的同一合同内抵销,法国民法既规定了司法抵销项下的同一合同内抵销,又规定了债权让与时的同一合同内抵销。我国法上只存在为保护债务人利益的债权让与时的同一合同内抵销,在民事实体法层面不存在司法抵销项下的同一合同内抵销。
对债权让与时同一合同内抵销的正当性,有学者基于风险考量的外部视角进行了论证:由于反对债权和转让债权是基于同一合同或者同一交易产生的,受让人具有更强的认知可能性,而债务人通过自己行为损害受让人利益的道德风险更低,即便存在让与人不告知受让人债务人可以主张抵销的可能,这也是所有交易中都可能面临的共通风险,且受让人仍具有救济可能,此时将不利的风险分配给风险控制能力较强的受让人,不考虑债务人取得反对债权的时间,债务人都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就具有充分的正当性。[72]
这种视角的问题在于,低估了当事人抵销预期的解释力,最终损害当事人的私人自治。无论是“同一合同”还是“同一交易”,都应是论证当事人抵销预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规定的待抵销债权基于“同一合同”产生的情形,债权后到期的债权人已经有了合理的抵销预期,基于该预期足以论证抵销的正当性,无需舍近求远诉诸风险负担规则。在当事人没有抵销预期的例外情形,本属于特别法上的特别规定,应与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的一般规定形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差序格局。但如果以风险负担等外部视角论证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特别法上的债务人对受让人的抵销权与一般债权让与场合债务人对受让人的抵销权,在正当性方面就几无差别,会导致债务人的抵销预期反而被淹没在风险等外部因素的考量中,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差序格局也会变得混乱。
客观上属于同一合同的,未必一定能抵销。例如,保证金给出人迟延履行保证金担保债务的,就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债权受让人基于受让债权的事实及债务人迟延履行的违约事实,仍可作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违约责任。认可债务人的抵销预期,不意味着豁免债务人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有关履行期的约定也属于当事人的正当预期,不能厚此薄彼。与之相关,在让与人作为卖方和债务人签订货物买卖合同,约定先支付价金后交货,让与人将对债务人的价金请求权转让给受让人并通知了债务人,之后让与人履行对债务人的交货义务,但所交付的货物有轻微瑕疵的情形,也应尊重当事人既有的安排。此时,债务人获得对让与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债务人本可以向让与人的价金支付请求主张抗辩,在债权让与的场合,该抗辩自然也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此时并没有必要赋予债务人基于损害赔偿请求权对受让人的抵销权,债务人的抗辩权亦足以保护债务人,没有必要赋予债务人其意思之外的优待。可以想见,在债务人拒绝履行受让人的价金支付请求后,二者有可能达成协议抵销,但这与直接赋予一方抵销权不可同日而语。[73]
回归债务人的抵销预期,应以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区分,将“净额结算”和“交互计算”等特殊抵销交由特别法处理。[74]在一般法的层面,区分债务人有抵销预期的抵销和债务人无抵销预期的特殊抵销。对于有抵销预期的抵销,区分为主动债权先到期的抵销和主动债权后到期但有抵销预期的抵销,是否基于同一合同或同一交易发生,作为判断后到期主动债权是否有抵销预期的依据。对于无抵销预期的特殊抵销,应以判例的方式逐个确立,正如在商事留置场合存在没有关联性的留置权。在这种真正特殊的情形,考虑风险负担等要素才是正当的,而不是一般性地将同一合同内抵销的正当性建立在风险分配之上。
在民法典颁行前,有学者主张在破产法中区分独立抵销(抵销[?2] )和同一合同内抵销。其理由包括:其一,抵扣不受破产法的相关限制(如自动中止),抵销则否;其二,即便不承认抵销的国家,抵扣也受保护;其三,在诉讼法理论上,抵扣可以构成强制反诉事由,抵销则否。[75]但是,在我国破产法的语境下,并不存在美国法上的自动冻结制度,[76]区分抵扣与抵销对所谓自动冻结并没有意义。依我国破产法,以允许抵销为一般原则,因此区分抵销与抵扣,进而在不允许抵销的背景下凸显保护抵扣的必要性也不存在。此外,破产法会集中处理抵销和抵扣问题,不存在区分抗辩、反诉及强制反诉事由的必要。在普通的民事诉讼法中,我国法也不存在美国法意义上的强制反诉,[77]即便实体法上区分了抵销与抵扣,其诉讼法上的意义也十分有限。在破产法中区分独立抵销(抵销[?3] )和同一合同内抵销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对于债权让与时债务人抵销预期的保护,民法典第549条第2项的新规即可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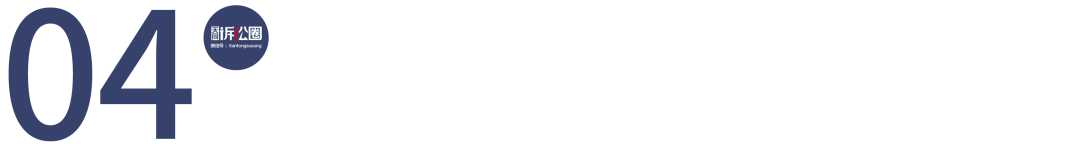
无需考察偏颇清偿问题的抵销预期
在保证金给出人和收受人的关系中,保证金虽由收受人控制以担保特定债务,但“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一方面,保证金虽然交付给了收受人,但区别于借贷和预付款,既不发生由收受人付息的借贷效果,也不发生减少主债务利息的清偿效果;另一方面,在履行保证金协议时,收受人是以保证金“清偿”所担保债务,在所担保债务消灭后,保证金应“退还”于给出人。[78]
在涉及包括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在内的第三人时,“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会影响保证金给出人的抵销预期。若“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对第三人发生效力,其抵销预期得以对抗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保证金给出人的抵销就不会存在偏颇清偿问题。若“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未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抵销预期就不能对抗第三人,抵销必须受到禁止偏颇清偿规则的审查。
(一)“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的射程
实践中,可以通过“封金”“保证金账户”“直接交付保证金给收受人”三种方式设定保证金担保,此等担保均具有如下要素:其一,保证金属于给出人;其二,收受人基于担保的目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保证金;其三,在条件成就后保证金收受人应将保证金返还。三种方式设定的保证金担保,均构成保证金担保的一种类型。“封金”“保证金账户”的特殊设立方式,与担保是否构成保证金担保无关,与债权人对保证金的权利能否对抗第三人进而“优先受偿”有关。既然对第三人而言,债权人对保证金的权利是优先“受”偿,那么债权人控制的保证金就不属于债权人,“保证金归属于保证金给出人”也同样对第三人发生了效力。在给出人直接交付保证金给收受人的情形,给出人虽然在与收受人的保证金协议中明确了保证金属于给出人,但接受保证金的收受人事实上可以处置保证金,第三人无从知晓收受人的部分金钱是属于给出人的保证金,且保证金给出人本可选择“封金”或“保证金账户”的方式获得优先权益,此时“保证金归属于给出人”对第三人就没有约束力,给出人对破产收受人的权益相较于收受人的其他债权人不具备优先性,除非收受人有为保证金开设专户的法定义务。
以“封金”“保证金账户”方式设定的保证金担保,与收受人有开设保证金账户的“法定”义务,对第三人的效果是相同的,均可向收受人的其他债权人表明“保证金属于保证金给出人”。若保证金收受人有开设保证金账户的法定义务且履行了该义务,则构成保证金账户担保。在保证金收受人本有法定义务设立保证金账户却未设立的情形,实践中的做法值得商榷。有法院认为,在保证金收受人本有法定义务设立保证金专户却未设立的情形,保证金被混同后,保证金给出人仍有取回权。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中,广东高院认为:“证券营业部没有设立专门保证金账户分账管理,过错在于证券交易营业部,并不能因此认为保证金所有权已发生变化。证券交易营业部是广东国投公司的分支机构,广东国投公司破产后,股票所有人依法可以通过破产清算组取回保证金。”[79]因未开设保证金专户,保证金与破产财团的其他资金已经发生了混同,保证金本身已经无法识别,“取回”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广东高院判决的意图,无非是以“取回”的权利形式保护保证金给出人的优先利益,但据此将保证金给出人的权益论证为取回权,有违一般法理。认可“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不等于认定给出人的权利一定是取回权。
设立专户分账管理为法定义务还是意定义务,对第三人有实质影响。若该义务为法定,因其法定性而为第三人知晓。在保证金给出人与第三人的关系中,“保证金属于给出人”据此对第三人有约束力,即便收受人未履行法定义务未设立专户分账管理,“保证金属于给出人”在给出人与第三人的关系中也不受影响。相反,若设立专户分账管理属的义务属意定,第三人没有理由知晓该义务,“保证金属于给出人”对第三人就没有约束力。此时,仅在保证金专户被实际开设且存入保证金时,给出人才可依据“保证金账户”的担保方式对抗第三人。在龙州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与龙州鑫磊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一般取回权纠纷案,[80]以及开封市北达商贸有限公司与北京五谷道场食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取回权纠纷案中,[81]不存在收受人设立专户分账管理的法定义务,即便约定了开设保证金账户的义务,也不能对抗第三人。虽然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相同,这两个案件中的收受人也都使用了保证金,但审理两案的法院并未审查设立专户分账管理的义务问题,且最终认定了给出人的权益为普通债权。
(二)基于取回权的抵销
基于“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给出人可以向收受人主张取回保证金。取回权虽然也有对债权的取回,[82]但对保证金的取回往往是一种基于物权的取回,实践中有大量的取回权与债权抵销的案例。
在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破产抵销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保证金质押期满后,在案涉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没有发生或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况下,中博公司作为保证金账户资金的所有权人,有权在保证金质权消灭后请求建行温岭支行返还账户资金,该权利性质上属于物权请求权,然而,金钱具有一般等价物属性,案涉金钱的物权请求权目的不在于要求返还存入保证金账户的特定金钱,而是要求返还等价货币,因而中博公司返还金钱的物权请求权实际上等同于金钱债权,建行温岭支行对中博公司负有实质上的金钱债务”,[83]因而可以发生抵销。
在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被上诉人STX(大连)造船有限公司管理人破产抵销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中行辽宁分行的主债权消灭,则设定于该保证金之上的质权也消灭,该保证金担保功能丧失,不再具有特定物之属性,其性质应转为普通存款。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动产、种类物,其占有与所有是同一的,一旦交付,即发生所有权的移转。对中行辽宁分行占有的该保证金,STX造船公司只能请求返还同等数额的钱款,而不能够根据物权请求权要求中行辽宁分行返还原物,因而,STX造船公司就案涉200万元及期间利息对中行辽宁分行享有债权”,可以抵销。与之相应,“STX造船公司管理人认为该200万元仍然具有特定物之属性,该公司仍享有物权而非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84]
上述两个案件,均属于保证金收受人主张抵销,而非保证金给出人主张抵销,但其核心问题为取回权与债权能否发生抵销,保证金收受人主张的抵销也有相同问题。两案的基本论证路径为,将保证金权益论证为普通债权,以满足“互负债务”的抵销要件,进而依破产法第40条抵销。两案的具体论证思路稍有区别:前案认可保证金给出人对保证金具有物权请求权,但将该物权请求权等同于债权请求权,后案不认可保证金给出人对保证金具有物权请求权,依占有即所有的规则,将保证金给出人对保证金收受人的权利论证为普通债权。
物权和债权都是保护特定利益的形式。物权区别于债权,除了可以向相对人主张,还可向不特定第三人主张。萨维尼奠定的物权概念,通过去关系化,[85]实现了物权的对世效力。去关系化也有程度的问题,在“物上之债”的情形,去关系化就没有物权那么彻底,债权人基于物的关系对限定范围的债务人享有权利。[86]对具体的诉讼而言,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仅对诉讼对象的选择有意义,基于物权可以针对不特定对象提起诉讼,基于债权原则上只能起诉债务人。在确定被告开启诉讼程序后,物权和债权并无本质差异,都意味着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的给付内容。在两人关系中,保证金给出人即便对保证金享有所有权,能主张的也是返还保证金而已,与基于债权主张返还并无差异。
在罗马法时代,虽然没有萨维尼抽象出的绝对的物权概念,但已经有了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的基本区分,前者可以基于对物的权利向不特定的人提起,后者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提起。对物之诉中也有抵销,优士丁尼对此有着清晰的论述。[87]对物之诉中的抵销,并不意味着“返还原物的诉请因金钱债权或其他债权的反请求而减少,而是对物之诉中的返还义务转化为金钱给付之债时的抵销”。[88]当对物之诉中的返还义务本就是金钱返还之债时,抵销自然更无疑义,保证金的抵销正属于这一情形。现代法亦认可此点,债权以外的物权请求权,理论上亦允许抵销,只要请求权的内容不违反同种给付之要求即可。[89]在比较法上,货物请求权与金钱债权间可以发生抵销,[90]两继承人间对共有遗产交错持有时也可以发生抵销。[91]《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中,对主动债权的界定使用的是“履行请求权”,回避了使用债权。[92]这里的履行请求权,显然也可以基于物权发生。物权或取回权的权利形式不构成抵销的障碍。保证金给出人可以基于取回权直接主张抵销,保证金收受人也可以基于其债权抵销给出人的取回权。
以物权性质的取回权可以抵销债权,取回权的权利形式并不构成抵销的障碍,即便待取回的保证金数额不确定,也可以基于取回权主张抵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已失效)第85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70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设立专门的保证金账户并由债权人实际控制,或者将其资金存入债权人设立的保证金账户,债权人主张就账户内的款项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新解释相对于旧解释,核心变化在于以“实际控制”替代“特定化”。“债权人主张就账户内的款项优先受偿”,表明此处的保证金有担保物权的功能。“特定化”的保证金,可以交付,属于动产质押。但“保证金账户”担保并非“封金”担保,在设立时保证金账户内的金额未必“特定”,只是债权人“实际控制”而已,构成一种特殊的担保,可以适用金钱质押规则,也可以适用债权担保规则。[93]在以保证金账户方式设立保证金担保时,即便保证金的数额并不确定,保证金权益仍能够以“担保物权”的形式存在,在保证金给出人破产时,收受人就能以“别除权”的方式行使权利。与之对应,在保证金收受人破产时,保证金给出人也有“取回”保证金权益的可能,基于该“取回”的可能,也就能够进一步主张抵销,不受数额不确定的影响。
(三)基于共益债权的抵销
以“封金”“保证金账户”的方式设立保证金担保后,收受人违法处分保证金,导致给出人无法实现其取回权的情形,给出人的权利应为共益债权。破产的保证金收受人本有“法定义务”设立保证金专户却未设立的情形,给出人的权利亦应为共益债权。共益债权的根据在于,“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已经对第三人发生了效力。
对于取回权转化为共益债权,破产法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形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3〕22号,下称“破产法解释二”)第37条第3款规定,在所有权保留场合,买受人破产时,“买受人管理人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导致出卖人损害产生的债务,出卖人主张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出卖人原本具有取回权,但在因买受人原因不能取回,且其权益可以对抗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时,无法实现的取回权就转化为了共益债权。保证金给出人本应获取的取回权,也应转化为共益债权,理由有三:第一,不当处分附所有权保留的标的物的买受人,与不当处分封金或保证金账户内资金的保证金收受人,以及本有法定义务设立专户却未设立的保证金收受人,其过错的性质和结果是一致的,均导致出卖人、保证金给出人无法获得本应获得的取回权;第二,“所有权保留”与“封金”、“保证金专户”及设立专户的法定义务的情形,在法律结构上均对第三人有约束力,破产买受人、破产保证金收受人的其他债权人均受到此等担保方式的约束;第三,无法取回时强行认定取回权有违基本的法理,会出现“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中“混同后仍可取回”的逻辑混乱。
现行破产法规范中,“破产法解释二”第45条规定了优先债权的抵销问题。该条规定,“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所列不得抵销情形的债权人,主张以其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与债务人对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抵销,债务人管理人以抵销存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的债权人,是“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亦即别除权人。无论别除权人还是取回权人或共益债权人,都属于有优先权的权利人。在别除权的范围内,债权人的抵销不会导致偏颇清偿。在保证金给出人有取回权或应有取回权的场合,也不会导致偏颇清偿。在本有的取回权或应有的取回权转化为共益债权时,也不会导致偏颇清偿。基于限制偏颇清偿与限制抵销的一致性,[94]也就不应基于偏颇清偿的考量限制抵销。
在保证金收受人破产时,若收受人有设立专户的法定义务,或以“封金”“专户”方式实际设定了保证金担保,给出人有取回权或共益债权,可以据此对破产的收受人主张抵销,法院无需考虑偏颇清偿问题,对基于破产法第40条的偏颇清偿规定提出异议的,应不予支持。只有在保证金给出人将保证金直接交给收受人,且破产的收受人没有设立保证金专户的法定义务时,给出人才应依普通破产债权抵销,也才有偏颇清偿的问题。这与审判实践中对待银行“扣款还贷”的立场是一致的。在银行与破产债务人明确约定了“贷款债权加速到期”“扣款还贷”或类似条款时,此等内部约定并不产生外部效力,银行主张以破产债务人的存款抵销其债权的,法院均会基于偏颇清偿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往往会基于偏颇清偿的考量否定银行的抵销主张。[95]
区别于保证金收受人的破产,在保证金给出人破产的情形,法院对保证金收受人的抵销主张可以直接进入到偏颇清偿环节,无需考察“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对第三人是否有约束力,即无需考察保证金担保的设立方式及是否存在为保证金设立专户的法定义务。收受人有返还保证金的义务,在收受人以其对破产的保证金给出人的其他债权抵销该债务时,就有偏颇清偿的可能,因而也就有排除偏颇清偿的必要。实践中的判例在此情形有可以改进之处。在丰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与多个银行的抵销权系列纠纷案件中,[96]丰立集团以保证金账户的方式设立了保证金担保,苏州中院和江苏高院对给出人权利的性质究竟属于物权还是债权有根本分歧,在进行偏颇清偿的审查后,均认可了收受人的抵销主张。在原告绵阳东源生态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平武县林业局对外追收债权纠纷案等案件中,[97]原告并未以开设专户的方式设立保证金担保,而是直接向被告缴纳了120万元的保证金,法院在排除了偏颇清偿的可能后,认可了被告的抵销主张。在宁波骏潮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破产抵销权纠纷案,[98]以及宁波东来化工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破产抵销权纠纷案中,[99]法院认为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在主债务被清偿后成为存款,保证金给出人享有的权利为存款债权,在审查了保证金收受人的抵销主张是否构成偏颇清偿后,支持了收受人的抵销主张。上述案件的审理中,没有必要特别考察保证金给出人主张返还的权利性质,保证金给出人能主张返还即可,重要的是对是否构成偏颇清偿的审查。
结 语
之所以需要发现抵销预期,是因为抵销预期在既有的抵销制度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民法抵销制度无视当事人的抵销预期,其正当性在于当事人可通过抵销以外的途径获得救济。在互负债务的一般情形,债务人基于后到期债权的抵销预期隐而不显,是因为债务人可通过迟延履行被动债权,事实上实现其抵销预期。破产法普遍审查抵销时的偏颇清偿问题,是因为抵销制度预设了“债权”的抵销,基于物权或其他优先权益的抵销只能削足适履。在处理一般的抵销问题时,抵销预期即便被忽视,也无碍抵销问题的解决。但若遭遇了保证金破产抵销这样的特殊情形,不回到抵销预期就无法妥善解决问题。
“保证金权益不确定”挑战了抵销“互负债务”的基本要件,“保证金与所担保债务的特殊关联”挑战了“主动债权不晚于被动债权到期”的抵销要件,“保证金权益归属于给出人”使得破产抵销是否有必要考察偏颇清偿成为问题。被民法抵销制度无视的抵销预期,表明债权的不确定并不构成主张破产抵销的障碍。主动债权后到期时债务人原本隐而不显的抵销预期在债权让与时显形,并为基于“同一合同”的抵销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能够约束第三人的抵销预期,意味着部分破产抵销的确无需考察偏颇清偿问题。
无论待抵销权益是否确定,无论据以主张抵销的债权先到期或后到期,也无论据以抵销的权益是物权还是债权,均不能否认当事人事实上有着抵销的预期。抵销预期植根于当事人的私人自治,实为抵销制度的无用之大用,在抵销制度步履维艰之时,能够为抵销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
注释:
[1] 保证金由债务人或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给出,本文限定债务人为保证金给出人,以聚焦于论文主要问题。
[2] 参见吴兆祥:《论民法典抵销制度的修改与适用》,《中国检察官》2020年6月(上),总第341期,第15页。
[3] 参见龙俊:《民法典时代保证金的双重属性》,《法学杂志》2021年第4期,第31页。
[4] 参见崔建远:《论中国民法典上的抵销》,《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22页。
[5] 参见湖北贤德面粉有限公司与中央储备粮襄阳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枣阳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3民初4296号。
[6] 参见亳州市广齐置业有限公司诉张立伟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终781号。
[7] 参见亳州市广齐置业有限公司等诉张立伟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74号。
[8] 参见许德风:《破产视角下的抵销》,《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137页。
[9] 参见朱虎:《债权转让中对债务人的延续性保护》,《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157页。
[10] 参见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破产抵销权纠纷案,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民初5016号。
[11] 参见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被上诉人STX(大连)造船有限公司管理人破产抵销权纠纷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157号。
[12] 参见“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民事裁定书。请补充该裁定书的文号。
[13] 参见龙州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与龙州鑫磊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一般取回权纠纷案,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4民初32号。
[14] 《拿破仑民法典》,李浩培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5页。
[15] 李世刚:《法国新债法·债之渊源(准合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
[16] 《意大利民法典》,陈国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该译本将确定性译为“结账可能”。
[17] Cfr. Roberta Catalano, Profili Evolutivi della Compensazione in Ambito Civile e Fallimentare,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2020, p.111.
[18] Cfr. C. 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l’obbligazione), Giuffrè, 1990, p.505.
[19] 前引15,李世刚书,第172页。
[20] 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982页。
[21] Guido Astuti, Compensazione (storia), ,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Civile, VIII, Giuffrè, 1961, p.11. 这是什么文献?
[22] 同上文,第2页。
[23]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通则)》(朱虎撰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23页。
[2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0〕20号修正)第233条第2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25] Cfr. Piero Schlesinger, Compensazione (diritto civile), in Novissimo Digesto Italiano, III, diretto da Antonio Azara e Ernesto Eula, UTET, 1957, p. 723. 这是什么文献?
[26] [德]乌尔里希·福尔斯特:《德国破产法》,张宇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18页。
[27] 参见吴传颐编著:《比较破产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13页。
[2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破产法解释(一)·破产法解释(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第461页。
[29] 黄茂荣:《债法通则之三:债之保全、移转及消灭》,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王洪亮将之译为“可能之抵销”,并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诉讼行为(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黄立将之译为“预备的抵销”,并认为此种抵销被附以败诉的法定条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条件,因而不构成附条件的抵销(参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5页)。
[30] 参见前引17,Catalano书,第123页。
[31] 参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与上海金源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佳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浙江佳宝高仿真化纤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019号。
[32] Cfr. Giuseppe Ragusa-Maggiore, Compensazione (diritto civile), 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Civile, VIII, Giuffrè, 1961, p.22. 这是什么文献?
[33] 参见前引25,Schlesinger文,第729页。
[34] 对于抵销通知的效力,民法典第568条规定,“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并没有明确到达对方的通知是否具有溯及力。在民法典立法前,有学者主张抵销通知不应具有溯及力。参见廖军:《论抵销的形式及其效力》,《法律科学》2004年第3期,第57页;张保华:《抵销溯及力质疑》,《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第101页。在解释论上,似乎有理由认为,民法典倾向于抵销通知应无溯及力。参见前引23,王利明主编书,第525页。
[35] [日]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王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36] 威海老船长航运有限公司、孙广达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案,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0民终433号。
[37] 参见[日]石川明:《日本破产法》,何勤华、周桂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38] 参见[德]莱因哈德·波克:《德国破产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39] 参见前引28,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书,第461页。
[40] 参见王志诚:《重整程序中债权人行使抵销权之期限》,《月旦法学教室》总第137期(2014年3月),第23页。我国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着相同见解,参见前引8,许德风文,第156页。也有判例支持了此种见解,参见丰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破产抵销权纠纷案,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民终2407号。
[41] 参见四川广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林兴刚破产抵销权纠纷案,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6民终1055号。
[42] 参见忠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破产抵销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商终字第27号。
[4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17条规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不存在保证金给出与担保特定债务间的关联性,条件成就后由债务人“付给”价额而非将保证金“返还”给出人。此等“工程质量保证金”实为一种暂缓支付的价款而非保证金。参见前引3,龙俊文,第30页。
[44] 若保证金给出人破产,收受保证金的债权人执行保证金协议即可,无需抵销。若受让人破产,则保证金给出人依然可以从收受保证金的债权人处获得保证金返还,理论上亦无需抵销。
[45] 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46] 参见前引4,崔建远文,第22页。
[47] 前引8,许德风文,第138页。
[48] 前引35,我妻荣书,第283页。
[49] 在法国法中,出租人以保证金清算欠付租金的,也被认为是一种抵销。参见《法国民法典》下册,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81页。
[50]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80页以下。
[51] 此处限于民法留置。商事留置情形,往往不存在民法留置中的留置预期,也就是不存在合同签订时的履行抗辩权预期。德国法上的商人留置权不以请求权的关联性为前提,参见[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页。
[52]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似乎并不区分“牵连”与“关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已失效)第109条的表述是“债权人对动产的占有与其债权的发生有牵连关系”,权威学者也认为留置以“牵连关系”为构成要件。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6页。
[53] 参见徐广萍与朱尧峰民间借贷纠纷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345号。
[54] 参见肇庆市东方广场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王如洪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867号。
[55] 参见山东佳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明海项目转让合同纠纷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初1097号。
[56] Cfr. Giovanni Pugliese, 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 Terza edizione, G. Giappichelli Editore-Torino, 1991, p.629.
[57] 参见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3页。
[58] 同上书,第515页。
[59] Biondo Biondi, Compensazione (diritto romano), in Novissimo Digesto Italiano, III, diretta da Antonio Azara e Ernesto Eula, UTET, p.721. 这是什么文献?
[60] 前引21,Astuti文,第11页。
[61] 前引32,Ragusa-Maggiore文,第21页。
[62] 参见前引15,李世刚书,第172页。
[63] 参见前引20,冯·巴尔等主编书,第982页。
[64] See Nils Jansen & Reinhard Zimmermann (eds.), Commentaries on European Contract Law, Oxford, 2018, p.2967-2968.
[65] 参见前引5,(2019)鄂0683民初4296号。
[66] 参见前引6,(2016)皖民终781号。
[67] 参见张保华:《抵销抗辩中的关联性与确定性:实体法与程序法交织的视角》,《法律适用》2020年第9期,第67页。
[68] 参见前引7,(2017)最高法民再274号。
[69] 刘哲玮:《论诉讼抵销在中国法上的实现路径》,《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第151页。
[70] 参见王融擎编译:《日本民法条文与判例》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393页。
[71] 参见前引15,李世刚书,第172页。
[72] 参见前引9,朱虎文,第155页以下。
[73] 相反观点参见前引9,朱虎文,第157页。
[74] 关于净额结算的简介,参见周成杰:《“净额结算”制度浅析——涉“中央对手方”机制法制保障研究》,《上海金融》2015年第10期,第91页。
[75] 前引8,许德风文,第140页。
[76] 美国法上的自动冻结,参见[美]道格拉斯·G. 贝尔德:《美国破产法精要》,徐阳光、武诗敏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00页。
[77] 参见严仁群:《既判力客观范围之新进展》,《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第555页以下。
[78] 海关法第93条规定了保证金的“抵缴”,保险法第97条规定了以保证金“清偿”债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0条规定了保证金的“没收”。在保证金给出人不履行义务时,不论保证金是被“抵缴”、“没收”还是用来“清偿”债务,保证金都是“归属”于保证金给出人的。保证金的占有人不能“没收”已经属于自己的保证金,也不能“抵缴”已经属于自己的保证金,更不可能用已经属于自己的保证金“清偿”保证金给出人的债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28条甚至明确规定了保证金属于给出保证金的会员、客户所有。意定保证金与法定保证金皆为保证金,在此点上并无差异。
[79] 参见前引12。
[80] 同前引13。
[81] 参见开封市北达商贸有限公司与北京五谷道场食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取回权纠纷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09)年房民初字第02882号。
[82] 参见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
[83] 同前引10。
[84] 同前引11。
[85] 参见苏永钦:《大民法典的理念与蓝图》,《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第64页。
[86] 参见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
[87] 参见前引57,徐国栋书,第515页。
[88] 前引59,Biondo Biondi文,第721页。
[89] 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2页。
[90] 参见前引26,福尔斯特书,第119页。
[91] 参见前引49,《法国民法典》下册,第980页。
[92] 参见前引20,冯·巴尔等主编书,第972页。
[93] 参见前引3,龙俊文,第38页。
[94] 参见[美]查尔斯·J. 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册,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6页。
[95] 参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行、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78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新支行、深圳市华芯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887号;浙江保达机电环保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23号。
[96] 参见前引40,(2017)苏05民终2407号;丰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破产抵销权纠纷申诉、申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申3685号;丰立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破产抵销权纠纷申诉、申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申3680号。
[97] 参见绵阳东源生态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与平武县林业局对外追收债权纠纷案,平武县人民法院(2018)川0727民初466号。
[98] 参见宁波骏潮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破产抵销权纠纷案,余姚市人民法院(2014)甬余商初字第1091号。
[99] 参见宁波东来化工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破产抵销权纠纷,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211民初369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