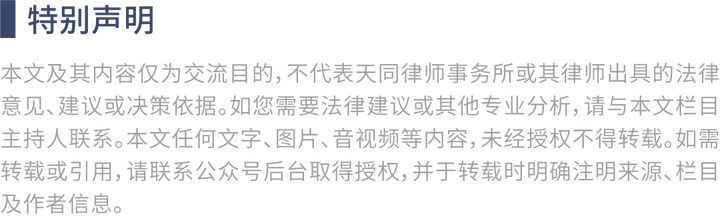注:本文发表于《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载第102-118页。
作者按:2019年6月28日,最高院作出“斯曼特”案再审判决,确立了“董事对发起人股东出资负有监督义务及违反该义务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裁判规则。鉴于我国绝大多数公司股东处于“认而不缴”状态,董事履职风险将明显放大。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包括:1.董事应否负担此项监督义务;2.此项义务的法律性质;3.其义务违反之构成及认定。问题2影响到能否通过章程豁免、当事人举证责任配置并被告抗辩事由等。问题1也关涉“斯曼特”案参照适用(类推)《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之检讨。期待本文能引发并有助读者朋友们的更深思考。
摘要:董事应否对股东出资负有监督义务,是公司法理论和实践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股东出资对公司资本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和董事的职能定位,董事应对股东出资负有监督义务。该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并非仅属注意义务,而是区分不同情形分属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斯曼特案中,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违反的是忠实义务而非注意义务,再审法律适用存在错误。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在义务构造、因果关系等诸多方面存在特殊性,人民法院在未来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严格依照行为、损害、因果关系、违法性和过错五大侵权构成要件,谨慎、精细地认定董事违信责任,以司法保障公司法的正确实施。关键词:董事;股东出资;监督义务;信义义务;违信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由斯曼特案引入
我国《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1]其中,公司法对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作出了“列举加兜底”的规定;[2]但对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未作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未形成清晰、可操作的义务外延和规则。例外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3]特别对公司增资时董事监督股东出资的勤勉义务作出了具体解释和规定。依照该规定,董事消极不履行监督增资股东出资的勤勉义务致使出资未缴足的,应承担相应责任。基于增资股东出资与发起人股东出资的同质性,自然导出的疑问是,董事对发起人股东的出资是否负有同样的监督义务?若有,违反该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对此,公司法理论和实践都未有明确结论。
2019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对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斯曼特公司)、胡秋生、薄连明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斯曼特案)作出再审判决,以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为由,撤销了一、二审判决,改判胡秋生、薄连明等深圳斯曼特公司的六名董事就发起人股东South Mountain Technologies Ltd.(以下简称开曼斯曼特公司)未出资部分共计4,912,376.06美元向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该判决对“董事对发起人股东出资的民事责任”的裁判规则产生了颠覆性影响,[5]犹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董事暴露在随时可能为股东未出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危险之中,该案[6]造成了巨大了社会舆论影响,后续高检院是否会抗诉?若抗诉,最高院是继续维持还是彻底改判?皆未有定数。
鉴于斯曼特案确立的“董事对发起人股东出资负有监督义务和违反该义务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裁判规则的重大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有必要在公司法理论上对该案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其背后的法理,勾勒出董事对股东出资监督义务的轮廓,在丰富我国公司法董事受信义务理论的同时,助力司法实践。
原告深圳斯曼特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11日,系外国法人独资公司,股东为开曼斯曼特公司,认缴注册资本额1600万美元。2005年1月11日至2006年12月29日,胡秋生、薄连明、史万文、Kyle Ranson、John V. Harker、Mike Yonker共6人任深圳斯曼特公司董事;2006年12月30日起,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Kyle Ranson、Gregory Stevens、Peter Behrendt共6人任深圳斯曼特公司董事。胡秋生、薄连明、史万文、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以下简称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在担任深圳斯曼特公司董事期间,同时也是开曼斯曼特公司的董事。深圳斯曼特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成立后90天内股东应缴付出资300万美元,第一次出资后一年内应缴付出1300万美元。开曼斯曼特公司于2005年3月16日至2005年11月3日分多次出资后,仍欠缴出资5000020美元。2011年8月31日,深圳中院作出裁定,追加开曼斯曼特公司为被执行人,在5000020美元范围内对深圳斯曼特公司债权人捷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7]经强制执行,开曼斯曼特公司仍欠缴出资4912376.06美元。2013年6月3日深圳中院受理了深圳斯曼特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管理人遂代表深圳斯曼特公司起诉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对前述欠缴出资所造成深圳斯曼特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认为,虽然通过对《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的解释,追缴股东欠缴出资属于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应负勤勉义务的范围,但是按时足额缴纳出资是股东的义务而非董事的义务,深圳斯曼特公司未收到全部出资,系因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所致,而非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消极不履行勤勉义务或者未积极催缴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所致,因此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的消极不作为与公司所受损失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请。[8]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认为在公司章程没有明确规定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的义务、没有证据显示其消极未向股东催缴出资与公司所受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情况下,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9]
最高院的再审判决颠覆了一、二审的裁判立场,支持了原告的诉请,其裁判逻辑是:首先,董事负有监督发起人股东出资的勤勉义务。理由有二,一是虽然《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并未列举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情形,但由董事的职能定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作用所决定,董事负有向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二是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的股东负有的出资义务与公司增资时是相同的,董事、高管负有的监督股东出资的义务也不应有所差别,故可参照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的规定,认定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负有向发起人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其次,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具有过错。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同时又是开曼斯曼特公司的董事,对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运营情况均应了解,具备监督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便利条件。再次,深圳斯曼特公司受有损害。深圳斯曼特公司因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由此,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未缴清出资的行为实际损害了深圳斯曼特公司的利益。最后,具备因果关系。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消极不作为放任了实际损害的持续,损失的数额即为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欠缴的出资,故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深圳斯曼特公司所受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据此,最高院判决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向深圳斯曼特公司连带赔偿4912376.06美元。[10]
通过前文对裁判要旨的重述,不难发现三级法院在法律适用上的主要分歧有二:一是董事是否对股东出资负有监督义务。一审通过对《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的解释,认为董事负有催缴股东出资的勤勉义务。二审则干脆否定了该义务,认为由于法律和深圳斯曼特公司章程都没有明确规定董事负有催缴股东出资的义务,因此难以得出董事负有前述义务的结论。再审以董事的职能定位和资本对公司关键性作用并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为理由,从《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中解释出董事负有催缴股东出资的义务。二是董事消极未履行该义务与股东未全面出资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一、二审均认为,董事消极未履行与股东未全面出资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理由是出资是股东的义务而非董事的义务,董事是否催缴与股东是否出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再审则认为,开曼斯曼特公司未缴清出资实际损害了深圳斯曼特公司的利益,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消极不作为的行为放任了这种损害的持续,故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此外,与一、二审法院不同,再审为证成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的赔偿责任,进一步分析了过错和损害两个要件。
由上引出的一系列问题是:第一,董事应否负有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若有,该监督义务在法律性质上是注意义务还是忠实义务?抑或是一种独立类型的信义义务?是全体董事的义务,还是部分董事的义务?第二,依法足额按时出资是股东的义务,股东未缴足出资是公司受有损失的直接原因,董事消极未履行催缴义务仅居于或有的次要地位,最高院以“放任了损害的持续”为由,证成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消极不作为与公司受有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理由是否充分?第三,关于过错的问题,最高院认为,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是共同董事,推定其对开曼斯曼特公司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明知的,因而具有错过。由此引发的疑问是,共同董事是过错成立的必要条件吗?若不是,在非共同董事的情形下,该如何认定过错?第四,关于损害的问题,任何市场主体都可能陷入支付不能的状态,股东未能按时足额出资,是董事对公司造成的损害,还是公司本应承担的商业风险?这种损害在法律性质上是公司的商业损失,还是非商业损失?第五,关于责任形态的问题,再审判决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否具有法律或者约定的依据?第六,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后,他们之间的内部责任该如何分配?以上问题,是厘清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和构建合理、清晰、明确的裁判规则,急需回答的理论难题。
此外,斯曼特案还有以下诉讼法问题有待进一步商榷:外方董事是否应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11]鉴于该问题并不聚焦于公司法,本文暂按下不表。
二、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及其法律性质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法都规定董事对公司负有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在内的信义义务,我国亦不例外。其中,注意义务要求董事在作出商业决策时必须尽到一个一般谨慎的人在同样或者相似的情形下的注意;董事只要尽到该义务,即便决策失误致公司受损,其亦受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12]忠实义务要求董事在行使职权处理公司事务和财产(包括信息)时必须尽到善意的努力以增进公司的利益;否则,董事要为公司由此受到的损失承担个人责任。[13]可见,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通常是对董事作出决策或者积极行为时的要求。
然而,在董事没有意识到需要作出决策或者疏于对公司行为的监督、消极不作为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场合,董事是否违反了对公司的有关信义义务?未有清晰的答案。以斯曼特案为例,董事消极不监督/催缴股东出资致使公司受损,是否违反了对公司的信义义务?若是,该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注意义务还是忠实义务,抑或是构成一项单独的、独立的信义义务?恰好落入了这个几乎空白的领域。
在探讨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之前,有必要先说明董事对公司所负有的一般监督义务。对此,我国公司法文献鲜有涉及[14]但有境外公司法学说和判例可供借鉴。
美国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董事对公司的监督义务,该义务要求,当董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出现违法或者其他可能致使公司受损的行为时,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否则董事要对公司的损失承担个人责任。[15]在Francis v. United Jersey Bank[16]案中,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为,董事在管理公司上需要尽到一般意义上的注意,包括对公司业务的熟悉、持续了解公司经营活动的状态和财务状况,以及当发现公司存在违法活动时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Mrs. Pritchard作为公司的董事,对公司事务没有基本的了解,有义务知道公司的另外两名董事(她的儿子)在对公司实施盗窃行为而不知情,没有积极行使董事职权阻止损害的发生,判决其对公司损失承担个人责任。无独有偶,美国公司法立法和实践的领头羊特拉华州,通过Graham v. Allis-Chalmers Manufacturing Co.[17]、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18]、Stone v. Ritter[19]和In re Citigroup Inc.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20]四个具有影响力的典型案件,发展和勾画出了特拉华版本的董事监督义务的基本轮廓。
在Graham案中,雇员违反联邦反托拉斯法致使公司受损,股东提起派生诉讼要求公司董事承担个人责任,理由是董事没有采取适当的监控措施去防止公司雇员实施违法行为。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在董事没有发现存在违法活动的危险信号(red flag)之前,他们有权信赖下属是诚实和正直的,没有义务必须建立一套监视制度,因此,在董事们对雇员违法行为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无需承担个人责任。[21]在Caremark案中,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对董事监督义务作出了与Graham不同的解释,认为董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存在违法行为时,有义务去纠正。[22]也就是说,1963年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Graham案中确立的“只要董事对公司违法行为不知情就不用为此承担个人责任”的规则被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所推翻。[23]Caremark案实质上扩大了董事承担监督责任可能的范围,也即在董事应当知道公司存在违法行为时,也负有义务去纠正,这与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Francis案中的裁判逻辑如出一辙。
十年后,Caremark案确立的规则被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Stone案中确认并重新表述,成为特拉华州现行的董事承担监督责任的基本规则,即“董事承担监督责任的必要条件是:(a)董事完全没有构建任何报告、搜集信息的制度或者内部控制;或者(b)已经实施了这样的制度或者控制,却有意识地不去监督制度的运行致使他们自己未能获取应当知悉的信息。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对董事处以责任,都必须要证明董事对自己没有履行信义义务是知情的。当董事没有履行一个他们知情的义务,从而有意识地无视他们的职责,他们就会因没有善意履行信义义务而违反了忠实义务。”[24]而关于何谓“没有善意履行”,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In re Walt Disney Co. Derivative Litig.案中作出了具体描述:未能善意行事是指,例如,受托人故意不以促进公司最佳利益的目标行事,或者受托人故意违反制定法,或者受托人有意识地不去履行一项明知的义务。[25]三年后,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在Citigroup案中确立了“董事通常无须为未能监控公司的商业风险而承担个人责任”的规则。该案中,法院拒绝了原告股东提起的要求董事因未尽控制商业风险的义务导致公司受损而承担个人责任的诉请,其给出的一个理由是,风险是商业的本质特征,董事和高管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经营公司时本身就要做冒险决策。[26]但对该规则的合理性,理论界存有争议。[27]至此,董事对公司行为的监督义务就主要体现为对违法行为的监督,而不包括一般的商业行为。
从上文对监督义务的描述和内涵界定看,董事对公司行为一般意义上的监督义务可以涵盖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但后者又有其特殊性。董事对公司行为监督义务的典型情形是对公司违反公法[28]行为实施监督,而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是对一项私法行为的监督。虽然二者在监督对象的性质上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两种行为在“对公司可能造成的损害”这个特征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概念上将后者纳入前者是顺畅的。同时,鉴于股东的出资是公司资本形成的唯一来源,而资本的确定、维持又是公司人格得以正当存在和存续、公司事务得以有效运行、股东享有有限责任的必要保证和条件。加之,无论公司作为拟制的实体还是实在的实体,其对外的行为或活动都必须要依赖董事等公司受托人作出。因此,笔者认为,公司内部至少须有一位董事等高管负担监督股东依法按时足额出资的义务,以此维护公司对其资本的合法权益。在该问题上,《日本公司法》甚至规定公司设立时股东未能足额出资的,董事须对公司受有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9]可以说,让董事等公司高管对股东出资负担监督义务具备坚实的法理基础。在斯曼特案中,二审判决径行以法律和公司章程并未明确规定董事负有监督股东出资的义务为由,否定董事负有前述义务,该论点并不成立;再审判决以董事的职能定位和资本对公司关键性作用并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解释《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认定董事负担前述义务的理由是充分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注意义务还是忠实义务?抑或是一个独立、特殊的信义义务?我国既有文献一般认为监督义务属于注意义务的一种,与商业决策共同构成注意义务,[30]但该问题在美国公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不无争议。[31]
从特拉华州的判例看,监督义务的法律性质经历了由注意义务向忠实义务转变的过程。在Caremark案中,特拉华州衡平法院认为原告诉请被告承担监督责任并不涉及到利益冲突,因而不是一个有关忠实义务类型的纠纷。[32]七年后,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在Guttman案中认为,董事承担监督责任的法律基础,是因为他们没能尽到善意行事的义务(act in good faith / duty of good faith)而违反了忠实义务。[33]该裁判观点在三年后,被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Stone案中所确认,赫兰德(Randy J. Holland)法官指出,无论是在Disney和Caremark案中,董事之所以要承担监督责任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忠实义务,这也与衡平法院在Guttman中的认定是一致的;忠实义务并不局限于处理涉及经济上的或者其他被承认的利益冲突的案件,它也适用于受托人违反善意行事义务的案件。[34]对此,班布里奇(Stephen M. Bainbridge)教授等三位学者批评道:这种做法十分奇怪,将会导致传统上用于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忠实义务变得模糊。[35]他们猜测,法院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避免董事的这种义务被公司章程豁免的司法技术考量。[36]在学界,学者们既有将与善意行事义务相对应的监督义务纳入注意义务考量的,[37]也有将其纳入忠实义务讨论的,[38]未有定论,但前者是多数派。
笔者认为,前述分歧并不存在根源性矛盾,实然是监督义务在不同情形下可分属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质言之,就董事违反监督义务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而言,其既可能是违反注意义务也可能是违反忠实义务。前者主要是指,董事在客观上对公司可能或者将要受损并不知情,从而没能采取适当的监督行为最终导致公司受损;而基于注意义务的要求,董事在法律上处于应当知道该事实并须采取适当措施的状态。后者主要是指,董事在客观上明知公司可能或者将要受损,但却有意识地故意不作为,进而放任了这种损失的发生;这种明知公司要受损却有意识的放任和不作为,违反了善意行事的义务,在语义上可以说该董事对公司不够“忠实”,违反了忠实义务。
在后一种情形下,将忠实义务作为董事承担监督责任的法律基础,并非如班布里奇教授所猜想的那样仅是出于“司法技术考量”。诚然,不可否认的是,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将监督义务纳入忠实义务确有司法技术的考量,但是这种做法在法理逻辑上同样也是成立的:通常情形下,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原因是过失或者重大过失,[39]而当一名董事明知自己负有某种信义义务而有意识地不去履行时,他在主观上是处于明知、故意和“知法犯法”的状态,在此情形下其仍坚持“消极不作为”放任公司损失的发生,其在道德上的可非难性更加倾向于是对忠实义务的违反而非注意义务。这也正如赫兰德法官在stone案中所指出的:“当董事没有履行一个他们知情的义务,从而有意识地无视他们的职责,他们就会因没有善意履行信义义务而违反了忠实义务。”[40]通俗地理解,在语义上,董事未履行监督义务似乎应属注意义务的范畴,因为未履行某种义务,就意味着董事不够注意、不够谨慎;但古语有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如若受托人明知委托人利益可能受损而有意识、故意地“无动于衷”,放任或者希望这种损害的发生,这时候由于受托人在主观上对该项事务是处于充分知情的“明知”状态,对他的评价已不应再局限于“是否充分知情”“是否足够注意”“是否足够谨慎”等问题(即逸出注意义务的范畴),而应聚焦于他对委托人是否足够的善意、足够尽“忠”尽责(即落入忠实义务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在董事明知的情形下,若不采取任何监督措施是董事经过充分知情和研究后作出的、“为公司最佳利益计”的决策,那么该消极不作为本身也构成一项积极的商业决策,[41]此时,该监督义务就又脱离了忠实义务而进入注意义务的范畴。这是因为,监督行为本身就是有成本的,只有在监督收益大于监督成本时,实施监督行为对公司才是有益的。
一言蔽之,区分不同情形,董事的监督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分属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当董事应当知道而不知道公司将因违法行为受损且未能采取任何适当的监督措施时,董事违反的是注意义务/注意型监督义务;当董事明知公司将因违法行为受损且有意识地不采取监督措施或放任这种损害的发生和持续时,董事违反的是忠实义务/忠实型监督义务。
厘清董事对股东出资应否负有监督义务及其法律性质后,需进一步探讨的是该义务相较于一般性监督义务的特殊性,以及违反该义务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特殊性。
首先,义务对象上的特殊性。董事监督义务通常体现为董事对公司行为的监督,监督的对象主要是董事、经理和雇员等能够代表公司实施相关行为的公司代理人。而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监督的对象是股东。在现代公司法理论上,股东是委托人,而董事、经理是受托人,两者之间存在的“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所要解决和降低的主要制度目标。[42]世界各国公司法都赋予了股东选举和罢免董事的权力,以此来监督和制约董事权力。在此种制度构造下,要求作为被监督者的董事去监督作为监督者的股东,让“下级”去监督“上级”,难免有点“强人所难”,其成效可想而知:一旦董事实施了催缴股东出资的行为使股东对其产生不满,股东就可能撤换他,他将失去工作、薪酬和福利待遇;但若不催缴,其就将可能承担个人责任,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法谚有云:“法不强人所难。”有鉴于此,让董事对股东出资承担个人责任必须更为谨慎。
其次,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可以在董事、经理之间分配,但不可以被免除。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沃尔考特(Daniel F. Wolcott)法官指出,董事们的义务取决于公司的性质。[43]在事务纷繁复杂的公司中,难以期待每一位董事对公司所有事务都全面知悉和了解;同时,不同董事、经理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法律应允许公司将包括具体经营业务、财务会计、法律合规、人力资源等不同公司事务在董事、经理之间进行分配,进而使得董事、经理们能够专心于自己负责的工作领域,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这种分工既可以具有特定的法律形式,如通过公司章程或者内部文件对董事、经理的职责进行规定;也可以是事实上的,如某个董事在客观上实施了某个行为。如此,当某一个事务致使公司受损而须由董事承担个人责任时,应重点追究负责该项事务董事的责任,而不是由全体董事或者经理共同承担责任,从而实现“从集体责任到个人责任、从身份责任到行为责任”的合理问责与精准追责。[44]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和监督是公司事务的其中一项,也应允许公司将该事务分配给特定的董事负责,而使得其它董事免于承担和关注这项义务和事务。另外,公司法理论上允许公司通过章程豁免董事的注意义务。[45]笔者认为,这并不适用于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理由并不仅仅限于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乃是法定义务,还因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兼具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双重属性,当公司意欲通过章程豁免董事违反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而应承担的个人责任时,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履行情况就将处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状态,这就将进入忠实义务的范畴,而违反忠实义务是不允许通过章程豁免的。[46]
最后,共同董事(overlapping director)情形下董事对股东出资监督义务的特殊性。在公司实践中,尤其是在公司集团的情形下,一个人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是十分常见的情形。在公司集团中,母子公司之间在通常情况下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并不存在利益冲突,于此情形,共同董事只需要在两家公司分别履职,各尽其职即可。然而,一旦母子公司利益发生冲突,共同董事就陷入“一仆难侍二主”的困境,此时其应优先考虑哪一家公司的利益,便成为了一个十分棘手和尖锐的难题,斯曼特案便是一个典型的写照。在该案中,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同时担任母子公司的董事,他们对母公司开曼斯曼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亦对子公司深圳斯曼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在高检院组织的听证过程中,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表示,因显示器市场急剧变化,继续投资将会扩大亏损,开曼斯曼特公司作出了不继续投资/出资的决定,他们作为开曼斯曼特公司指派的董事,必须也有义务执行开曼斯曼特公司的决定。[47]由此,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便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若催缴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出资,则对母公司不利;若不催缴,则对子公司不利。于此情形下,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作为共同董事该如何行事?其是否仍负有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对此,公司法理论有较为系统和精细的回答,归纳而言即:区分是否是为全资子公司,在全资的情形下,只要不损害子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董事可以优先考虑母公司的利益而使子公司受损;在非全资的情形下,还需要增加不损害子公司其他中小股东利益这一要件。[48]具体到斯曼特案中,深圳斯曼特公司对外存在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而被申请破产的情形,故而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共同董事无权为母公司的利益计而牺牲子公司的利益。
因果关系在违法行为和损害之间建立某种事实和法律上的联系,从而使损害归咎于具有过错的主体,由其向受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果关系是矫正正义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甚至几乎是其全部理由。[49]因果关系的判断必然会受到行为和损害性质的影响。一般作为式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是较为直观的,譬如,甲开车撞伤了乙,甲开车的行为是乙受伤的直接原因也是近因,既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也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然而,董事因消极未催缴股东出资致使公司受损是一种不作为侵权,其行为(董事消极未履行监督义务)和损害(公司因股东未出资而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一般的作为式侵权存在极大的差异,在因果关系的成立上常常会受到如下诘问:出资是股东的义务,即便董事履行了向股东催缴出资的监督义务,股东也可能无力缴足出资致使公司受有损失,故董事消极不履行义务与公司利益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成立。这也是斯曼特案中,一、二审法院否定原告诉请的主要理由之一。
笔者认为,前述观点并未认识到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特殊性,而径性以判断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方法来认定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在侵权法理论上,以不作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所起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将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分为起果型因果关系和防果型因果关系。[50]前者是指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就是不作为,后者是指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不是不作为本身(如董事消极不履行监督义务),而是其他事实(如股东未出资)。[51]董事消极未催缴股东出资致使公司受损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即属于后者。哈特指出,当不作为是来源于第三方时(例如董事消极未催缴股东出资,笔者注),作为和不作为在原因地位并没有实质性差别。[52]就董事消极未催缴股东出资致使公司受损而言,董事的消极不作为至少在事实上不当扩大了公司遭受损失的风险,是引致公司受损的原因之一,在原因地位上与股东未足额出资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应当说,虽然股东未足额出资是公司受有损失的直接原因,董事的不作为仅居于次要或辅助地位,但是基于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应认定此种因果关系成立。
在学理上,董事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害可以区分两大类型,一是商业损失,二是非商业损失。[53]前者又可以分为商业判断失误致使公司受损和不公平关联交易致使公司受损两类,后者主要是指公司的不法行为致使公司受损。区分不同情形,董事消极不催缴股东出资致使公司利益受损可分属前述三种损失类型:
第一,构成商业判断失误损害公司利益。在特殊情形下,采取法律手段或其他手段向股东催缴出资的成本过高,或基于其他商业考量(例如股东是公司客户或供应商),董事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善意、谨慎地作出不向未缴足出资的股东催缴出资的决定,而后发现该决策是错误的,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此种损失即属商业损失。此时,董事履行的是对公司的注意义务,作出的是商业决策,受到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由此引申出的一个命题是:在特殊情形下,若违法对公司是有利的,公司能否“知法犯法”?[54]此时董事是否仍须承担个人责任?这涉及到董事商业判断的广度和深度问题,对此公司法理论上未有定论。[55]笔者认为,在我国法语境下,区分法律的位阶和效力,可以明确的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是公司必须要遵守的;其理由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本身就具有控制法律行为内容的功能,违反这类法律的法律行为无效,在法律被严格实施的前提下,公司将确定性地因此遭受损失。第二,构成不公平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在法人股东和公司之间存有共同董事的场合,董事作出不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决定因存在利益冲突而构成关联交易;若由此致使公司受损,即属董事对忠实义务的违反而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构成未尽监督义务导致公司因不法行为受损。这是最典型和常见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董事对公司行为的监督义务的对象是公司违反公法的行为,而在董事消极不催缴股东出资的情形下,董事怠于履行的是对公司违反或者说放弃私法义务或权利而受损的监督义务。
董事违反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致使公司受损后,应承担何种形态的法律责任?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是直接责任还是补充责任?斯曼特案中,再审法院判决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对股东未出资部分向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言下之意,即是认为董事违反监督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形态是连带责任。笔者认为,该裁判观点没有认识到董事违信责任的特殊性,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理由如下:
首先,董事违反对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致使公司受损是对公司的损害,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对股东出资义务的债务加入。从学理上看,在董事违信致使公司利益受损的场合,董事直接损害的是公司利益,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由于股东、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享有不同顺位的“剩余索取权”,[56]故而董事也间接损害了股东、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以后者有权通过股东直接诉讼、股东代表诉讼、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等制度向董事索赔,但是后者有权索赔的法理基础是因为董事对公司负有赔偿责任。因此,董事违信致使公司受损的赔偿责任与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是两个独立的、平行的、互不关联的责任。即便认为在前述场合下,董事应对公司负担赔偿全部股东未出资部分的责任,该责任与股东的出资义务之间亦非法律上的纯正连带责任,而构成事实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57]
其次,在无明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情形下,让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第87条、《民法总则》第178条(暨《民法典》第178条)[58]的规定,连带责任必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根据《公司法》第149条的规定,董事违法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承担对公司的赔偿责任。[59]《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规定,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致使增资股东出资未缴足的,承担相应责任;该条是对《公司法》第147条、第149条的狭义法律解释,因此,该“相应责任”也应指对公司的赔偿责任。据此,让董事对股东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在斯曼特案中,董事和股东之间亦无对股东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由是观之,再审判决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承担连带责任是否于法有据,值得商榷。
四、违反监督义务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与认定
境外的学说和判例有关董事监督责任的理论和规则对我国虽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在将其背后的法理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时,仍要根据我国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做相应的本土化改造,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应用法理和准确适用法律。在公司法理论上,董事违反信义义务致公司损害应承担的违信责任在责任性质上属侵权责任,[60]其构成要件应参照侵权法的相关规定。[61]我国侵权法在一般侵权行为的规范模式上采法国式的“大的一般条款”模式,而非德国式的三个“小的一般条款”模式,[62]故违信责任的构成要件与一般侵权行为的要件一致。我国实定法并未明确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理论上对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采“行为、损害、因果关系、违法性和过错”的五要件说,[63]还是“损害、因果关系、违法性与过错”的四要件说,[64]抑或是“损害、因果关系与过错”的三要件说,[65]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借助法律解释方法,以上不同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为了使分析更为精细,本文采五要件说。在五要件说下,行为、损害和因果关系共同构成要件事实,与违法性和过错相并列。[66]下文便对董事对股东出资监督责任的侵权法构成要件逐一分析。
董事在客观上未履行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是本文讨论的事实前提。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董事“客观上未履行催缴义务”?譬如,董事对未履行出资或未全面履行出资的股东进行口头催缴或者书面函告是否构成合格的催缴行为?抑或是说,董事必须采取诉讼的方式对股东出资进行追缴才能不被认定为是“客观上未履行催缴义务”?
笔者认为,只要董事对股东进行书面催缴即可构成对催缴义务的合格履行,该书面形式既包括纸面形式,也包括数据电文的形式。[67]理由在于,一方面,口头形式有违商事活动的严谨性和严肃性,这在比较法上有立法例可兹镜鉴。譬如,《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凡是超过500美元的买卖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68]并且,口头形式在发生纠纷时,存在举证证明上的困难,因而不足可取。另一方面,鉴于诉讼成本高昂,是否要采取诉讼的方式催缴股东出资属董事商业判断的范畴。例如,股东未出资部分仅为10万元,但诉讼费和律师费却高达20万元,以诉讼方式催缴,不符合最佳公司利益原则。此外,前述提及的美国特拉华州Caremark和Stone两案确立的董事承担监督责任标准之一,即是董事完全没有实施任何报告、信息系统和其他控制。笔者认为,只要董事通过书面形式对股东出资进行了催缴,就应认定其“实施了有关控制”,[69]构成对监督义务的适当履行。最后,关于行为期限问题,笔者认为,董事应当在股东出资义务到期后的合理期限内实施催缴,合理期限通常不应超过30日。[70]超过合理期限后的补救催缴,不构成对催缴义务的适当履行。
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公司受损的直接原因,董事消极未履行催缴股东出资的义务仅居于次要或者辅助地位。因此,判断是否存在损害的关键,是要确定股东在客观上是否确定性的缺乏清偿能力。在我国,确定一个股东缺乏清偿能力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股东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包括出资义务在内的全部债务,并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或者终结执行的;二是企业法人被依法破产清算,未能全额清偿包括出资义务在内的全部破产债务的;三是自然人股东死亡,且遗产不足以清偿包括出资义务在内的全部债务的。在法律形式上,通常体现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执行程序[71]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72]等。
在比较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一般区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因果关系,普通法系称事实因果关系,大陆法系称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该层次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采条件说;第二层次因果关系,普通法系称法律因果关系,大陆法系称责任范围因果关系,该层次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有可预见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等。[73]我国侵权法司法实践在裁判形式上并不严格区分因果关系的两个层次,但是在侵权责任的成立和范围的判断过程中,实际运用了两阶层的因果关系判断方法。[74]循此,在董事对股东出资监督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也应遵循两阶层的因果关系判断方法。
首先,关于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在董事消极不履行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致使公司受损的场合,公司的损失主要是由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造成的,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仅居于次要地位。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董事不作为致使公司受损中的因果关系,属于不作为侵权因果关系中的防果型因果关系,与作为侵权中因果关系存在显著差异。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只要董事的不作为与公司因股东未足额出资而受损之间存有原因力,那么就应当认定责任成立因果关系成立。在举证责任上,只要原告初步举证证明董事的不作为是引发公司受损的一个事实原因之一,那么就可以认定责任成立因果关系成立;但与此同时,董事亦可以举证证明即便其履行了催缴义务,股东在特定的时点也无力履行该出资义务,从而否定此种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此安排的理由在于,由原告来证明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与公司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于困难。在比较法上,《德国股份法》即采此种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公司根据《德国股份法》第93条第1款、第2款向董事提起损害之诉时,只要公司能够证明过失行为和损害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那么董事的举证责任就不仅涉及狭义的过失,而且涉及具有客观性的违反义务的行为和因果关系。[75]
其次,关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在责任成立的前提下,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一个法律政策选择问题。理论上关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一是相当因果关系说,该说以经验法则来判断因果关系,被王泽鉴先生称之为是“另一种损害归责之法的价值判断及案例实践运用”;[76]二是近因理论(the nearest cause),该说主要关注损害与行为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关系;[77]三是公平归属理论(justly attachable cause),该说聚焦于判断损失是否可以“公平地”归咎于被告的行为;[78]四是合理预见理论(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该说关注损害是否超过被告可预见的范围。[79]可以发现,无论是哪种标准,都逃不出价值判断的窠臼。从价值选择的范围上看,无碍乎有两种:一是让董事对股东未出资部分向公司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二是根据各董事的过错或者原因力大小,按比例对股东未出资部分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以上两种情形下,董事在承担责任后都可以向股东追偿,董事的赔偿责任和股东的出资责任之间构成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只不过这种连带责任属于补充连带、有限连带。[80]笔者认为,第一种方案更为合理,理由有二:第一,让董事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可以适度矫正公司资本全面认缴制给公司债权人带来的超额负外部性风险,加强对债权人的合理保护;第二,方案二依过错或原因力大小来判断责任范围,使法院负担了过重的裁量义务,不利于实现“同案同判”的司法正义。
董事消极未履行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因违反董事对公司的法定信义义务而具有违法性。对于违反法定义务的侵权行为,在比较法上,德国侵权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其称之为“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的一般侵权行为,此种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即因“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而具备。[81]采“大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的我国侵权法虽未区分出“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的一般侵权行为,但此种行为违法性成立的法理是一致的。我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董事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即属于“保护他人之法律”。[82]董事的行为违反该条,即具备违法性。
前文已述,董事消极未履行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既可能违反注意义务,也可能违反忠实义务。前者主要是指董事应当知道而客观上不知道股东未足额按时出资,消极未履行催缴股东出资义务,导致公司受损的情形;后者主要是指董事主观上明知股东未足额按时出资,却有意识地或者故意放任此种状态的持续。因此,应区分违反注意型监督义务和违反忠实型监督义务,判断董事消极不作为的违法性。
首先,在董事违反注意型监督义务的情形下,前文已述,法律允许公司将经营业务、财务会计、法律合规、人力资源等不同公司事务在董事之间进行分配,换言之,催缴股东的注意型监督义务可以仅由部分董事承担。因此,首先要判断的就是,哪些董事负有催缴股东出资的义务。在公司已经对董事之间的职责分工作出安排的情况下,只有负有催缴股东出资的义务的董事,其消极不催缴的不作为才具备违法性;其他非负有此项义务的董事因不负有此项义务而不具备违法性要件,或者说,他们可以声称公司指派他们负责另外的事务从而阻却违法性要件的成立。在公司未对催缴股东出资的义务作出分配的场合,该义务由全体董事负担,全体董事的不作为都因违反注意型监督义务而具备违法性。此外,在存有共同董事的场合,在不损害公司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前提下,共同董事们可以为母公司利益计,而免于负担向母公司股东催缴出资的监督义务。
其次,需要进一步查明,是否存在董事明知股东未按时足额出资,而有意识地或者故意放任此种状态的持续;这类董事违反了忠实型监督义务,其不作为亦具备违法性。在Stone案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董事善意行事的义务是忠实义务的内容之一;在Disney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将受托人有意识地不履行一项明知的义务,认定为是对善意行事义务的违反。对于不负有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的董事,虽然他不必去积极了解股东们是否按时足额出资的状态,也不必主动对未出资股东进行催缴;但是一旦他知悉了某位股东未按时足额出资或者根本不打算出资,从善意行事的角度讲,他即便不负有采取相关催缴措施的义务,至少也应具有向负有此等义务的董事报告的义务。据此,笔者认为,一位虽不负有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的董事,在明知某位股东未足额按时出资而不向公司或者负有此种义务的董事报告时,他违反了善意行事的义务,同时也违反了忠实义务,其行为具有违法性。斯曼特案中,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即属此等情形。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深圳斯曼特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的董事,对开曼斯曼特公司未按时足额出资和决定不再出资是明知的。于此情形,他们既没有向股东追缴出资,也没有采取减资措施,违反了对深圳斯曼特公司的忠实义务。再审法院以违反勤勉义务为由让其承担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
私法以过错将侵害行为和损害结果相统一,从而将损害归咎于过错行为人,实现矫正正义。[83]正如法儒耶林所言,导致损害赔偿义务的不是损害,而是过错,其道理就如同化学原理“让物体燃烧的不是光,而是空气中的氧气”一样简单。[84]因此,在董事消极未履行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致使公司受损的情形下,要使董事承担个人责任,还必须证明董事存有主观过错。在侵权法理论上,“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的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要件是推定的,其背后的法理是,“盖既有保护他人法律的存在,行为人自有注意之义务”[85]。该法理在我国公司法下亦是适用。我国《公司法》第146条规定了董事的消极任职资格,由此虽不足以直接推出董事应当知道股东负有向公司按时足额出资的义务,但结合《公司法》第28条[86]、第147条,通过法律解释可以得出,董事最起码应当知道股东负有向公司依法按时足额出资的义务。然而,前文已述,公司可以将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分配给特定的董事,因此,并非每位董事都须对股东们是否已经按时足额缴纳出资知情;只有负有监督股东出资的义务的董事才处于应当知道前述事实的法律地位。因而,一旦某位董事被认定负有向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那么其主观过错就推定成立。
此外,过错在内部责任分配中亦具有重要作用。侵权法以过错作为归责原则,尤其是在终局性责任承担者的选择上,必须要以过错为依据。在董事向公司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之后,在董事内部求偿关系上,可依过错或原因力大小分担损失。在过错大小的判断上,应考虑每位董事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工作时间、职务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87]
五、结论
公司资本是公司得以正常运营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是公司取得独立人格的前提条件;而股东出资又是公司资本的唯一来源,对维持公司独立人格、维护公司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作为公司受托人的董事应对股东出资负有监督义务。本文最主要的理论创新,即在于指出此种监督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并非仅属注意义务,而是区分不同情形分属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当董事应当知道股东未按时足额缴纳出资,但在客观上却不知道,从而未能实施适当的监督行为致使公司受损时,董事违反的是注意义务/注意型监督义务;当董事在客观上明知股东未按时足额缴纳出资,但却有意识地不作为、放任这种状态的持续致使公司受损时,董事违反的是忠实义务/忠实型监督义务。需要注意的是,在后一种情形下,若消极不作为是董事在充分知情和研究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那么其本身也构成一项积极的商业决策;此时,该监督义务就脱离了忠实义务而回到了注意义务的范畴。在斯曼特案中,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深圳斯曼特公司和开曼斯曼特公司的共同董事,在明知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未缴足出资、亦无进一步缴资的意愿,有意识地消极不履行催缴股东出资的监督义务,致使公司利益受损,违反了忠实义务,应承担对公司的赔偿责任。再审法院将违反注意义务作为胡秋生、薄连明等六名董事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基础,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最后,无论董事违反的是注意型监督义务还是忠实型监督义务,违反该义务应承担的违信责任本质上是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严格依照行为、损害、因果关系、违法性和过错五大侵权构成要件审查责任是否成立。
注释:
[1]在学理上,我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勤勉义务与注意义务(duty of care)、善管义务等概念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异,本文在相同意涵上使用前述概念。参见赵旭东:《公司法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314页;朱锦清:《公司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27页。
[2]参见《公司法》第148条。[3]《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4]参见深圳斯曼特公司与胡秋生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民事判决书。[5]在斯曼特案之前,司法实践中董事往往无须对发起人股东未出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尹纪宏诉朱镜春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205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中支行与山东蓬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6]相关媒体报道,参见《炸了!股东欠缴出资,最高院判决全体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载微信公众号“裁判讲堂”,2020年8月16日;王光明:《董事不能承受之重:股东欠缴出资的连带责任》,载财新网,2020年8月4日,https://opinion.caixin.com/2020-08-04/101588485.html。[7]参见捷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追加深圳斯曼公司为被执行人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深中法民四初字第54号民事裁定书。[8]参见深圳斯曼特公司诉胡秋生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破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9]参见深圳斯曼特公司诉胡秋生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破70号民事判决书。[10]参见深圳斯曼特公司与胡秋生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民事判决书。[11]笔者认为,斯曼特案中,外方董事与中方董事在公司法上的地位都是董事,应属该案的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被告。必要共同诉讼的相关阐释,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以下。[12]See William T. Allen & Reinier H. Kraakman, Commentaries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Williams & Wilkins, 2016, p. 229; also see Revised Model bus. Corp. Act § 8.30;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 4.01.[13]See William T. Allen & Reinier H. Kraakman, Commentaries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Williams & Wilkins, 2016, p. 283.[14]国内既有的关于董事监督义务的文献,主要是对境外案例的翻译和解说。例如朱锦清:《公司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83-599页;林建中:《注意义务的任务与极限:公司法的信义义务与金融风暴的省思》,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2期。[15]See Eric J. Pan, Rethinking the Board's Duty to Monitor: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Delaware Doctrine, 38(2)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9, 209-210 (2011).[16]Francis v. United Jersey Bank, 87 N.J. 15, 432 A.2d 814 (1981).[17]Graham v. Allis-Chalmers Mfg. Co., 188 A.2d 125 (Del. 1963).[18]In re Caremark Int'l, 698 A.2d 959 (Del. Ch. 1996). [19]Stone v. Ritter, 911 A.2d 362 (Del. 2006).[20]In re Citigroup Inc.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964 A.2d 106 (Del. Ch. 2009). [21]Graham v. Allis-Chalmers Mfg. Co., 188 A.2d 125 (Del. 1963).[22]In re Caremark Int'l, 698 A.2d 959 (Del. Ch. 1996). [23]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下级法院并非不能作出与上级法院既有判例不同的判决,只不过它们通常不会这么做。[24]See Stone v. Ritter, 911 A.2d 362 (Del. 2006).〔[25]〕Brehm v. Eisner (In re Walt Disney Co. Derivative Litig.), 906 A.2d 27 (Del. 2006).[26]In re Citigroup Inc.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964 A.2d 106 (Del. Ch. 2009). [27]See Robert Miller, The Board’s Duty to Monitor Risk After Citigroup, 1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1153, 1158-1161 (2009).[28]公法的概念十分宽泛,笔者认为,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公法表现为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则不在其中。更为详细的介绍,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147页。[29]参见吴建斌编译:《日本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7页。[30]参见邓峰:《领导责任的法律分析——基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赵俊:《董事勤勉义务研究:从域外理论到中国实践》,载《浙江学刊》2013年第2期。[31]笔者猜想,存在这种差异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学界还未对董事监督义务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32]In re Caremark Int'l, 698 A.2d 959 (Del. Ch. 1996).[33]Guttman v. Jen-Hsun Huang, 823 A.2d 492 (Del. Ch. 2003).[34]See Stone v. Ritter, 911 A.2d 362 (Del. 2006).[35]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Star Lopez & Benjamin Oklan, The convergence of good faith and oversight, 55 UCLA Law Review 559, 585-586 (2007).[36]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Star Lopez & Benjamin Oklan, The convergence of good faith and oversight, 55 UCLA Law Review 559, 597 (2007); also see William T. Allen & Reinier H. Kraakman, Commentaries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Williams & Wilkins, 2016, p. 312-313.[37]See e.g., Melvin Aron Eisenberg & James D. Cox,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 Press, 2011, p. 693-700; Robert W. Hamilton, Jonathan R. Macey & Douglas K. Moll,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 including Partnerships and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West Group, 2010, p. 672-686; Melvin A. Eisenberg, The duty of care of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officers, 5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945, 951-956 (1989).[38]See e.g., William T. Allen & Reinier H. Kraakman, Commentaries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Williams & Wilkins, 2016, p. 311-313.[39]参见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15页;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以下。[40]See Stone v. Ritter, 911 A.2d 362 (Del. 2006).[41]参见朱锦清:《公司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99页。[42]See Reinier R. Kraakman et 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 approach,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43]See Graham v. Allis-Chalmers Mfg. Co., 188 A.2d 125 (Del. 1963).[44]参见赵旭东:《中国公司治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载《现代法学》2021年第2期;王毓莹:《公司法规范变革的六大重要视角》,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45]See William T. Allen & Reinier H. Kraakman, Commentaries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Williams & Wilkins, 2016, p. 246-247.[46]Se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102(b)(7);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2.02(b).[47]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胡秋生、薄连明、史万文、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与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申请监督案公开听证会》,载中国检察听证网,2021年3月29日,https://jctz.12309.gov.cn/main/live-details/991616978345。[48]参见黄辉:《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314页。[49]See David Howarth, O Madness of Discourse, That Cause Sets Up with and Against Itself, 96 The Yale Law Journal 1389, 1389-1424 (1986).[50]此种分类借鉴了刑法学上对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的分类。参见侯国云、梁志敏:《论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1期。[51]参见李小华、王曙光:《论侵权法中的不作为因果关系》,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5期。[52]See H. L. A. Hart & Tony Honoré, Causation in th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38-141.[53]See William T. Allen & Reinier H. Kraakman, Commentaries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Williams & Wilkins, 2016, p. 248.[54]该“法”既包括公法,如遵守刑法;也包括私法,如行使合同权利、遵守合同义务。[55]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 & James D. Cox,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 Press, 2011, p. 700-708;William T. Allen & Reinier H. Kraakman, Commentaries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Williams & Wilkins, 2016, p. 277-281.[56]See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Corporate Contract, 89 Columbia Law Review 1416, 1424-1425 (1989).[57]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608-610页。[58]《民法典》第178条第3款:“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59]参见《公司法》第149条;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09-410页。[60]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07-408页。[61]需要说明的是,董事的违信也可能是受到幕后股东或者其他主体的指使,此时后者的法律责任亦有待探讨。可参见刘斌:《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62]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206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63]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0-63页。[64]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65]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66]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67]参见《民法典》第469条。[68]Se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2.201.参见潘琪:《美国〈统一商法典〉解读》,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52页。[69]See Stone v. Ritter, 911 A.2d 362 (Del. 2006).[70]以30日作为默视合理期限,符合民事立法传统。参见《民法典》第145条、第171条、第177条。[71]参见《民事诉讼法》第25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法〔2016〕373号)。[72]参见《企业破产法》第120条。[73]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0-238页。[74]例如河南福林克斯机械有限公司与翘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等海事侵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408号民事裁定书。[75]参见[德]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5-227页。[76]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267页。[77]See William Lloyd Prosser,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orts,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41, p. 247.[78]See Henry W. Edgerton, Legal cause, 72(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American Law Register 211, 211-244 (1924).[79]See A. L. Goodhart, The Unforeseeable Consequences of a Negligent Act, 39(4) The Yale Law Journal 449, 449-467 (1930).[8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关于公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81]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73页以下;《德国民法典》,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732-733页;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6页。[82]参见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120页。[83]See Ernest J. Weinrib, The Idea of Private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45-170.[84]参见[德]耶林:《罗马私法中的过错要素》,柯伟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85]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7页。[86]《公司法》第28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87]对此,有境外判例可供参考。See In re Emerging Communications Inc. Shareholders Litigation, No. 16415, 2004 Del. Ch. LEXIS 70 (Ch. May 3, 2004). 在该案中,特拉华州衡平法院考虑了不同董事的专业技能,最终判决具有投资银行经验的董事承担赔偿责任,其他董事无责。